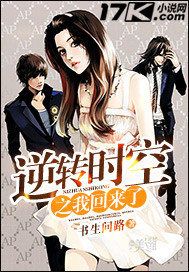走了数里,张天福方才不再追赶。泽世回顾身后,竟只剩孤身一人。心中凄凉,下了马来歇息。此时天已明亮,泽世太困了,寻到一处草窝里,将马栓在附近一棵树上,潜身睡了。
睡了许久,朦胧中听得有人言语,声音渐大。泽世抓枪在手,小心起身,将眼看来人,却是周吉带了数个人过来。周吉道:“我说大哥的马怎么在这,原来大哥在此歇息。”
泽世道:“别说了。你哪里来?”周吉道:“本来守着盘虫驿,凌高峰这狗贼引一支清军从南边迂道进了县城,我回军去救,后面清军大举进入,我兵少当不住,躲进林子里。后听说凌鸟又诈躲入钱三哥营中,趁他不备,使人刺杀了三哥,伏兵尽起,杀散了我军。”
泽世道:“不渝呢?”周吉满面愁容道:“不知道。怕已……”泽世叹息道:“我们回县里去寻不渝。寻到寻不到,再去太平与旌德县找恒之。”周吉道:“好,咱去宰了那狗县令。”
日暮时分,泽世与周吉将马匹、枪、叉都交与了余下几个兵士,令他们在山坳里藏着。两人扎紧了衣服,插了腰刀,周吉背上负了一把大刀,向县里行去。
到了县郊,日落月上,光影幽幽。两人拣小路向凌高峰宅里行去。路上时有清兵巡路,两人都避开了。来至院墙外,院门关着,墙却不高,两人遂逾墙而入。刚落地即听得有人走近,慌忙都趴进墙影中。
月光中见是一个仆从打扮的人走过,去了茅房然后回转来。泽世忽地跳出,将刀架住他脖子道:“休要叫喊,不然顷刻要你命。”仆从张大了嘴不敢出声。
泽世道:“你家老爷呢?在房里吗?”仆从摇头道:“有一个张将军据了县衙,晚上请老爷吃酒,老爷人还未归。”
泽世道:“你可知嘉义伯的下落?”仆从道:“不是杀了吗?”周吉旁边叫道:“是杀了你吧!”一手捂住仆从的嘴,一手将刀在他脖子上一抹,登时割破喉管而死。
泽世道:“你做什么?里面人看他不回,定要出来查看。”周吉说道:“我方才怒了,一时情急。现在咱一不做,二不休,将里面人杀光了就是。凌老贼已是犯了全家抄斩的死罪。”
泽世道:“胡说。他该死,与他家人何干?”此时听得门开,有女声唤道:“小五,你怎么还不回来?与谁说话吗?”两人赶紧藏起。那女子渐渐走近,周吉低声道:“大哥,我自进去。等我叫你进来你再进来。”
泽世欲待制止,心里道:“且由他吧。我已把话说了。他不听,与我无干。”那女子方看见地上仆从的尸体,刚要叫喊,周吉一跃而出,一刀杀了。悄悄趋近后门,见门掩着,并未上栓,里面透出光亮来。周吉侧耳一听,有人说话。回转身子,看到侧边一间厢房,窗户是黑的。周吉移过去,将手推外门。原来也是虚掩的,周吉提刀在手,轻轻开门蹩进去,只是内中什么都不能见。他又开了里门,走到外间,只见烛光里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儿玩耍。
周吉本要动手,停了片刻,却下不了手。心中道:杀不杀,只看你们叫不叫了。乃走出来将刀一晃,妇人与小儿已是晕了。周吉便舍了他们,步入正堂,见有数个男女在打双陆,泾县捕头程六也在其中。当时周吉一手拿腰刀,一手持大刀,抢出来,一刀剁了一个,已是砍翻了数人。来砍程六时,被他侧身闪过,举刀来斫周吉。周吉左手刀架住,右手劈过一刀。程六急往后退开,起一脚将一个凳子踢飞向周吉。周吉让开,也起一脚,踢出一只凳子,正中程六身上,程六立不稳跌在地上。周吉跃起,一刀将他头枭了。侧室中奔出一个女仆,一边喊一边往门前跑。周吉投出一刀,正中其背,赶上复砍了一刀,也将她杀了。
又寻到其余房间,床底下揪出两个人,都杀了。一共杀了十来口。乃侧耳于门前,听外边的声音。听了一会,并无异样。
此时周吉满脸是汗,身子都有些抖。将汗拂了,定了一定,出来对泽世道:“大哥你进来吧。都了结了。”泽世入内,见着男女尸身,皱眉道:“你都杀了?”周吉道:“小孩儿未杀。还有一个妇人未杀。他们晕了。”
泽世道:“此算是警示。下回不可如此了。”周吉道:“知道。”两人就去前屋中等着凌高峰。
直等到丑牌时分,方听得外面有人喊门道:“快来开门!你家老爷喝醉了,张总兵着我们送他回来。”周吉道:“有清兵,一并杀了吧。”泽世道:“不行。惊动清军,我们必不能脱身。我来装一装。”一面迅即套上一个仆从的衣服,走上前开了门,见一队清军围在门前,凌高峰歪了头,一身酒气,由两个清兵搀着。泽世笑道:“多谢军爷们相送我家老爷。我家老爷他日必请军爷吃酒。”
一个兵头道:“扶他进去吧。酒是少不得的。”泽世将凌高峰扶进去,清军自去。泽世关了门,周吉看着凌高峰道:“老贼,还不知死到临头呢!”看着凌高峰软瘫一处,泽世从庖房取了一盆冷水,往凌高峰头上浇去,丝毫无用。
周吉道:“欲要他醒,只有一法!”当即扬刀将凌高峰右臂斩断。凌高峰痛声大叫,酒意早消了,护着右臂浑身发颤。
周吉道:“老贼!你看着我们两人。你有害了我不渝哥吗?”凌高峰四面环视,瞠目痛声道:“你两个畜生,只管杀了我!我一家人都被你们杀了,我难道还贪生吗?”
泽世问道:“你为何要降清?为何突然降清?”凌高峰冷笑道:“不降也是死。我原来不怕死。但不能死。如今可以死了。”
周吉怒火陡窜道:“死不改悔!吃我刀吧!”当头一刀,将凌高峰劈死。还要再砍,泽世以刀架住道:“好了。我听他言语,他也有难言之隐的。以小县来抗清,是要舍了一家的性命。他为保家才降的也说不准。死人为大,不要再砍了。”
周吉怒气未消,道:“大哥!你也顾家,我也顾家,还抗什么清?都俯首帖耳罢了。他害了我们许多兄弟性命,我杀他一百刀,也不解恨!”
虽如此说,周吉也不再动刀。泽世以血在墙上写道:“有敢降清者同此”,周吉寻块干布将刀上血抹了,又从房中找出一些碎银,两人开了后面院门,悄悄往那藏着马匹、兵器的山坳行去。
毕竟不知不渝生死,泽世与周吉的安危,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