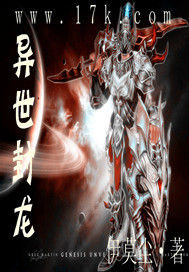恒之不语。盛泽世道:“敢问巨山兄年有几何?”四叔道:“年方二十岁。”泽世道:“二十岁也能做得。不过,既然当了首领,凡战必须在前,遇敌不可退缩。若不然,辜负了我等的殷意,也毁了你们左氏声誉。”
四叔叹口气,脸上无神道:“我儿不至如此的。”陈氏从内室走出道:“左不渝,你跪下。”不渝吃惊道:“母亲,这是何为?”
陈氏道:“左氏虽众,谁不知你祖父才是宗族之望?你祖母才死两月,难道左令公的名望都保不住了吗?你们兄弟年幼失祜,我一个寡妇希望你们留在家里,你们却都要去。既去,又要找什么人来做首领,你们无愧于先祖吗?”
一番话了结,不渝当真跪下了,满脸的羞愧,言语不得。恒之说道:“母亲,儿虽不才,就做这什么首领吧。”看着三叔、四叔们。
四叔也十分尴尬,勉强笑道:“不是我们要争这个首领。只是恒之资历太浅,尚若弱冠,怕义士们不能相服。”
陈氏看着不渝,闭上眼睛叹气。“让我来吧。檄文是我写的,从兄不在,我做领头人。我不会武艺,恒之可以助我。”不渝站起,他的身上有一股热流在翻涌。热流冲上大脑,他觉得自己清醒而又不能控制自己了。
几位族叔相互一视,三叔点头道:“也好。不渝是去过北京,见过先帝的,我众人都以他为左氏的希望。怕他不愿去做,既愿做,就是不可更替的。”
四叔道:“不渝肯出来,我还说什么?我先回了。”与族叔们都去了。陈氏道:“渝儿你起来吧。”一脸郁然的转入内室。泽世道:“不渝公子,你放心吧。做领头的第一就是要志坚,心决。”
不渝点头。许久,说道:“我在想,要不要效法信陵君救赵时的做法,父子从军的父亲回去,兄弟从军的哥哥回去,让勤王的义士省却了后顾之忧。我兄弟并不在内。”
泽世说道:“与其如此,倒不如使身体羸弱的,心怀观望的回去。”周吉道:“都回去吧。人不在多,在精。”
泽世又道:“南京危急。过了明日后日,大后天咱们必须出军。”众人都同意:“这是必须的。”
隔了一日,盛泽世、周吉都在点校兵马,定在巳时出军。不渝与恒之一早却与左氏宗族从军的四十多人同来至后山中央一座小岗上。岗上密布着新老坟茔,茔冢前都立着碑石,有的高些,有的低点。
不渝说道:“祭奠了先人,我等好行。”恒之与各左家儿郎将果品分开置好,纸钱都摆放了。众人齐跪在左氏远祖腾公墓前,不渝长吁一气,说道:“左氏源出黄帝时之史官,已有四千多年流长。先祖腾公,五百年前自河南迁入,今日桐城左氏蔚为繁盛。方今国家有难,男儿不辞。今日拜别于先祖,望列祖列宗佑我左氏,佑我大明。”
日头不是很紧,不渝的额上却渗着许多汗珠。他的面色凝重,两只眼睛很深,看不出里面盛着什么。
各人站起,分开向各自先人的墓前走去,不渝与恒之移至祖、父的墓前。两墓连在一起,一边还有祖母的新墓,再旁边是一个衣冠冢,正是史可法的。可法曾在左家住过几次,留有一些衣物。不渝将它们收拾了,建了这个衣冠冢,以作凭吊。
兄弟俩双双跪下,不渝道:“祖父,祖母,父亲,史伯父,你们能看得到我们吗?要打仗了,不渝与恒之都要去与那清虏拼命。你们见了,是高兴还是难过?”说着,不渝自己流下泪来。恒之道:“哥哥哭什么?怕吗?”
不渝拭了泪,说道:“我是怕。怕许多。怕死,怕杀人,怕损了左家名声,怕……”长叹一口气又道:“史伯父私下里曾对我说,乱起后我最好躲藏起来,以全性命。伯父是为我好,也是看出我不是一个能成事的人。但我如今除了一条命之外,还有什么?清军来了,又将剩什么?与其苟且活着,倒不如死在战场上!死了不知痛,活着真受罪!”
不渝说到此,忽然以头触地,连撞了十余下,一次凶过一次,将恒之都惊呆了。恒之回过神来,急忙将不渝拉住,喊道:“哥哥,做什么?何苦伤了自己!”看不渝额上,皮早破了,血痕数道,眼上还挂着泪。
恒之又呆了半晌,只是说不出话来。不渝又道:“祖父,您与阉党相斗,英名贯于天地,伯父,您死守扬州,沧海巨川为之动容!我们今日一去,不知尸身可能还家?但我们若死,虽粉身碎骨,亦必葬在中国。我们俱为父母所生,我父母先祖亦为中国所生,为国而死,夫复何憾!”
恒之等人听不渝这样说了,方才定下心来。不渝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来,看着书面道:“这些年来作的诗文积为此集。如今才觉着全无一些意味。”翻了一页,开篇第一首诗道:“我思:我思天地外,总有浮云痴。离却人间世,漂游无所羁。”又一首道:“伤诗:胸中万语化为诗,相对悠悠渐渐痴。诗外诗中还自我,何人会意解堪识?”苍白一笑,将书合上,缓缓置于燃烧的纸钱上,看着书渐化为灰烬。
恒之立着一动不动,迎着风,他砸着嘴说道:“先人们都安歇吧。身为左氏人,死为大明鬼。我们去了!”看着不渝道:“都在等我们。走吧。”
不渝起身,众人都站起,一齐下了山岗。
到了家门前,左氏宗族老小都围拢过来,纷纷嘱咐、告别。陈氏看着两子道:“你们不要念着家里了。若你们都死了,为娘必随你们而去。只恨我尚无一个孙儿……”言未毕,滴下泪来。不渝与恒之双双跪倒,不渝道:“并非永别。母亲更不要说随死的话。这样说,我们生不如死了。”恒之道:“母亲,我们真若死了,你也请好好度日。只当我们被玉帝请去做天兵天将了。”
陈氏哭着笑道:“我儿果长大了。知道宽慰为娘了。”抚着二子之头,眼角复又溢出泪来。不渝与恒之也流了泪,二人立起,说道:“母亲留步,我们走了!”
当时与众儿郎跨上坐骑,奔往安庆府的官道上去了。盛泽世、周吉与义军都在那里等候。
这一去从此走上多年抗清路,演绎出多少事故来?尽在后文。
不知义军怎的勤王,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