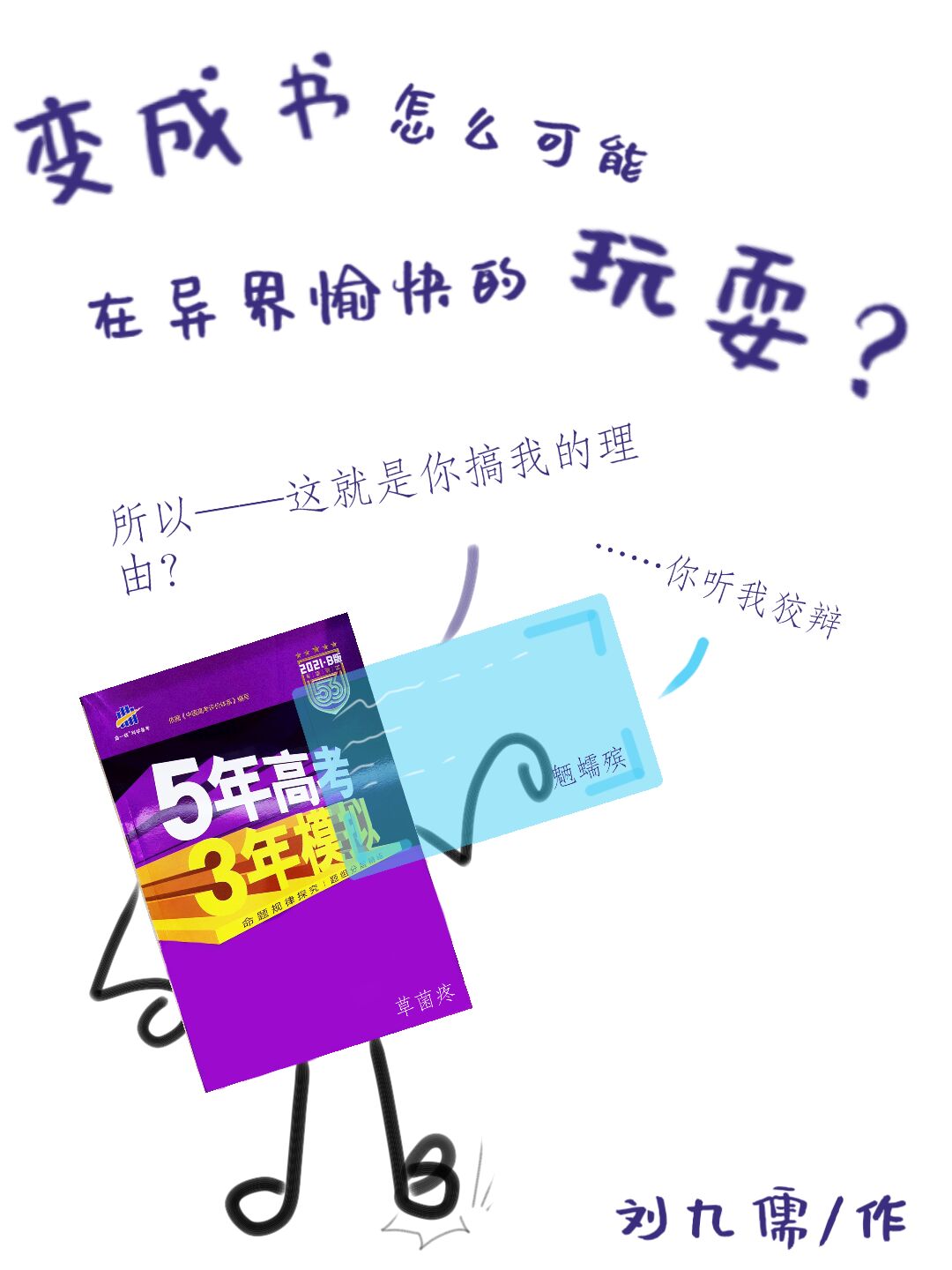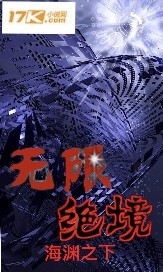“哪个人?你这请求也来的太快了些。”
刘鼎道:“是先前的翰林小吏张家玉。他是刘鼎的朋友,有些迂,却不曾害过人,也没有钱,如今已被关了数日,还望陛下保全他的性命。”
自成笑道:“这个人有意思。朕也不想就杀了他。明日朕亲来问审他。”当时自成又问了些话,刘鼎沉着应答,众人又闲言几句。自成起身离去,众人各自散了。
刘鼎走出,后面李岩跟上问道:“更生,你不是懂兵法吗?怎么又说不能带兵。”
刘鼎笑着轻声道:“李大哥,我若说能带兵,怕犯了上面忌讳。我作谋士已是某些人看不顺的,改要兵权,可不得了。他们以为大局由自己定了,我却来分功呢。”李岩道:“也是。”
刘鼎即去吏部,核了身份和官职,领了一身新的蓝色官袍。之后也不肯多走动,除了李岩暂居的王府,只在自成召见时去皇宫。
再说次日己时,自成来至武英殿,牛金星、李岩、刘鼎等殿下立着。自成命道:“将那糊涂的书生张家玉带上来。”
兵士即解了家玉入殿上前。自成放眼看他,身系枷锁,形容枯槁,然傲然挺立,怒目相视。
刘鼎心中惨然,忙道:“张家玉,见了真龙天子,还不下跪?”家玉道:“你个没骨气,不知耻的奴才!你枉做一个真人,绝非一个君子!你要我与贼为伍,不过死而已!”
刘鼎急得脸色发青,无言可语。自成道:“下站的,朕闻你有荐举人才于新朝,是真的假的?”家玉道:“真的便是真的,不过……”牛金星说道:“不过什么?你自家为何不降?”家玉道:“怪吗?”自成道:“快说缘由。”
家玉呵呵大笑:“无其他缘故,耍你们而已。所荐诸人,俱在南方,你们如何得用?”
自成大怒,“这野人无礼!来人,把他扯出去斩了!”
家玉面不更色,骂道:“逆贼,由你逼死先帝,我戏你不得耳?”刘鼎急跪下道:“陛下,请容我一言。张家玉此人性情刚硬,其实并不仇恨新朝,若杀他,恐失民望。”
自成道:“你若能使他跪朕,朕即免他一死。”刘鼎道:“请陛下不惟免他死,还能解放他去。”牛金星道:“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李岩道:“陛下襟怀宽广,不须太过计较此人。”自成道:“人各有志。依了刘鼎你吧。”
刘鼎看着家玉,思量片刻道:“张家玉,你若肯跪下,即恕你前罪,如若不然,当诛你九族,你的父母妻儿俱不能免!”
家玉也思量片刻,乃双膝跪地,说道:“何必累我父母!”
刘鼎笑向自成道:“陛下,他跪了。”自成也笑道:“放他去吧。此是孝子。虽不为我用,朕也不惧他为明用。”
兵士将家玉押出,卸了他的枷锁,说道:“你真是走了大运,皇帝心情好。赶紧去吧。”
家玉出了皇宫,回到房舍,收拾细软欲离京南下。他本来没有家小在身边,轻轻走到南门处,只摇一摇头回转了身去。原来城门处有兵丁盘查,没有令牌文牒是出不去的。
家玉一路惆怅,细细思量着忽然想到了一座去处。却是方以智提过的普惠寺,他虽不敢断定以智就在寺里,但自己此时落魄如此,又担心李闯哪一天又要抓他去,不如待寺里清净。
于是打听着走上城东去,在一条冷寂些的街上寻出这家寺院,青砖灰瓦,悬着匾额,两扇门紧紧掩着。家玉上前敲开门,里面出来一个僧人,道声阿弥陀佛,问道:“施主是来避难的?”一面让开身去。家玉欠个身作答:“便是了。”走入寺内,但见内里是一间进香殿,摆着几尊大小菩萨,待着数个俗人。走进去是一个大院子,一侧燃着一个大铜香炉,冒着紫气,旁边植着几株松柏,修的齐整。再傍边是几进偏殿,后面又有一排的屋宇。
此时出来一个主事的和尚,看见张家玉虽装束与常人无异,气度却非俗人可比,问道:“施主尊姓大名?”
张家玉淡笑道:“鄙人姓张名家玉,不知贵寺住持可在?”那和尚合掌道:“阿弥陀佛。原来是张施主。可不是方施主的契友吗?住持正在内间和方施主,另一位左施主谈话呢。”
家玉心里道:“多认识人总是好的。”口上道:“正是我了。麻烦领我就去见他们。”
到了一间侧室门前,和尚推开门进去了,家玉跟着入内。就见到左不渝、方以智坐在椅子上,旁边一个老和尚慈眉善目,胡子花白的,三人喝茶叙话。家玉道:“到底还是来寻你们了!”以智见了喜道:“听说你被抓了,我们都急坏了。幸而出来了。”不渝欲笑又哀地道:“玄子大哥,忧死我们了。”
张家玉也涩笑道:“我没有那么容易就死,让你们担心了。”对着住持道:“张家玉这里有礼。”住持回礼,几人说话不提。
再说过了两日,家玉三人还在房内商议怎么出离京城往南边去,忽然有小和尚来道:“外边有人要见三位。”
以智听了,惊道:“闯军捉拿前吏,是他们来了?”不渝道:“欲擒故纵吗?”家玉站起,问道:“几个人?”
“就两个人。”不渝道:“是谁呢?”正想间,已走入两个人,不渝见了吃惊不小。
以智叫道:“刘鼎?”家玉道:“不想你真降了闯贼,可怜我以前还和你称兄道弟!”
刘鼎摇摇头道:“你们不要太拘执了。我也想做大明的干臣,不行。”旁边左不渝呆了半晌,方道:“伯父,你不是……”
以智、家玉回过神来,看另外一人年届五十,穿着长袍,神色黯然的。以智道:“这是左按察?”来人点一点头道:“是老夫。我没有死。降了大顺,现在是户部官员。”
左不渝一脸惊疑道:“都以为你死了呢。”左安国叹息道:“死了倒好。可恨下不了心。如今也没得退了。”
张家玉道:“原来又是一个胆小怕死的窝囊废。真辱没了左御史的家风。”
左安国盯着张家玉,不悦道:“说我便是,不要说我父亲。”张家玉听他这样说,冷冷道:“你也知道惭愧!”刘鼎道:“玄子,密之,贯之,今日我们不必说当不当降的话,这话也说不完。只说你们要怎么离开京城好了。”
以智问道:“你哪里知道我们在这?”刘鼎道:“以为你们瞒的过我。”不渝道:“伯父,我晓得你定有苦衷。升之大哥本来是同我一道的,到了北直隶他偏生了病,只好停了。此时定是在南都了。”
左安国道:“傻侄子,他不是病,必是自己不敢来,装出来的。”刘鼎道:“左大人可以取到出城的令牒,你们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