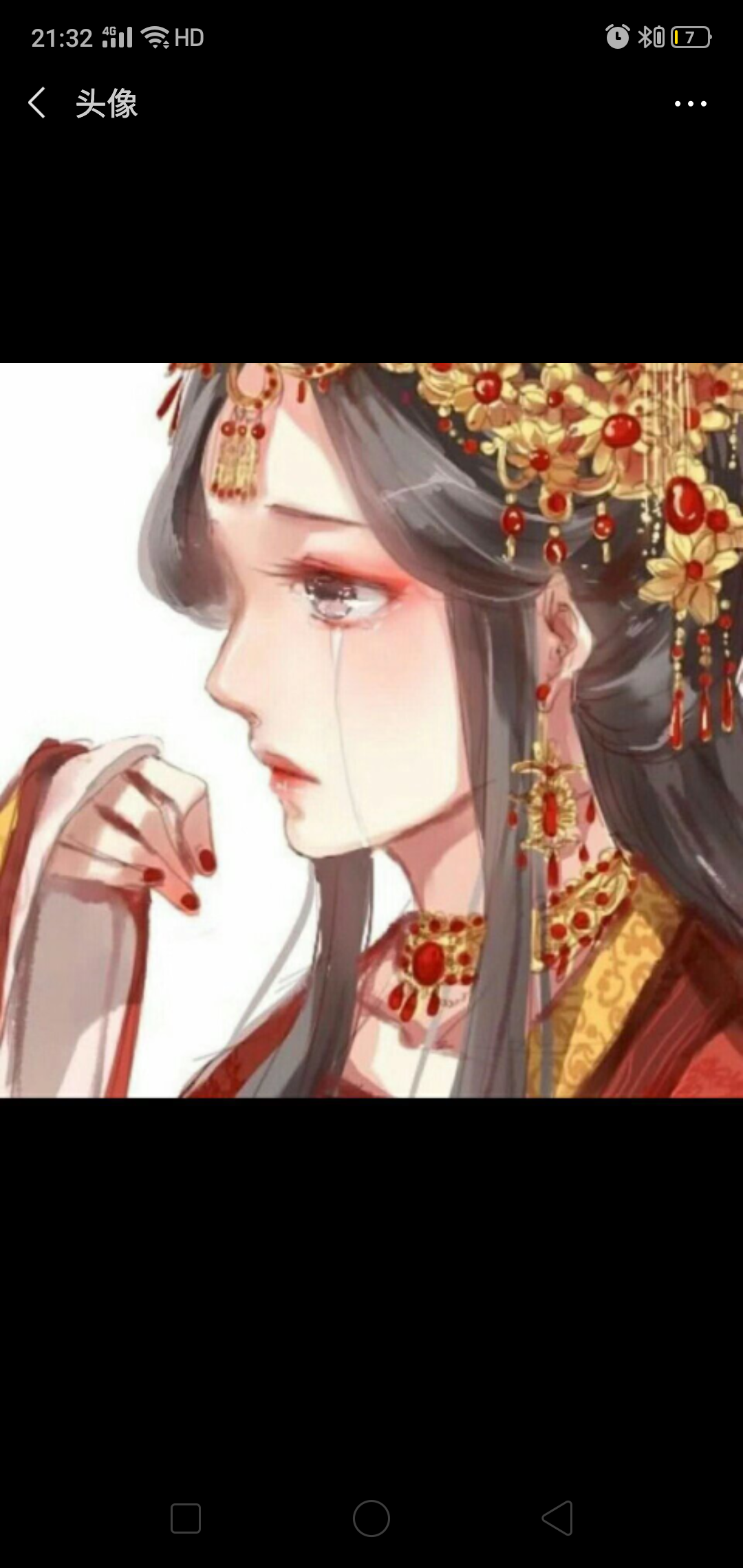她还没在宫里发过这么大的火,今日却是故意为之。她想试试她的性情变化谁最想看到。她把许昌走时留下稳妥的葛公公调走,才能放手去撒泼。
宫里的消息传得真快,紫苏宫的太后差人来问她可好。
这让她更加确信,宫里头安插了不少想要搅乱宫闱的。她不知道对方是谁,只能静静地等着葛公公来报和对方能露出蛛丝马迹。
奏折有人看,差事有人去办,仗有人去打。她只管闷在宫里当个养尊处优的皇帝,这样的格局她在一手形成的。收拾旧河山未必那么容易,打仗在前面,但黑手伸到后宫朝堂里来了。
她早就看到,却不能相信这样的事,如今局面摆在面前,她只好认了。她把宫人都撵出殿外,也给想要接近她的人多一些机会来靠近她,从而把目标缩小。
到底是谁?她记得昨天晚上在宫灯下留下的你两个背影。那只孔雀簪让她记忆犹新。
在这个宫里掖庭宫里没有一万人也有八千人,一百多年来宫中留下来的这些宫人,有的是别国的妃子国破没入宫中为奴,也有从民间选入宫中的。她能安稳地到今天不被人牵制,完全是梁景和云霓衣拼着自己的命保下,才能让她在皇位上坐稳。
她的身边存在的都是自己人,现如今随着她的年龄增长,多少人盯着后宫那些空置的妃子的位置,想要拿来做文章。明的在朝堂上直言让她立妃子,暗的不外乎托关系送进宫等着用 姿 色 来当筹码。
以前她可以借着把国事抛给梁景,把后宫丢给宁绒和云霓衣,如今她想把这种走了还要回来的局面结束,回到宫闱之中,真正亲政以后,她立了誉凡为太子,才真正知道朝堂和后宫的弯弯绕绕。
天下就像一盘永远没有办法停止的棋盘,你想在这其中有个自己的落子之地,就看你能看不看得清这埋在其中的暗子到底是谁。
“皇上,邵常侍让奴婢来问问皇上何时摆驾御书房?”她正在思虑着怎么更好地引蛇出洞,宫人进来禀告。
“就说朕过会过去。另命御书房的宫人们好生伺候着各位常侍,不可有任何怠慢。”她依然闭着眼睛回答。
“是。”宫人领命便退下了。
宁绒那边不知已经找到了可疑之人了没有?后宫之中只有一个皇后也不安宁,再来多几个妃子怕是更有的生事。
以前她是任意让人摆弄的小皇帝,如今她羽翼日渐丰满,怕是有人想要拿她没辙,只好用暗的。
她还记得当初林默是怎么进宫,当年她将计就计跟着林默,倒是迅速地引发了常州之战。梁睿在常州非死即伤看着是在战场上,但我方兵力部署敌方一定知道。
她曾经怀疑过身边的人,但后来发现都不是。曾经梁家恩宠无双,没人能动梁相府。但只要挑拨离间,让梁景失去信任,她收回大权,梁睿调离她身边到了战场,自然会有人要动作。
当初她执意让梁睿去常州北征,一来是远离朝堂,二来是让所有人都麻痹在她和梁相府有了裂痕。
如今她把这些都做了,想要搅乱风云的人也就浮出水面了。
她原以为让她当了女扮男装的皇帝已经够荒唐,竟然有人要用女人的身体来扭转自己的局面。
看来这十八年不是她一个人在成长,所有人都在谋算。昔日先帝在位不断劝谏先帝要纳妃,先帝执意只守着一人,后来英年早逝,说是暴病,谁知道原因,这些年她明察暗访终究是没有结果。如今怕是发现了她和先帝一个模子出来的,劝谏无果的,索性都不说,表面上是恭恭敬敬的,实际上是在暗中谋划。
她把八个年轻英俊的才子安插到宫中来当个常侍,给他们一个假象,皇帝断袖或许是后宫一直空置妃位的主要原因。她闭着眼睛心里却从未如此清醒,一朝天子一朝臣,未来就看谁是能和她抗衡的人。
她一天都不吃正餐,吃点水果和点心,不饿也不饱,就像让自己能放空一切静下心来好好地想想她该如何利用这个局面。
到了傍晚,内侍葛公公回到宫中,一到寝宫,就来拜见她,发现一桌子的果子皮核:“皇上,奴婢一刻没在皇上身边,皇上这么糟蹋自己身子,一天一口膳食都不进,吃些果子充饥,这该如何是好?”
“葛公公,朕让你去办事,你还能一直盯着朕,莫不是朕要在你的管教之下才能活着。”她故意曲解葛公公的意思。
“皇上,奴婢不敢。”葛公公赶忙跪了下来。
“从即日起,你不用在朕身边伺候了。听到了吗?”她在大殿上大声嚷嚷着,生怕没有人听到。
葛公公不知为何他刚踏入这殿门就被她呵斥:“奴婢在皇上身边服侍也有一段日子了,奴婢自认为无过错,不知奴婢犯了何罪?”
“朕是天子,你处处挟制着朕,是何道理?以下犯上。逐出去。”她大声呵斥,把殿内的侍卫给引了进来。
“带下去,等候朕的处置。”她朝着进殿的侍卫说道。
“是。”她用这种蛮不讲理的方式把这个在她身边守得牢牢的葛公公给彻底地带走了。
葛公公一走,她便让接替葛公公的宫人小成子去给传旨让程田舒把寝宫和御书房的侍卫调走一些, 让一直在窥探的人觉得有机可趁。
这天下间能保护她的人有一天会一个个地远离她,她要学会着保护他们。
她原本以为自己一回到宫中束缚在宫里苦闷委屈,昨天在轩茶阁的那一幕似乎让她看到了什么,回想起一些可疑的陈年旧事,想想这些年的一切。她就全明白了。
人莫大于心死。如今她的心活过来了,梁睿在常州,誉凡宁绒在宫中,她回来布下的这个局终究要维持下去。
在寝宫憋了一天了,她不想去御书房,溜达着溜到宁绒的寝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