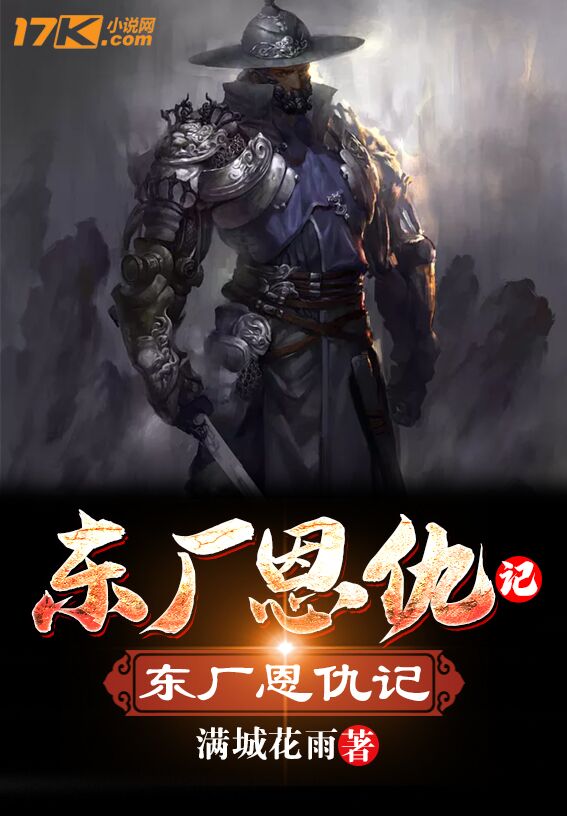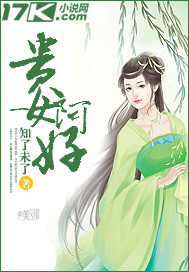河套自从曾铣离开之后,顿时乱作一团,俺答直接打到了居庸关,不过因为居庸关是一处天险,俺答难以攻入,又转道杀向宣府,把总江瀚、指挥董蔭相继战死,手下大多逃离。
其中有一人名叫项世杰,因为受了极为严重的伤势,对于战争心生惧意,准备逃回老家顺德。
不料上茅房的时候忽然间看到了一个黄色的包袱,他打开一看,里面是二百两银子。
他心想这肯定是谁丢下的,这么多钱都丢了,那人一定很难过。
于是他就蹲在茅房周围看着,过了没多久,就发现一个身穿短衫的大胡子着急的在茅房内外查找。
项世杰上前询问道:“这位大哥,敢问可是丢了什么东西?”
“是啊。”那大胡子道:“是一个黄色的包袱。”
项世杰把包袱拿了出来道:“可是这一个?”
大胡子把包袱打开,仔细一看,确实是自己的。
不过此人乃是一个奸商,最会四处投机取巧,坑蒙拐骗,以至于有不少仇家追杀他,若非如此,他也不会逃到这个兵荒马乱的地方。
他见项世杰老实,于是准备欺负他一下道:“包袱是我的没错,只不过我这包袱里明明有五百两银子,现如今怎么少了三百两?”
“这我就不知道了。”项世杰还不知已经上当了,仍是如实说道:“我从茅房里捡到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二百两银子,并未见其他东西。”
“可是只有你看到了我的包袱,难不成那三百两银子长翅膀飞了?”胡子责问道:“我看就是你贪心昧下了!”
“真没有!”项世杰有口说不清了道:“真的没有啊!”
“你让大家来评评理。”胡子吆唤道:“我的包袱里有五百两银子,刚刚掉在地上了,被捡起来再回到我手里就没了三百两,你们说这是谁偷的!”
“那有可能是捡的人拿的。”
“那不对,既然都捡了,怎么可能还想着还给别人?”
有中正的道:“我看谁也别说谁对谁错,去县衙问问大老爷怎么评判。”
大家一起起哄道:“走,去县衙!”
胡子一听说要去县衙,有些心虚道:“我看还是算了吧,这事就这么罢了,你得再给我一百两银子,不然等去了县衙,你可就没好果子吃了。”
“去就去,谁怕谁?”项世杰一咬牙道:“我就不信,这世上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说着,项世杰向县衙走去,胡子落在其后,其他人随着去看热闹。
“有意思。”天权本来在一处茶摊喝茶,歇歇脚再赶路,不料碰上了这一段小插曲。
他心里想着,不能让好人蒙冤受屈,于是追上去看看这县衙是怎么判的。
那县令生得精瘦,两眼昏暗无光,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看来战火折磨的官员都受不了了。
县令打了个哈欠,一拍惊堂木道:“下跪者何人!”
胡子又说了一遍道:“是小人不慎丢失了银两,被他捡到了,可是没想到却被他私自拿去了三百两,如今小人只剩二百两银子了,这让小人回家怎么交代啊!”
“你血口喷人!”项世杰恼火地道:“我明明只拿到二百两银子,哪有什么五百两银子?”
“你若是实在委屈,那不如当场搜身啊!”胡子道:“证明你的清白!”
项世杰忽然变了脸色,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仇恨,甚至还有一些恐慌。
县令见项世杰不肯吭声,以为他做贼心虚,于是审判道:“那谁偷拿胡子的三百两银子,赶紧尽数归还,退堂!”
项世杰双拳紧紧握住,从牙缝里吐出四个字:“我——没——偷——钱!”
“我可以证明!”天权忽然站了出来道:“这位仁兄绝对没偷钱!”
“哦?”县令道:“这位小道士,你且说来听听。”
“因为这包袱是我的!”天权道:“我正好带的是二百两银子,是我师尊给我下山请工匠修建三清祖师像的,结果在我出恭的时候不小心丢了。”
“你胡扯。”胡子不屑地道:“这银子明明是我的,怎么会是你丢的?”
“可是你丢的明明是五百两银子啊!”天权很是疑惑地道:“而这包袱里只有二百两银子,显然跟你所说的不一样,怎么会是你的?反而与我的极为相似,就连数目都一样啊!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一个包袱里装有五百两银子的包袱,而不是二百两银子,然后再把这二百两银子给我,让小道士好得以交差,不然我会被师傅责罚的!”
胡子被天权一阵抢白,顿时哑口无言,只能吹胡子瞪眼道:“你这小道士哪里来的!竟然胡说八道,这是我的包袱,里面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既然你都知道是五百两,那你为何还要认这二百两银子?”天权不解地道:“再者说了,天下间人都有长得一模一样的,更何况是包袱?你确定你没有看走眼?”
“当然没有!”胡子大怒道:“这二百两银子可是我从票号里取出来的!一路带到这里,岂能有假!”
“事情解决了。”天权耸了耸肩道:“这包袱从一开始就只有二百两银子对吧?”
胡子自知失言,恼羞成怒道:“算你狠!”
人们都哄笑道:“原来他才是坏人。”
县令判决道:“胡子恶意敲诈,来人啊,把他给我关进牢里去!退堂!”
衙役上前把胡子捆了起来,拖到了大牢里。
大家纷纷都对道士道:“这位小道长好机敏,不然一个好人就平白的被诬陷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得。”天权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发道:“不然没人帮忙,以后谁还敢做好事啊。”
项世杰上前拱手谢道:“多谢这位道长替在下解围,不知道长道号为何,在哪处宝山修行?”
天权报上了名号道:“贫道道号天权,在昆仑山玉虚宫修行。”
“昆仑山距离此地极为遥远啊!”项世杰问道:“道长为何来此地?”
天权道:“我奉师尊之令,要去京城一趟。”
“好巧啊!”项世杰道:“我要去顺德,正好同路,不然我们同行如何?”
天权想着自己第一次去京城,难免有些不熟悉的,于是答应了下来。
若是天权不去凑这个热闹,直接赶路,或许还来得及救夏言。
书说简短,这二人一路奔波,终于在中午时分到了京城。
不过夏言早就已经被害了,京城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那就是夏言的徒弟张居正直接临阵倒戈,加入了严嵩一党,并且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严世番。
此时京城内外无不痛斥张居正的为人,就是一个墙头草。
项世杰也是大怒道:“没想到夏言这么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竟然教出这种人,真是玷污了夏大人的名声!”
天权皱眉道:“这下可麻烦了,我师尊就是让我把信交给夏言啊,如今他都死了,可怎么办?”
“那不如我们拆开信件看一看。”项世杰道:“说不定我们还能为夏大人做点什么。”
天权犹豫再三道:“也好。”
二人进了一家茶坊,拆开信件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天权的身世!
“贫道极一参拜宰辅,一十六年前,贫道携其子真卿入山修行,如今时限已满,特遣其子送此信与宰辅大人,望一家成就围炉之乐。”
落款:昆仑山玉虚宫极一道人。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项世杰直接跪倒在地道:“竟不知道长是夏大人的儿子,请恕小人一路之上的无理!”
“快起来。”天权紧皱眉头,扶起来项世杰道:“不要这样,我只是一个道士罢了。”
项世杰道:“可是您是夏大人的儿子啊!理应为夏大人报仇!”
天权见有许多人都看向他们,对项世杰道:“我们去别的地方再说话。”
二人走出了城,项世杰低声道:“公子,不说别的,夏大人这一生都在和这些奸党做斗争,您难道能够眼睁睁看着奸党乱了朝廷而无动于衷吗?”
天权极为头疼地道:“我也很想对付严嵩,只不过我势单力孤,又怎么去对付他?”
“不管怎么说,夏大人生前都有几个好友。”项世杰道:“依我看不如找他们去。”
天权点了点头道:“好!”
项世杰凭着记忆,说了几个人名,天权依次找去,可是还没进门就被赶来出来。
要知道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就连兵部尚书和边疆大吏都被贬官了,谁还敢再掺和此事?
要知道昔年的胡惟庸案牵扯了多少人?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能被判刑,就连开国功臣李善长都被满门抄斩,唯有一个独子活了下来,然后被发配了。
所以他们只要一听说来人是夏言的儿子,都跟避瘟神一样躲着他,甚至连夜出城。
“这些人真是势力!”项世杰愤怒地道:“当年夏大人没少帮他们,可如今出了事,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罢了,也不能怪他们,毕竟他们也要活下去。”天权无奈地道:“我听说我娘亲还在,我决定去找我娘,侍奉她过完下半辈子。”
天权还想问项世杰有什么打算,却看到他慌忙躲了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什么恶魔一样。
这时,一个鲜衣怒马的锦衣卫来到了天权身旁道:“你是哪里来的道士,不知道规矩吗?”
天权问道:“什么规矩?”
“按照大明律法。”那锦衣卫道:“凡是在京城的道士都应该着红道衣、金襕,可是你却一身青色道袍,这不是有违律法?还不快快伏法认罪!”
按照洪武十四年的诏令,只有在京城为官的道士才需要这么穿,而天权并没有官职,所以他着青袍并不算触犯律条。
可以说只要不是当官的道士,想怎么穿都行,根本没人管。而这个锦衣卫就有些无理取闹了。
天权本来不想理他,不过他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话,让天权立刻跟他走了。
“夏公子,随卑职来一趟,我家大人有要事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