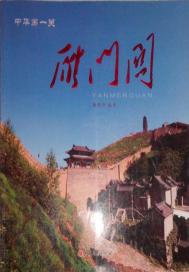岳飞无奈收回了手臂,坐在边上默默的想起了心事。
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一心求醉的岳震,却是越喝越觉清醒,仿佛牛饮鲸吸进去的醇酒,只是白水一样。
掌柜的在一旁摇头不止,暗道,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本领。震少这样的酒量,自己这群手下能站着走回去的,恐怕是寥寥无几喽。
果然不出所料,又是几轮推杯换盏,‘闵浙居’已经有人砰然倒地,醉态可掬溅起来一阵欢声笑语。环视桌上,反而是那几位自认不行的却还安坐在椅上。掌柜的眼色丢过去,几人纷纷起身,扶着东倒西歪的同伴向岳家父子请辞离去。
院子里安静下来,失去了对手的岳震没办法,只好自斟自饮。
抬头看看月色依旧银闪闪的,岳飞估摸时间已经不早了。“小二,天色已晚。人家掌柜忙碌整日,也该安歇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掌柜的一旁接口道:“不妨事的,岳元帅,您要是累了就先去休息吧。在下还有些事儿,相与震少聊一聊。
岳家父子同时一怔,本来有话想和儿子说说的岳飞暗想,看来只能等明天啦。
岳震放下手中的酒碗,笑道:“掌柜的有什么话,但说无妨,我的事没什么好瞒着父亲。老爸您若是不困,不妨坐下来一起听听。”
留下来肯定会让掌柜的为难,立刻就走又显得不给儿子留面子。踌躇间,岳飞眼珠一转岔开了话题,呵呵笑道:“老爸?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有人叫老子,也有人称老爹,你且给我说说,这个‘老爸’是从那里来地。”
父亲摆明车马,不想参与自己的事情。岳震也不好勉强,只能跟着插科打诨道:“这有什么好稀奇,这是对您无声地抗议,谁让您老是小二、小二的叫我来着。”
“哈哈哈···老爸,我喜欢!”岳飞大笑起身说:“听起来如乡野俚语,蛮亲切。为父准你以后就这么叫啦。早睡早起,明天为··不,老爸还有事和你商量呢。”
岳震和掌柜的站起来,目送着哈哈大笑的岳飞,看到那边过来一个伙计指引着岳元帅向客房而去,两人这才回身落座。
“申屠大老板,现在只有你、我二人。”岳震目光炯炯盯着掌柜的,“阁下这些日子煞费苦心,为了小弟跑前跑后,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掌柜的微微一惊,旋即摇头笑道:“原想着瞒不过震少,可是还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你知道了我的身份。在下猜,一定是钟捕头邀功心切,言谈话语间露出了马脚。震少果然够聪明,在下没有看错你。”
岳震不置可否的淡然一笑,仔细的端详着他的面部表情,好像是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些蛛丝马迹。
明亮的月光洒落院中,视线与白天相差无几。可是岳震仍然觉着对面这个人,浑身上下都透着神秘,仿佛是隐藏在团团迷雾之中。
从面貌上,岳震很难推断掌柜的实际年龄。白净略长的脸型,南方人特有的高颧骨和宽大的额头。一双眼睛好似深不见底的潭水,古井无波,深邃而宁静。
“震少有没有兴趣猜一猜,在下如此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越是看不透,岳震的警惕之心就越重。看到掌柜眼神中的几分狡诘,他不禁生出些恼怒,脸色一沉,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哈哈哈···”掌柜的闻听不以为许,反而仰天大笑。搞的岳震非常郁闷,好像是一拳打在了棉絮上,空荡荡说不出的难受。收起笑容,掌柜也摆出一付正经八百的面孔,说出来的话却依旧是莫明其妙不着边际。
“在下已经观察震少你很久了,今个跟你说实话吧。在下自认阅人无数,可像震少这般年纪,能让在下看不透的,迄今为止只你一人而已。”
岳震听到不由暗暗失笑,我的神奇经历,你要是能看穿了,那不成了神仙喽。原来咱俩是彼此彼此啊。
掌柜的看到岳震微微有了些暖意,也是轻轻一笑,接着说道。
“以震少的年龄和显赫的背景,不外乎几种情形。纨绔不羁为祸乡里者有之;方正不阿胸怀大志者也不以为奇;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却男盗女娼的少年奸雄虽不常见,但在下也不是没有碰到过。唯有震少你,唉···”
说到这里,掌柜的不由仰天长叹,黯然说:“在下实在是堪不透呐!”
看到他苦恼的样子,岳震心中升起几分快意。翘起了嘴角问道:“申屠大老板,不会是因为想看破我,你才下这么大的辛苦吧?”
“起初就是这个原因。”申屠掌柜一本正经的和他对视着,“可这时日一长,还有后来的一些变故,使得在下改变了初衷。”
“哦?”岳震扬起了眉毛,不知不觉间被他勾起了好奇心。
“震少你自己或许都没有发觉,你天生就有着领袖的气质。岳元帅的影响力,固然有一部分原因,但震少你骨子里的坦诚和义气这才是主要的。因此你就如一块磁石将许多人吸引到你的身边,这其中的年轻人都是想跟着你作一番大事业的。”
岳震被人家夸的有些面皮发烧,挠着后脑勺赫然说:“这算什么领袖气质,对朋友够义气、实实在在,很多人也都能做到的。”
申屠掌柜深以为然的点头道:“不错,所以震少你吸引我的地方,不在于此,而在于你够朋友、够义气,但做起事来却往往出人意表,离经叛道。”
“一幅籍籍无名的《将军饮马图》,被你震少一番造势,就卖到了天价。你若一味的讲义气,这画恐怕早就被拿到宗老帅的坟前烧掉了,哪来整船整船的军粮运往鄂州?”
一股凉气从岳震的后背串上来,让他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自己的一举一动尽在人家的掌握之中,这样的感觉实在是不妙。他脸上的变化,让掌柜的看出了他的心思,摇头笑道:“震少不用担心,等你清楚了在下究竟是什么人,自然也就明白我为何会知道的这么多。”
“呼···”岳震深吸一口,稳住了心神,平静的注视着申屠掌柜。
“好吧,话已经说的够多了,阁下也该交待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人,蓄意接近本人到底有何用意?”
掌柜的一拍桌子站起来,“好,就让咱们一件一件的来说。”
说着话,他绕过了长桌到了岳震的身前,二话没说,撩袍扑通跪到了地上。
岳震先是一愣,尔后深深的锁紧了眉头。经过白天的事情,他对古人这种动辄就要下跪的作风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他却没有搀起申屠老板,只是抱臂眼睁睁的看着,看着申屠老板砰砰的在地上磕了三记响头。
“狗官刘倬虽不是死在公子的手里,但震少与贵友功不可没。请公子受我申屠希侃三拜,这是替那些死去的亲人,答谢公子为我申屠一家报了血海深仇。”
听到他声音颤动,语带悲愤,不像作伪的模样,岳震这才伸手拉起了他。
“掌柜的,你的大名是申屠希侃?”
申屠老板顺手拉过凳子坐在岳震的身旁,点头回答说:“不错,在下全名,申屠希侃,福建侯官县人氏。震少现在定是一头雾水,莫急,且听希侃慢慢道来。”
这一幕人间惨剧,发生在十几年前的闵境。
申屠家不算大富大贵,但以诗礼传家,渔耕为业,却也颇为殷实。家主申屠虔,早年就失去了老伴,辛辛苦苦的将一双儿女养育成人。长子,申屠希侃,自小就立志要做一个大商人,年龄稍大一些便常年奔波在外,生意也是做的蒸蒸日上,颇具规模。
申屠老人的宝贝疙瘩,自然就是女儿,申屠希光。这个女孩不仅貌美如花,温顺善良,更是远近知名的才女。
希光踏青春游时,与临县的才子董昌相遇,两人一见倾心,生出了彼此间的爱慕之情。希光回家禀明老父,申屠虔便将宝贝女儿许配给了董昌。
隔年二人完婚,申屠希光随丈夫回到了临县长乐。小两口恩恩爱爱,举案齐眉,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后来小家庭又添麟儿,把个申屠老人乐的成天合不拢嘴。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灭顶的灾难,降临到这家人的头上。
董昌误交一损友,此人姓方,全名,方六一。董昌家中时常聚些文友,一起吟诗作赋,方六一也是常客之一。久而久之,这贼子垂涎申屠希光的美色,便起了霸占**的歹心。
方六一先后买通了当时的长乐县令刘倬,以及书记,一干捕头、衙役等等。然后他又花钱雇了些泼皮无赖冒充泉州海匪,作下了一连串陷害董昌的伪证。直到锒铛入狱时,可怜的书生董昌依旧蒙在鼓里。
奸计得逞,方六一又时常跑来嘘寒问暖,让申屠希光觉得丈夫这个朋友,人还不错。
而狱中的董昌,拼死也不肯承认他们捏造的罪状,最后活活的被折磨致死,还被定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噩耗传来,申屠老人一病不起,希光更觉天塌了一般,急忙托人给哥哥捎信。
董昌下葬不久,方六一便托媒婆上门求亲。申屠希光痛斥之余,也琢磨出来这里面不对劲,聪明的女人起了疑心。希光散尽了家财,多方求证打听,终于被她得知了事情的真相。悲愤之中,申屠希光冷静下来,开始一步步的实行自己的复仇计划。
方六一贼心不死,再次找人上门,却不料申屠希光竟答应了。方贼子欣喜若狂的筹办婚事,却不知自己已经踏上了黄泉路。
成婚之夜,申屠希光灌醉了方六一,拿出准备好的利刃,割下了仇人的头颅。
女人用大红的吉服包着那颗罪恶的脑袋,来到丈夫董昌的坟前。她没有哭泣,只是静静的坐在那里,久久的摸挲着墓碑上那个亲切的名字。直到发现血案的公差,沿着一路沥沥的血迹追到了坟地。
县令刘倬,害怕有人追查此案,迅速的给申屠希光定了通匪、杀人的罪名斩首于闹市。风烛残年的申屠老人怎堪连番的打击,随后追寻着爱女的一缕幽魂,含恨辞世。
可怜申屠希侃,日夜兼程的赶到妹妹家时,看到的是三个新土堆砌的坟茔,听到的是六岁小外甥走失的消息。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晴天霹雳在耳旁炸响,一口鲜红的液体喷射而出,七尺男儿昏死在亲人们的坟头。
诉说的人娓娓而谈,无悲无愤,平静的宛如说着毫不相干的事情。
闻者却不能不动容。好一个知情重义的刚烈女子!想到如此善良的一家,却落了个如此悲惨的下场,岳震不由得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砰!”岳震一拳狠狠的砸在桌上,汤汤水水溅起来老高。他一脚将椅子踢到一旁,怒不可遏的站起身。“狗官!天杀的狗官!若早知道他是这样一个草菅人命的狗官,本少爷一定要打爆刘倬的狗头!嗯···气死我啦!”
“震少息怒,普天之下境遇凄惨者,何止我妹妹一家人?”申屠希侃淡淡的劝说道。
“你···”岳震一指他,不觉气就不打一处来。冷哼道:“哼!旁人我管不了。如若这样事落在我身上,本少定要杀他个血流成河,山川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