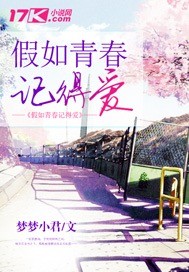“嘿嘿嘿···”岳云、岳雷也跟着父亲表情古怪的笑起来。
银屏粉脸羞得通红,跺脚娇嗔道:“不理你们啦,我去给爹爹收拾东西。”
冲着大姐跑出去的背影,云少帅起哄道:“大姐,你就在家里等着做新娘子吧。”
“哈哈哈···”父子三人开心的大笑起来。
此刻岳震正有滋有味的嚼着干巴巴的窝头,四处打量着牢里的环境。
记得来的时候曾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大约一丈见方的牢笼应该是列在甬道的两边。自己身处甬道的尽头,而且还拐了个弯,所以看不到外面的情形,只能隐约听到狱卒的喝骂之声,偶尔还有一两声粗瓷大碗落地的声音。
‘我住的可能是个单间吧’
岳震扬脖灌了口清水,暗笑道,恐怕这里面还有钟达永的功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倒是愿意和别的犯人住在一起,他真还想看看传闻里的牢头狱霸,是何等的凶神恶煞。
想曹操,曹操就到。岳震刚放下粗瓷碗,钟捕头就来到了牢门前,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看到岳震将最后一块窝头放进嘴里,开门进来的钟达永急声道:“罪过,罪过。申屠老板一再叮嘱,不可让岳掌柜受了委屈,这··这是钟某的疏忽。”
一通辩白后,他转身对跟着那人说:“何兄快请进来,兄来的正是时候,怎能让岳掌柜用这些粗陋之食。”
乍一看进来之人青衣小帽,岳震还以为他是那家的仆随,待仔细的看清楚面容后,岳震立刻推翻了心中的猜想。此人虽衣衫普通之极,但生的气宇轩昂满脸正气,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浓眉大眼,尤其是宽大的额头格外引人注目。
来人放下手中的食盒,对钟捕头抱拳道:“多谢钟捕通融,何某想与这位小兄弟说几句,不知···”
“请便,请便。你我同衙为官,何兄不必这般客气。”钟达永笑答着:“今日正好兄弟当值,你们想聊多久都没关系。何兄,岳掌柜,钟某先告退了。”
钟捕头带上门离去,来人笑吟吟的打量着岳震,自我介绍起来。
“在下姓何名铸,大理寺派到临安府的检审主薄。呵呵··岳公子不用猜疑,你我素未平生,这是首次相见,何某此来,不是为了案情,是有些私人的事情想问问,略备些吃食,不成敬意。公子请···”
岳震一头雾水的看着何铸打开食盒,摆放着食物,心里犯开了思量。
大理寺以前听说过,貌似现代社会中的最高法院。但检审主薄这个官职就陌生的很了,他能有什么私事要问?。
一脑门问号的岳震,面色却也平静,与何铸面对面席地而坐,想听听他究竟是何来意。
“何某唐突了。”两人坐定,何铸开口道:“不知岳公子家乡那里,家里可有什么人在朝为官?公子与李易安有何关系?”
岳震淡然一笑,反问说:“何大人这算审问,还是私下闲聊呢?”
何铸赶忙摆手说:“公子不要误会,在下不是受什么人指示,来探口风。”说罢,他略一沉吟接着讲到:“在下本来只是例行公事,翻看今日府衙的捕人公文,无意中翻到了公子的案子,才知道此案与易安大家有牵连。在下平日酷爱诗词歌赋,对李大家的词句更是推崇万分,所以···”
‘哦··’岳震这才明白了,原来这个人是李清照诗词的爱好者,用现在的话来讲,是阿姨的铁杆粉丝啊。
“呵呵···原来如此。”岳震开心的笑道:“原来何大人也是文雅之仕,喜爱易安阿姨的妙语佳句。”
何铸猛点其头,“是极,是极,听公子此言,莫非与在下嗜好相投?”
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关系自然就拉近了很多,岳震也乐于有人陪他聊天,就与何铸在诗词上探讨起来。而他对宋代诗词的印象,大多是从赏析中看来的,这些后世出版的赏析,收集了几百年文人对宋词的深刻理解。这些闻所未闻的评析,经他口中说出来,令闻者何铸,如饮琼浆玉液,乐陶陶之中顿觉相遇知音。
“公子高论呐,在下佩服,佩服。”何铸不胜感慨的说道:“公子年纪轻轻,却胸怀锦绣,若要因为官司阻碍了前程,实在可惜,可惜呀。”
岳震依旧那付平静自然的模样,模棱两可的应付说:“多谢何大人关爱之情,是非曲直自有公道。”
何铸见他好像与己无关的样子,忍不住善意的提醒起来。
“话虽如此,可官字两张口啊,更何况公子不明白这里面的私情交织。”
“哦?何大人可愿据实相告?”岳震听他说的这么严重,好奇之余也想有个心里准备。
何铸踌躇了好久,才一拍大腿道:“罢了!岳公子雅量高洁,何某怎忍你蒙在鼓里,不明不白的被人害了!方才我看过案卷后,特意去通判大人那里相询,对原告那边的情形略有些了解,公子这次惹上大麻烦。”
“不就是已被罢免的枢密院知事汪伯彦吗,他一个罢相还能只手遮天?”岳震笑着摇头。
“汪伯彦贪婪成性固然麻烦,但还不是最可虑的。”何铸觉着既然开了头,也就豁出去了,一五一十的说起来。
“圣上南渡后,汪、黄就一直是拍档,后来因为禁军哗变双双被贬。但黄潜善此人不可小觑,他与现今的枢密院知事赵鼎,即是同乡还有姻亲,关系不同一般呐。”
岳震一愣,不觉有些意外。赵鼎,实际意义上的国家总理,这事要和他牵连上,还真就麻烦啦。虽然早对官场上盘根错结的关系网有些耳闻,可他还是想不到,怎么拐来拐去,拐到了当朝宰相的身上。
见他皱起了眉头沉默无语,何铸也失去了说话的兴致站了起来。
“在下官卑言微,也只能与公子讲这么多啦,要是公子有亲眷在朝里,需要传递消息,何某义不容辞。公子休息吧,何某告退。”
岳震这才猛然惊醒,忙站起来抱拳相送。
“多谢一番提点,如有劳烦何大人的地方,小弟一定不客气。何大人请走好··”
鄂州城外,码头。
一艘船体狭窄的军用快船已整装待发。
岳飞脱去戎装一身常服,站在船头,对着岸上的三个儿女道:“此事万万不可让你们娘亲知道,小二煞费苦心弄出了‘孔明车’,若是···”岳帅不禁有些烦闷,挥手道:“不说了,都回去吧!”
“爹爹,且慢。”银屏见父亲转身要入舱,情急之下也顾不上什么矜持了。
“屏儿,还有什么事不妥?”岳元帅闻听回身,对女儿的意见,岳飞一向都很重视。
往日果敢干练的岳小姐,却意外的忸怩起来。
元帅猜出了个大概,不忍乖女儿受窘,便对岳云两兄弟道:“云儿,雷子,你们骑马先回去吧,以防被你娘看出破绽。告知亲兵队,晚一点再护送小姐回去。”
看着弟弟们打马飞奔的背影,银屏小姐抑住了羞意,郑重的对父亲说:“爹爹,小弟的事情完了,让小弟去见见张宪,如若小弟满意,女儿也不会反对,爹爹就把他调回鄂州。若是小弟觉着张宪不甚可靠,这件事,就休要再提了。”
说罢岳小姐丢下一脸愕然的父亲,含羞跑向了远处的亲兵卫队。
直到亲卫护着女儿的一行人消失在夜色里,岳飞才回过神来,挥手下令开船之际,苦笑着暗想道。
怪不得银屏迟迟不肯答应,原来是想听听小二的意见呐。小二呀,小二,哥哥姐姐都说你今非昔比了,为父也想早点见到你啊。
小船飞快的划破了破浪,船头上屹立的,不再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只是一位牵挂着孩子的父亲。父亲深邃的眼神,仿佛要刺破浓重的夜色,一直望到了远方的都城。
临安皇宫,养心殿,御书房。
“坐吧,十弟,也没有外人了。”高宗疲倦的倚在龙椅上,指指边上的锦墩。
福王默然坐下,垂下眼睛看着脚边花团锦簇的地毯,诺大一个书房悄然无声。
“唉,朕知道,在福丫头的事情上,你心里在怪我。”赵构虚弱的合上眼睛,怅然道:“看到丫头现在这个样子,朕心里也不好受呀。”
福王依旧沉默无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赵构换了姿势,也没有睁开眼睛,接着说:“朕这个皇位,是五哥夫妻牺牲了一辈子的自由换来地;也是你,十弟抛却了一生的幸福换来地;如今,五哥的后人不开心,十弟你也不痛快。朕这个皇帝做的还真失败呢。”
福亲王抬起头看着哥哥,嘴巴张了又张,喉结颤动着,却又垂下头去。
九哥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赵榛的心房。他一时间想到九哥的诸般难处,便觉心如刀绞。
禁军之变当夜,九哥失去了唯一的皇子,却依然要整夜的屹立于皇宫城头,不能有半分的悲戚颜色。
今年粮价暴涨,九哥夜不成寐,呕心沥血,发文督办各地调粮来江南。每天傍晚开始批阅奏章,查看比对各地粮价,然后再行文督促各部,将粮食运往粮价居高不下的地方。往往是天光大亮时,才算告一段落。
福王悉数着皇帝的种种,不可抑制的羞愧涌上心头,王爷抬起微红的双眼动情道。
“九哥,你不必说了,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当年我自残身躯入‘残门’时,就已经想的明明白白。哥哥你说的对,生于帝王之家,就失去了退缩与悲伤的权力,几十年来,弟弟不曾有一丝的后悔。我想,即便是五哥身陷虎狼之狱,也与弟一样,无怨无悔。”
赵构闻言,轻轻的睁开了双眼,凝视着金壁辉煌的屋顶,幽幽叹道。
“是啊,转眼间,朕登基也快十年了,每每想起太祖打下的这片如画的江山,活生生的被人扯去了一半,朕···”
福王猛的站起身,‘噗通’跪在龙书案前。“九哥!弟知道错了!当年五哥临走时,不是说过吗,半壁还是江山,我大宋这半壁江山,还得九哥你来支撑呐。”
听到弟弟的话里,已经隐约有了泣声,赵构急忙起身绕过来拉起兄弟。
“十弟,你这是做什么!?你我兄弟说说知心话,相互倒倒苦水而已,你还怕哥哥撂挑子不成?来来来,快坐下。九哥知道,你对朕另立一支新军取代‘招讨府’,心里不痛快。早就应该和你商量的,只是近日···”
本来想顺势坐下的福王,又直起身肃容道:“招讨府现今弊端多多,弟难辞其咎。九哥你如何处置,弟都决无怨言。”
“你看,你看,又来了。”皇上见亲弟弟一大把年纪,还和年轻时一样的执拗,忍不住笑出了声。
“呵呵··你有什么咎?朕是府主呐。”说着,皇上搂着兄弟的肩膀,哥俩并排坐在了锦墩上。“十弟,你想想,现如今的招讨府,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咱们还能靠这样大白于天下的机构做什么事?所以,朕才忙里偷闲,组建了这支新力量。老规矩,还和当年一样,筹建归我,剩下的领导运作就是你的事情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