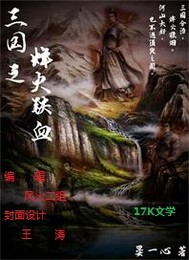想到身后的人不仅是柔福的长辈亲人,还是大宋朝手握权柄的重量级人物,自己这样的态度人家未必理解。岳震只好收起复杂的心绪,转身施礼说:“晚辈代敝友多谢师太和诸位前辈的回护之情,这位前辈可是?···”
总管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语,岳震只好把后半句‘柔福的叔父’咽回肚里。
“我率众前来只为拦截土古论,既然强敌已退我们也是时候回去交差了。至于其他的话嘛,此时此地不宜谈起,我们给岳公子留下一艘小艇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望着三人离去的背影,岳震才琢磨过味来,有些事情柔福的叔父未必想让王渊知道,尤其是自己和柔福的这层关系。
唉,有了诸多感情、名利等等牵绊,那能像土尊者那样来去自如,潇潇洒洒?。
直到小船上的禄伯挥手叫他,岳震才离开了这片难忘的战场,登上了两位左护军水手驾驶的小艇。
一路上水手们看岳震的眼神犹若仰视神明,能与击败金人第一强者的少侠同船而渡,恐怕将是这两个普通士卒终生都引以为傲的话题。禄伯则笑眯眯的看着自家公子,细心的老伯发觉战后的公子与战前相比,身上多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气质,俨然已从一个半大孩子中脱胎换骨了,举手投足间凛凛然,不怒自威。
岳震却没有注意到别人的神态,他从脖子上摘下‘聚灵珠’把玩在手里,把这一夜的经历认真的梳理梳理。
‘聚灵珠’虽然依旧入手很沉,但颜色已经淡了许多,圆润的表面上只留下淡淡的棕色纹路。握在掌心里隐约还能感觉到一些残留的灵气。
珠内的灵气仿佛也感应到岳震的气息,顿时欢快的流淌起来,像一群等待召唤的士兵准备着随时流进岳震的身体。
不忍将珠子里的灵气吸食一空,他将‘聚灵珠’套回脖颈陷入了深思。
因为战船已损,刘子翼和手下扈从们只得弃船登岸,从陆路策马赶奔临安,当然一路上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刚刚惊天动地的一战。
总管和师妹入城后就分手,静真已是一天一夜未回妙明寺,说不担心留在寺里的柔福那是假的。总管与王渊一行则沿着内河一路向南,过了保佑坊,东岸的福王府遥遥在望时,飞驶的小艇才减速放慢下来。
呼啦啦一群人拥进了王府的偏门后,厚实沉重的木门又砰然合住,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未发生。
天光大亮街上渐渐热闹起来,福王府朱红的大门轰然开启,三三两两的侍卫军官们走出大门。有心人看到这里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军官不正是昨晚那群黑衣人吗?街道两旁的行人也不禁为之侧目,淡灰色的制式军服以及他们腰上悬着的红缨腰刀,都表明了他们的身份,这是大宋京都里最神秘的一支军队,皇家禁卫军。
王渊是最后一个离开王府的,接过马僮手里的缰绳他飞身上马而去,满脸的疲惫却也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
谁也不会注意到王府的侧门悄然驶出了一辆马车,两匹俊秀的白马牵引着车厢轻快的跑进了大内禁城。
内城门外车帘高挑,福亲王赵榛赫然而出,立刻引得侍卫宦官们跪倒了一片,赵榛微微有些不耐的摆手匆匆而去。
王爷去后这班闲极无聊的小子,自然又是一番胡乱猜测议论纷纷。有个说,今个稀罕哎,平日病病歪歪的福王爷这么大早就进宫。那个惴惴不安的猜道,你们发觉了吗?王爷他一脸倦容,好像熬了整宿,是不是有大事啦!立时有个小太监凑过来嗤之以鼻,能有甚大事?最多是该杀的金人又派使节来喽,福王不是张罗着礼部那一摊子事吗。
岳震进城后没有随禄伯回后市街,而从保佑坊下船直奔了‘闽浙居’。
穿过前厅饭堂走进客房后院,抬眼就看到‘闽浙居’的掌柜站在那里含笑望着他。岳震心中微微一动,暗道,这可是个人物啊!不显山不露水间把生意做遍了大江南北。
“岳公子早哇,公子风尘仆仆可是刚从外阜赶回来?”想上前打个招呼,当岳震措词的功夫,人家掌柜的已经笑呵呵的开口了。
“掌柜的好眼力,呵呵···琐事缠身奔波劳碌,这不想借朋友的地方梳洗一下,让您见笑喽。”
掌柜的依旧笑容可鞠,待岳震走到近前两人将要擦身而过时,他压低了声音说:“贵友们正在打点行装,岳公子可有时间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岳震微微一愕,不过得知宗铣他们还没走也就放下心来,便轻声应了一句“愿听掌柜的赐教。”两人也没有走远,并肩漫步到了厢房的回廊下,掌柜的伸出一只手来逗弄着廊上挂的一只鸟儿,看似漫不经心语气却分外凝重。
“昨夜有人在贵友的住处做了暗记,我已差人悄悄的掩去,但还是隐约觉着有人在监视公子的朋友。天快亮时这些人才分头撤走,公子与贵友可要多加提防噢。”
微笑看着唧唧喳喳的小鸟,岳震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土古论不远千里的来杀宗铣,肯定会有人给他做好准备工作,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他觉着好奇的是,这位掌柜的哪来这么高的警惕性,和自己说这番话又有什么深意呢?。
看到岳公子波澜不惊的表情,掌柜的肯定了心里的揣测,外边的麻烦肯定已被这位公子解决掉了,也就是说一切尽在人家的掌握之中。
想到这些,掌柜的忍不住放下了手臂,再次认真的端详着岳震。
这一细看不要紧,阅人无数的掌柜不免一阵心惊眼跳。
上几次见到这位公子,只是觉着他干练沉稳,身上没有同龄人的轻狂或幼稚,还有就是掌柜最欣赏的书卷之气,虽然这份儒雅深深的隐在岳公子眉宇之间,但还是让掌柜的心生亲切和结交之意。
可短短的几日不见,也不知这位公子经历了什么,怎么会有这样显著的变化?他只是轻松自然的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如遇巍山峻岭,强者之息逼人心魄。
猛听到掌柜的呼吸粗重起来,岳震疑惑的转眼看去,只见到他一付愕然失神的模样,岳震笑道。
“多谢掌柜好意提醒,我今天来就是要挽留朋友们多住几日。不过您放心,小弟保证不会给贵店惹麻烦的。呵呵···您忙,小弟先走一步。”
望着少年渐渐远去的身影,掌柜的这才回复了常态若有所思。
进到宗铣他们的房间,见方小七几兄弟都已收拾利索,显然是准备出发了。小七见岳震来到还颇为惊诧,一问才知道宗铣和晏彪一早就出门,说是去‘佛缘阁’与震少道个别,等他们回来弟兄几个就要启程去鄂州,以安排晏家军余部赶赴河北。
直到证实宗铣平安无事,岳震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回肚里。暗自琢磨着,看来土古论所说的‘金龙秘谍’只是负责为他寻找目标,并未直接参与行动。
细细想来这也在情理之中,金人的密探必定费尽了诸般周折才掩藏下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暴露的。看来有战争的地方,就一定有谍报战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庆幸之余岳震也不禁有几分后怕,要是自己没听禄伯的在水军大营多停留一日,如果得知土古论不会危害皇帝,‘招讨府’会拼个全军覆没来阻挡他吗?。
岳震心不在焉的胡思乱想间,宗铣二人回来啦。方小七、闵小八几个一眼就看出来宗大哥精神恍惚大为奇怪,齐齐看向晏彪,彪子则耸肩摊手带摇头一付‘我也不知道’的模样。岳震心里明白,暗笑道,肯定是禄伯提起昨晚的事情,这小子和自己一样正后怕呢。
回到房里宗铣坐在那里呆了好久,才猛然一拍桌子长叹道:“唉,运数啊!我宗家不该绝后,俺宗铣命不该绝!”
晏彪众人一听生死攸关的大事,忙七嘴八舌的问起来。
宗铣一指旁边怪笑的岳震说:“几位兄弟还是问问咱们这位‘大宋朝第一高手’,让他说说昨晚发生的事情吧。”
众人顿时哄堂大笑,虽说震少是弟兄们当中身手最好的一个,可这么大的帽子他恐怕还戴不上吧?小哥几个以为宗大哥又在趁机调侃岳震,方小七更是夸张的一边前仰后合,一边对着岳震挤眉弄眼。
“不许笑!”宗铣一付痛心疾首状仰天长叹。“老天何其不公啊!这小子整天的吊儿郎当却狗屎运当头,天道不公呐不公。”
岳震闻听忍不住笑骂道:“好个白眼狼!本少跟人拼的要死要活,你却在这里大放厥词,本少忙的快脚不沾地啦,那有时间浪荡。”
晏彪在旁边听出了味道,忙制止这班兄弟继续起哄,认真的问起了宗铣。
宗铣把从禄伯那里听来的复述一遍,不外乎岳震如何神勇打退了土古论等等。
岳震在一旁听完,摇头笑道:“呵呵··禄伯只是在事后听那些侍卫们瞎议论,其中的过程哪有他们说的那么轻松?首先人家土尊者碍于身份,不愿使出全力欺负咱这样的后辈小子。再者人到了尊者那般年岁大多爱惜羽毛,你们想,他赢了我天经地义,搞不好还要落个以大欺小的坏名声。也就是说,从始至终土古论压根就没有必胜的欲望。”
“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宗铣也摇头说:“你们身在江南,对土古论这个名字没有切身的体会,那是女真人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啊!”
晏彪众兄弟搞清楚事情的始末顿时一片哗然,方小七更是兴奋的上蹿下跳,就好像自己打败了强敌一样,逼着岳震又把经过说了一遍。
挥手让兴高采烈的兄弟们安静下来,宗铣面带忧色道:“我知道小岳你是情非得已,可这么一来就等于是把你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今后将后患无穷呐。”
方小七一挺小胸脯不以为然。“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震少现在神功盖世,金人不服气尽管来啊。”
这一帮兄弟中还数晏彪最为成熟,他比较赞同宗铣的观点,但还是心存一丝侥幸,开口问道:“宗哥你说,土古论在女真部屹立近百年不倒,这么丢脸的事他会四处宣扬吗?我想他肯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找个其他的理由搪塞了事。”
“不会。”岳震首先否定了他的猜想:“以尊者的性格来讲,他回去后一定从实道来。不过宗哥你是不是有些过虑了,金人会因为此事再派人来吗?”
宗铣沉重的摇头说:“小岳你不明白,我不是担心金人再来找你的麻烦,而是觉得今后你在临安的处境堪忧啊。”
岳震心中悚然一惊,明白了宗铣所说的意思。是啊,自己的种种作为已经瞒不了赵家的人,而封建帝王对待人才的策略向来都是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必除之!
想到这些他不禁愁锁眉头,暗暗分析起来。也许现在有父亲这一层关系,朝廷还暂时能够隐忍,但能忍多久呢?最可虑的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很可能会加速父亲与皇家的破裂,他们决不会长期容忍像自己这样的人,且是无法控制的。
最后岳震还是忍不住想到了柔福,两人本来就有些阴影的前景,因为这次突发的事件,更加如乌云盖顶,充满了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