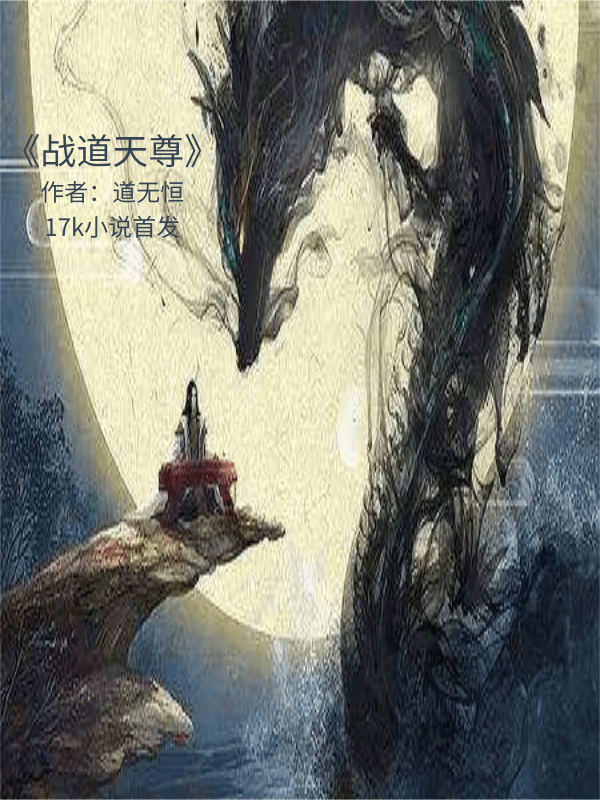梅娘手指成花,飘然生长,冒到无鼻道人眼前。这是一计杀手,也是司徒江与梅娘盼到的第一个机会。
梅花指。梅娘最拿手的功夫,梅花坚韧,屹立于寒冬之上。所以梅花下手也很重,很寒,寒到人的骨子里去。
无鼻道人阁起左手去挡,手上却只有半分力气。梅花落在手上,泛起片片紫红。
是血,无鼻道人的血。
他终究抵挡不住了。整个手掌被切落,切口圆滑平整,就好像是世上最锋利的刃切开的,血从伤口喷涌而出,渐在冰冷的石板上。
痛楚如大江涛流袭来,无鼻道人却面不改色,反而眼中带光。这份疼痛惊醒了他,更让他警觉,将他剩余的潜力统统激发出来。
梅娘悄悄退后几步,脱离战局。她可不想让这肮脏的鲜血沾染到自己身上。以司徒江的本事,制服少一只手的无鼻道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再切了二十招,无鼻道人被压住,终于跌在地上。他看着司徒江,看着司徒江即将对他下的杀手。他那张没有鼻子的脸孔仿佛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就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司徒江的手忽然化身为最利的茅,要穿透无鼻道人的胸膛。
也就在这一刻,李有财动了。
他一直睁着的眼睛却悄然闭上了。为什么要闭上眼睛,难道他不忍心看到无鼻道人惨死的模样?
当然不是,有时候闭上眼比睁开眼要更加的从容。他已然记下场景中的一切,左手银针飞出,右手前探,跟着身子像是一个弹簧一样,突然迸发。
这一切行云流水,旁人看了感受不到一丝瑕疵。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几乎做到最简、最快,而且极为精准。
司徒江的手突然收回了,他自然感受到李有财给他带来的压力。银针来的太快,还有两根是瞄着他的眼珠来的,这个情景下,他绝无可能避开。
忽然,他的身子十分不规则的一侧,整个身子几乎都扭转过来,躲过所有射向其身子的银针。与此同时,大手一挥,抓下朝其面部而来的银针。司徒江不愧是司徒江,在旁人看来近乎不可能的事,他却做到了。
但李有财也不简单,早知自己手中的银针伤不到他,所以他的杀手在剑上。银丝剑仿佛没有了剑身,李有财就像是一个疯子,提着剑柄刺来的疯子。
疯子有时候却会给正常人造成出乎意料的伤害。
剑到了。又好像没到。
看起来眼花缭乱,不知虚实。
司徒江忽然发现,就连自己也看不透。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只看到李有财的身影不断靠近,却不能辨别剑的位置。只觉得李有财手中的剑,忽近忽远,时而刺落,时而上挑。如果李有财手上是一只鸡腿,那没有人会怕。但若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利剑,那谁都不敢小视。
司徒江忽然退后,以他这时身上的气力,还不敢冒然出手,他虽有把握制伏李有财,但却不愿去冒那个险。
人往往就是这样,拥有的越多,就越害怕失去,更担心自己的性命。而穷的响叮当,一穷二白的人,却往往能做出一些不合乎常理的事。
幸好李有财还没有穷到这个地步。他虽然口袋里钱不多,但精神上还是很富有。
银丝剑不知何时已被他缠在了腰上,一把抱起无鼻道人,不再停留转身疾奔。
或许李有财自己也没想到,他与无鼻道人还能活着离开。
但事实出乎了他们意料,他们逃出来了。
不论如何,他们逃出来了。所以他们现在只想快快找人,快快寻到郭松仁。
李有财的一番顿悟,让他他对武学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正是这份理解才让他的一举一动有了蜕变。
可就算李有财变得功夫再高,抱着一个人,总是跑不快的。他为何又能从梅娘与司徒江这样的高手手底下逃脱?
因为他们没有追,又或者说是梅娘没有追。
李有财抱着无鼻道人要跑,司徒江当然不会放。眼前两人对他来说都是必杀之人,活着只会阻碍到他的计划。所以他立马要去拦,但一只玉手突然拦在其身前。
“你做什么!”这一次司徒江是真的愤怒了,若是无鼻道人跑了,无疑会打草惊蛇,满盘棋局可能要尽数复盘。
梅娘道:“对不起。”一个美人若娇滴滴的对你说“对不起”,你会不会开心?何况还是一个绝世美人。梅娘的面纱终于摘下,这果然是一张极美极美的面,美到摄人心魂,美到让人窒息。
就连司徒江的心都漏跳了一拍。
梅娘至少有四十岁了,可他看起来就像十六岁的姑娘。皮肤如此的光洁紧致,没有一丝皱纹。两颊红扑扑的,像极了熟透的小苹果。他的唇、他的鼻、他的嘴,都美到无法用言语表达。
所以司徒江的愤怒瞬间烟消云散,但愤怒消失归消失,人却不能让他们消失。绕过梅娘,几步踏出,刹那迈出几丈远,可梅娘忽然又挡在他面前。
司徒江心下一惊,他没想到的是梅娘的轻功竟这么高。还有梅娘为何要摘下面纱,又为何要三番两次的阻挡自己?
他的心沉到谷底,板起脸瞪着梅娘。女人再美,但若阻碍了男人的事,那美人终归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梅娘淡淡的笑道:“你很惊讶,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我。”
司徒江不答。
“你惊讶也是对的,你不记得我也是对的,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梅娘浅浅的笑出了声。他的兰花指又架在了嘴前,顶在他的红唇之上。
她又道:“你大可放心,我也要郭松仁不得好死。”
“你到底是谁!”司徒江厉声喝问。
梅娘忽然踮起脚尖,原地转了一圈,裙带飞舞,长裙扬起,“我就是我,还能是谁。”
司徒江出手了,这时候他已顾不上怜香惜玉。他从眼前这女人身上嗅到了危险。
五指并掌,劈山断岳。
梅娘身子飘后,双手又是一绕,竟缠上了司徒江的手。司徒江大惊之下竟忘了收掌。他可以确信在这么近的距离下,自己的快掌天下间没有人能抓住,但却愣是被梅娘的手缠上了。这证明梅娘出手比他还要快得多。
梅娘整个身子又想一条蛇一样忽然扭转,以司徒江身子为轴,绕到了他的身后。纤纤玉掌正架在他的脖子上,司徒江甚至没有怀疑这只手能轻而易举的要了他的性命。
“你现在也非常的惊讶,但不是惊讶我的身份,而是以为我的武功高你数筹。”
沉默半响,司徒江释然道:“输了就是输了,想不到我竟一直被你这贼娘所蒙骗,怪我自己看走了眼。”他好歹也是一代枭雄,生死之下忽然看的也淡了,既然栽了,就要栽的有骨气,推三委四又算什么男人。
“其实你也没看走眼,我的功夫的确远不如你,天底下又有几个人能修成你这样的功夫?”
梅娘的手忽然松开,从司徒江的脖子上落下。
司徒江转过了身,惊疑不定的瞧着梅娘。他没有再去追李有财两人,因为再追也追不上,李有财两人少说也已逃出了锦江阁,何况还有梅娘要阻拦他。
“天底下出乎意料的事总有很多,你也不必意外,我的功夫远不如你。”梅娘叹了口气,“只是你对自己太自信了,你以为任何事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甚至有许多聪明人在你眼中也是呆子。”
司徒江静静的聆听,将一双眼睛眯起。
梅娘接着道:“这便是你的可悲之处。你以为这些‘呆子’都是你的棋子为你所用,但就连你最信任的厨子都出卖了你。”
司徒江睁大了眼:“你说糖糕里有毒!”
梅娘道:“五毒门下有两绝,名头大的叫‘九百里’,无色无味能迷倒百里内的人。另一药名头虽不响,却为武林人士相当忌惮……”
司徒江道:“你是说‘散功方’。”
“你还算是有些见识。”梅娘说,“这‘散功方’虽不致人伤残,但却会使人在数日内武功尽失。你吃下去的药,渐渐发了药力。”
“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司徒江连说三句“想不到”,他怎么都想不到跟了自己三年的心腹竟会出卖自己,这时只觉得自己浑身功夫所剩无几,气若游丝,只剩下站着的力气。他忽然又道:“既然你买通了他,为何不索性毒死我。”
梅娘道:“毒药都有些味道,你以为你会看不出?”
“好,既然如此那你动手吧。”他仰天长啸,“不做人杰便做鬼雄!”
梅娘抬起手,直直点去。不过她点的不是司徒江,而是倒在地上的刘云水。刘云水甚至连反应都没有,便被点昏过去。
“我叫应子梅。”她转过面,还是在笑,但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悠悠伤感。
应子梅?这名字在司徒江的脑海中打转,他当然听过这个名字,而且印象非常的深。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番场景。那一天,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郭松仁。
那天雨很大很大,他刚取到了“千里毒虫方三头”的项上人头。他拎着血淋淋的人头钻进一家林中客店。而店主人是强盗头头,店里的伙计也都是强盗。
可他拎着方三头的头颅,店里的强盗全部吓破了胆不敢上来招呼。还是掌柜的胆子足些,上来问过了司徒江,给他备齐了酒菜。
几杯热酒下肚,司徒江便觉得浑身上下说不上的舒服。筷子还未落下,门外又钻进来两人,一男一女。他们浑身上下湿的不能再湿,就像是刚从湖里捞起来的一样。
男人相貌较丑,长得一张马脸,女人却美若天仙下凡,凡尘的雨水竟似不能沾染到他的肌肤,就算已经变成了落汤鸡,她看起来还是这么的高雅,这么的让人心动。
店里的绿林强盗自然都是好色之徒,多数人目不转睛的盯着女人,他们嘴里流下的哈喇子甚至比外头的雨水还要大。可那掌柜的却目不转睛的瞧着男人的面目,忽然大叫一声“郭松仁!”疾步奔出店铺,丝毫不顾外头的瓢泼大雨。
那时强盗最怕的不是黑吃黑,而是郭松仁。郭松仁嫉恶如仇,绿林好汉碰到他全没好果子吃,江湖之中甚至没一个黑道不恨透了他,即便那时他才初出江湖。
所以就算外边下着刀子雨,这店主人还是会逃出去,至少在他看来,刀子雨总比郭松仁来的容易对付。
于是,店内的小强盗们也一哄而散,不小的店铺里只剩下了三人,郭松仁与那女子,还有默默喝酒吃菜的司徒江。
郭松仁看了一眼司徒江,拉着女人走到他面前。
那时的司徒江虽未见过郭松仁,但郭松仁名头却早已如雷贯耳。他也万万想不到,自己与郭松仁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
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郭松仁,时而用余光去瞟站在其身后的女人,这女人实在太美了,他极力克制自己,但奈何不争气的眼睛总要注意到她。
郭松仁问候了他一句话,但他好似全未听到。也不知是这女人太迷人,还是外头的雨声太大。直到郭松仁拍了一拍他的肩,他才反应过来。
郭松仁一脸笑容,可司徒江并不想给郭松仁好脸色看,只听“砰”的一声,将那血淋淋的人头摆在了台面上。
他想吓一吓郭松仁,看看他的胆量到底如何。
“好!”郭松仁却大声道,“方三头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早该有这下场。在下郭松仁,还敢问侠客高姓大名。”说完,拉着女人在桌旁的长凳上坐下。
司徒江当然惊奇,郭松仁不愧是郭松仁,突然看见这么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却不受惊吓,而且还能分辨出是谁的头颅。不过更令司徒江惊讶的却是这个女人,任何女人在忽然看到一颗头被摆在桌面上必然会花容失色,可这个美丽的女人却连眼睛都未眨一下。
他不禁好奇起来,可他还是忍不住要刁难一下,“这酒这菜都是我的,你们要吃自己点去。”店里明明没了人,又能向谁去点,司徒江话中挑衅的意味非常明显。
郭松仁却不生气,反道:“兄台只管吃,我只想与兄台成个朋友。”
“你见到谁是不是都想交朋友。”
“我只交该交的朋友。”
司徒江每句话都要激一激郭松仁,可郭松仁却全然不理他这一套,放开胸襟侃侃而谈。他的身上就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牵引旁人的心绪。两人话说多了,自然说道点子上去,连司徒江自己都没发现两人竟越聊越投机,到后来已把酒言欢变成了朋友。而那女子从始至终都只在一旁静静的听着,不插一句话。
这么美得女人毕竟能牵动男儿心,司徒江还是忍不住问郭松仁:“郭大哥,这位可是嫂嫂。”
郭松仁道:“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应子梅。”
……
时光转瞬即逝,眨眼竟是二十余年。从那以后他再没见过她,但她的身姿久久不能拭去,直到有一日听到了她去世的消息。
可她还是会若有若无的出现在他的梦中。这或许也是他想杀死郭松仁的原因。
司徒江凝视着眼前的应子梅,他忽然想起应子梅那时去后堂做了几道小炒,味道妙不可言,另外还做了两道甜点。他才记起,原来自己是从那时候开始爱上甜点的。
无论面临怎样的对手,他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可现在连他自己都未发现,嗓中的声音竟不断发颤,他道:“可你——你不是已经死了?”
应子梅笑了,“你好像记起我了。你看我像是死人吗?”
她又道:“郭松仁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他的身上有一股别的男人没有的味道。”
“所以当初你才会与他在一起?”
“没错,但他却是一个没有野心的男人,我虽迷上了他,但却讨厌没有野心的男人,所以我离开了他。”
“没想到他骗了我,当初他还和我说你死了。”
应子梅吃吃的笑了,她抱着自己的肚子,笑的略有夸张,“那是我骗了他,我用假死避开了他的耳目,他倒以为我真死了。”
“那你为何还要他死?”
应子梅说不上来了,他怔在原地,过了半响忽然又说:“我就想要她死,我恨他。”
一般来说,女人如果说恨一个男人,往往就表示他爱这个男人。如果女人说要杀死他,那可能就有两个原因。其一便是恩怨情仇,世事无常总会有许多恩怨纠葛。其二,便是男人抛弃了这个女人。
如果郭松仁没有抛弃应子梅,她为何又要杀了他?先前这几句话也不过是梅娘信口胡诌的而已,试问郭松仁若没有野心,还能有今日吗?司徒江懂,但他未说。有的话还是藏着掖着比较好。
“你也了解郭松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司徒江顿了一顿,叹了一口气,“我不清楚你是在为谁做事,但你还是算错了,你要拿我至少也要在我杀了他之后。你现在对我下手,还能拿什么去对付他?”
“你以为仅凭你这点人手,杀得了郭松仁吗?”梅娘走到了石墩前,指着棋盘,道:“妄你跟了郭松仁十余年,却连他有多少底蕴都不知道。”
司徒江也缓步走来,再见应子梅,他竟连什么都不愿去想,甚至先前的所有计划都被他抛在脑后。他道:“我又如何不知?聚义盟之中有丐帮与数十散门对他尽心尽力,这里少说也有千人上下。”
应子梅卓有兴致的看着他,道:“不错。”
司徒江接着道:“郭松仁身边有十三护卫,更有无鼻道人与江白鹭两位绝顶高手。单是这些人便可横扫少林、武当之外的所有门派。”
应子梅的眼睛笑的有些弯了,她道:“也不错。”
“在江南武林中,他还培养了一匹武功不弱的年轻人,这些人对他誓死效忠。”
应子梅的眼睛几乎快变成月牙了,“没想到你连这个也查出来了。”
她在石凳上坐下,目光瞧着棋盘,道:“可除此之外呢?”
司徒江也坐下来,一双眼却紧盯应子梅那明亮的眸子。她的眸子闪闪发亮,就像黑夜中璀璨的明珠一般。
他试探的问:“你的意思是,郭松仁的势力不止如此?”
应子梅轻轻一笑,夹起一枚黑子,放在了司徒江先前犹豫不决的位置上。她没有回答司徒江的问话,反而道:“若你方才不犹豫,早早就能赢下这盘棋。可现在我们已离开棋盘,所以这棋只能算和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