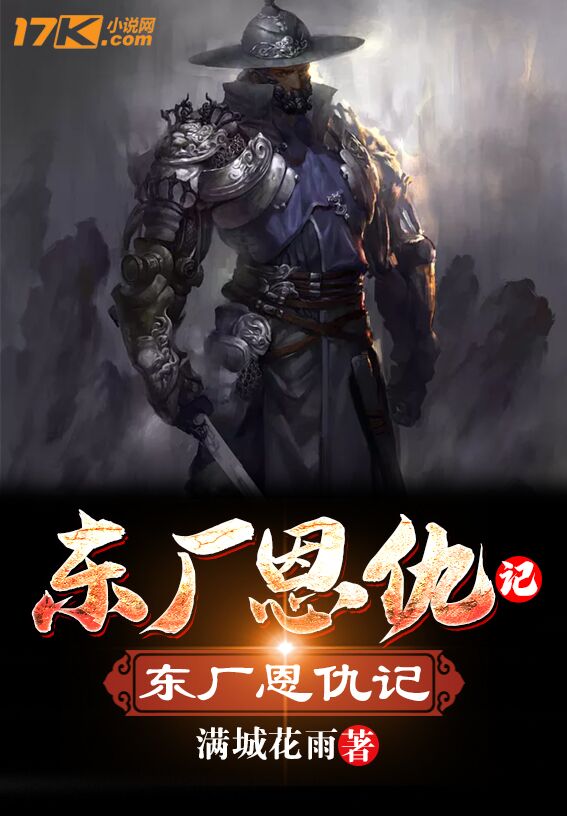第七十二章_冰谷初虹
见这么多人一齐冲了过来,别说那八名弟子,就是高延和白棠也暗暗生了惧意,倒是杨澈收刀入鞘,玩味地看向众人,丝毫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往生去吧!”水汜和轻哼一声,身周阴气暴涨,转瞬间凝成九条通体幽黑吐着信子的冥蛇,九条冥蛇张牙舞爪,盘旋着向众人袭去。见识过冥蛇咒的众人丝毫不乱,原地立稳运足了罡气护体。水汜和见状冷笑一声,目色一沉,九条冥蛇声势更厉,如疾风一般穿过众人,却是化作烟雾,消失不见了。
“尽是花招,看来没什么真本事,给我上!”顾南行哈哈笑了两声,又下令喝道。
而站在原地的一众黑衣人,却像是没听见一般,动也不动。
“小心,好像有点不对劲儿。”田了建伸手挡在顾南行身前,警惕地打量着四周。那些弟子别说动了,在这样寂静的深夜,竟连气息也丝毫感觉不到。
顾南行不是傻子,见状也猜到了这些人已经遭了毒手,不由地心中像打鼓一样,脑中不断回想着水汜和那句“往生去吧!”,身子不由地一阵阵发寒。
田子建见顾南行全身发抖,也见识了水汜和的一怒之威,当下抽出长剑,喝道:“南行,你快走!”
这一声喝却是让顾南行清醒过来,他望着田子建不顾性命地护着他,心中一暖,也不觉着害怕了,道:“子建,要走一起走!”
水汜和闻言抬起头,幽幽问道:“你叫子建?”
田子建一愣,显然不知水汜和何意,难不成他不杀无名之辈?可方才举手间便杀了二十多人,也未一一问过名讳。当下一阵疑惑,只得点头“嗯”了一声。
“哪个子?哪个建?”水汜和又问道。
田子建本被一招震摄,但临危之际,倒没了惧意,便昂首挺胸道:“君子的子,建安的建。”
水汜和“哦”了一声,淡淡说道:“好名字,我不杀你,走吧。”
田子建一愣,竟只因名字就得了赦令?随即想到:他定是有故人与我重名,含旧之下不舍得下杀手。松了一口气,道:“多谢城主大人,只是子建要带着他一起走!”说着指了指顾南行。
“你先走,我不会让他死!”水汜和淡淡说道。
若是留顾南行一个人在这儿,也不知会发生什么,田子建想了一会儿,还是不放心,道:“大人既有海量,何不能再容下一叶扁舟。”
水汜和见田子建不顾生死也要护着顾南行,笑了笑,道:“你放心,我会让他完好无损地回到流锋剑派。”
田子建犹豫了一会儿,他知自己倚仗名字之利,已让水汜和作出让步,若再得寸进尺,惹恼了他,两人只怕都走不了。想到水汜和身为一城之主,也定是一言九鼎之人,他既承诺了不会杀顾南行,便也只能信他。更何况,他根本没有与之谈判的资本。
“既如此,子建先行谢过大人!”田子建朝水汜和鞠了一礼,转身对顾南行小声说道:“我不会走远,有事叫我。”
顾南行点了点头,他此时也没了惧意,目送田子建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顾南行望向水汜和,见他无论出手还是谈判,始终都紧紧搂着高蝉,方才听得高蝉叫他“哥哥”,原来二人竟是兄弟,那难怪了,他将自己留下,定是要把高蝉受的伤都偿回来,想到只是受些伤,原本悬着的一颗心也定了下来,平静说道:“你想与我单挑?”
水汜和轻轻松开高蝉,对白棠道:“你们带蝉儿先走,小澈,你留下。”
见识了水汜和的实力,白棠也惊而生惧,她依言扶过高蝉,却不知该往哪去,藏身地点只有杨澈和秦望川知道,秦望川不在这儿,杨澈又被水汜和留下了来,想要开口询问,却终是没提起胆。心想水汜和既是想避着众人处置顾南行,只要先向前走一段儿,在那等着便是。只是顾南行这次栽在水汜和手里,可是相当不妙,她见识过水汜和对高蝉的疼爱,是那种会为之玩命的疼爱。
白棠扶过高蝉,向高延使了个眼色,便一道向前行去。因水汜和指名了白棠,高延更是连上前帮把手都不敢。
一行人走远之后,只剩下水汜和、杨澈和顾南行三人,还有树立着的,与活人一样的二十余人。水汜和幽衣一扬,一阵阴风刮过,那二十余人登时化作飞灰,顾南行亲眼见了这一幕,脑中又是一阵空白。
“小澈,你的阴脉咒术已有四重火侯,我现教你第五重咒术,你可看好了!”水汜和面若带笑说道。杨澈一听来了精神,笑道:“弟子愿学!”
睡了一觉,高蝉又做了那个噩梦,梦中父亲被一条巨蟒缠身,口中对他大呼着“快跑!快跑!”
高蝉惊坐起来,见水汜和正守在床前笑道:“又做噩梦了?”高蝉点了点头,水汜和笑道:“死鬼老爹也真是的,定是看你好欺负,整日纠缠着你。有胆子他入我梦试试,看我不把他打下炼狱?”
高蝉闻言“噗嗤”一笑,打量了下四周环境,见此处十分安静,连鸟叫声都没有,料想已经到了秦望川找的那个僻静之所,想到昨夜被顾南行追杀后遇到了水汜和,问道:“哥哥,你把顾南行怎么样了?”不知怎地,他丝毫不担心水汜和会在顾南行手下吃亏,似乎只要有他在,就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安全感。
水汜和倒了杯茶递了过来,淡淡说道:“有李淹长在,他死不了。不过有他在,李淹长也活不了。”
“什么意思?”高蝉喝了口水问道。
“不告诉你。”水汜和笑道,他实不想让高蝉知道阴脉咒术的险恶,或许是不想让他觉得自己也是个险恶的人吧。
“嘁,我还不想知道呢。”高蝉翻了个白眼。“嘿咻!”叫了一声,将手中的杯子掷到桌上,杯子平稳落下。
“武功有进步啊,快跟我说说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些啥?”水汜和坐在床边,一副聆听者的表情。
于是高蝉的长篇大论便如江水一般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从扬州到柞水,又沿丹江下襄阳,成都,渝州的所作所为,事无巨细,一一向水汜和阐述,直到了傍晚,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才停了下来。
二人行出小屋,高蝉见着秦望川、戚华等人平安无恙,也是十分开心。戚华早就备好了饭食,只是听了高延说起昨晚的情形,愣是不敢去叫水汜和与高蝉用膳。此时二人出来,她本打算去把饭菜热一下,又觉着给二人剩饭剩菜不妥,忙又下厨做了几个小菜。
高蝉便又叫了白棠、高延一起用饭,饭饱之后,杨澈与容焕宁一道过来,分别对二人行礼后,水汜和向高蝉问道:“这就是你新收的徒弟?”
高蝉点了点头,水汜和道:“怎地中了醉香含笑的毒?”
高蝉大惊,问道:“不是已经解了吗?”
水汜和摇了摇头,道:“只解了一半。”
高蝉心中充满疑惑,水汜和怎地一眼就看出了容焕宁中的毒,还能看出这毒只解了一半,不过既然能看出来,也定有解另一半的法子。
水汜和望着高蝉笑了笑,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将容焕宁唤过来,将拇指上隐戒取下,置于容焕宁掌心,五指虚空地不知在比划什么,过了一会儿,将隐戒收回,道:“好了。”
众人看得糊里糊涂,谁也不知他是如何解的毒,或者说谁也不知到底有没有毒,这两下子,倒是像极了那些江湖术士,就是人们常说的骗子。不过经由水汜和之手施出,众人却是不敢怀疑,每个人心中都暗道:“定是有毒的!已经被解了!”
“解毒之人应是顾虑到她腹中的胎儿,故留了一味猛药。”水汜和说道。
腹中胎儿?众人闻言一惊,容焕宁虽算是与云旗拜了堂,成了亲,可那是在云旗身死之后,连洞房都没有,何来的孩子?见水汜和下了谬论,众人也不敢反驳。
“哥哥,焕宁是云英女子,何来的胎儿。”高蝉小声说道,不过旁人也都听了去。
水汜和望向容焕宁,见她脸上潮红,时而娇羞,时而高兴。过了半晌,才激动地问道:“这么说,我怀了云旗的骨肉?”
水汜和点了点头,道:“已经足月了。”
容焕宁忽然大笑起来:“上天眷我,云家有后了。”忽又跑到廊下,向天地跪拜,像是自言自语道:“夫君,你听到了吗?我有了你的骨肉。”
已经足月,那时云旗还未死。众人见容焕宁神色,也都明了,原来容焕宁与云旗未婚就先圆了房。怀了这个孩子,也当是天意吧!
在孤鸿庄这么多人离开之后,终于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一时间,不仅戚华、方采薇等人笑得合不拢嘴,就连高延也激动地目光泛泛。
高蝉笑了笑,叫道:“兄长。”
“嗯?”水汜和问道:“怎么了?”
高蝉嘿嘿道:“哥哥,不是叫你,是叫他。”高蝉指了指高延,道:“他待我像哥哥一样,我便称呼他兄长。”
水汜和淡淡“哦”了一声。高延站起来欠身道:“高延不敢当,掌门还是直呼高延名讳的好。”
高蝉笑道:“今天是大好日子,不说这些,我方才是想说焕宁有了身孕,得好好补补,我看这个地方也未免太清简了些,兄长得空儿,去附近买些滋补的东西回来。”
高延忙应道:“是是是,属下领命。”
第二日,水汜和起身时,见高蝉正在房前一块空地处与秦望川和杨澈一块儿练武,这儿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倒像极了汜水城北的竹林小居。水汜和觉着舒服,便静坐下来,看着三人打闹。
过了一会儿,容焕宁打开房门,伸了个懒腰,秦望川见状,调笑道:“师妹今天怎地这么懒,现在才起。”
容焕宁白了他一眼,道:“我是有身孕的人了,渴睡了些,也是正常的嘛。”
秦望川听着一阵咯应,昨晚才知道有身孕,今天就摆起谱来了,平日与她打闹惯了,道:“晨练益精,快来一起过过招。”
容焕宁面如春风,摸了摸空瘪瘪的肚子,温柔如水道:“那可不行,我可不能吓坏我的孩子。”
这次不仅是秦望川了,连高蝉和杨澈也打了一个激灵,三人相视一眼,道:“我们换个地方练吧!”便一同向屋后走去。而容焕宁也不在意,小心地摸着肚子,满脸的幸福与满足。
水汜和见三人离开,笑意也渐渐地从脸上褪去,他站起身来,望着天空中还未落下的的略带青灰色的月盘,自顾轻声道:“八年了,炙野,你师父可还安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