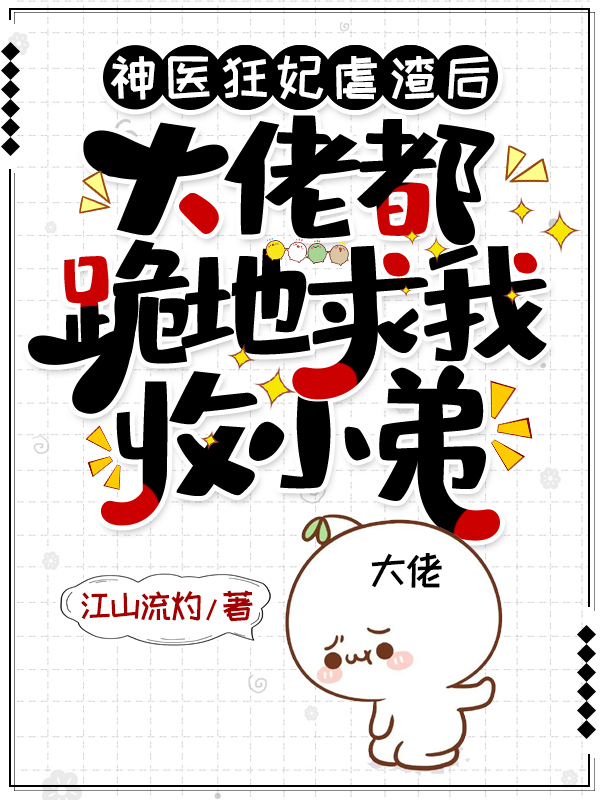尤氏哭哭啼啼陪着贾母和元春来到宁国府,直奔正房而去。
还未来得及进门,却见贾蓉一路哭着奔到贾母跟前,跪倒在贾母的脚下,抱着她的腿嚎啕痛哭起来。
元春见状,忍不住也伤心起来,又见贾蓉已经泣不成声,连忙伸手拉了起来,劝道:“蓉哥儿,有话慢慢说,快别吓着了老太太。”
贾母也着急道:“你爷爷和你父亲到底怎么样了,蓉哥儿快说呀!”
那贾蓉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家中突然发生如此变故,一时便慌了手脚,不知从何说起。
尤氏看见贾蓉急成这个样子,心中就知道出大事了,也向贾蓉着急道:“爷爷到底出了什么事了?蓉哥儿快快说来!”
“老太太!母亲!”
贾蓉终于缓过气来,哭泣道:“爷爷和父亲起了争执,两人都不肯退让,爷爷一起之下便离家出走了。”说着又哭。
听了这话,贾母心中也着急起来,一时又是心疼又是着急地,向贾蓉道:“蓉哥儿,你这个孩子,怎么也不知道命人跟着呢?”
贾蓉哭诉道:“派了焦大一路追了去,他回来说,爷爷,爷爷他,向城北的道观里去了,老祖宗,怕是劝也劝不回来了啊,呜呜呜.......”
“你父亲呢?你父亲哪儿去了?”
尤氏看了一圈不见贾珍的影子,感到事情更加地不妙,着急地向贾蓉问道。
贾蓉向尤氏哭道:“母亲去请老太太的时候,父亲就不顾爷爷的劝阻,抬脚就出去了。”
“平心而论,我们贾家到底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怎么遭这样的报应啊!天啊,您倒是睁眼看看啊!”
贾母仰天长叹,心急如焚。
元春见贾母烦恼,自己也不由热泪盈眶,一边为贾母擦拭着眼泪,一边劝慰道:“老太太要保重身体才是,我们,还都指靠着您呢。”
元春劝慰着,见贾母好不容易才收了眼泪,又连忙弯腰拉起贾蓉,劝慰道:“蓉哥儿快起来吧,再怎么要紧的事,也要等老太太进了屋再说才是呀。”
贾蓉和尤氏见贾母伤心烦恼,也怕老太太再出什么事情,连忙各自收了眼泪,向贾母道:“惹老太太伤心,是做晚辈的不是了。”
说着和元春一起扶着贾母来到正房的厅里坐下。
众人这才一一向贾母行礼。
贾母袖子一挥命众人起来,感伤道:“我只要你们大家都好好的,就是没有这些虚礼也就罢了。”
又向鸳鸯道:“快去请大老爷和二老爷过来,商量一下补救的办法吧。”鸳鸯口中答应着,可是心中还是放心不下贾母,立在贾母的身边欲行又止。
元春见状,伸手在鸳鸯肩膀上拍了两下,向她小声说道:“你安心留在这里,让抱琴去请大老爷和二老爷吧。”
抱琴连忙答应着匆匆地去传话了。
不到两盏茶的功夫,贾赦和贾政急匆匆地从外边进来了,二人向贾母行过礼,按序坐下。
贾母叹道:“敬儿和珍哥儿可恶,扔下这孤儿寡母的不管,竟各自去了,身为长辈,我们却不能袖手旁观,你们两个也说说,眼下的情况该怎么办?”
贾赦一边喝茶一边唉声叹气。
贾母看见,少不得又是一番抱怨,道:“找你来商量事呢,只顾着叹气做什么?”
贾赦放下茶盏,小心道:“儿子说了,又怕老太太不爱听,事到如今,只怕,我们也只好顺其自然了。”
“我就知道,事情不在你身上,你自然是不愿意操心的。”贾母向贾赦斥道。
贾赦连忙起身,向贾母赔礼道:“母亲息怒,不是儿子不用心,只是敬大哥和珍哥儿父子俩一向水火不容的,才发展到今日的这种状况,大家心中都是知道的,如果能够化得开,何至于会发生今日的事情呢?”
贾母恼怒道:“罢了罢了,我老太太左右不劳你费心便是了。”
元春生怕贾母情绪过度忧虑,再生出什么不测来,连忙跪在贾母的身边,哭劝道:“老太太,您就看着春哥儿和宝玉,也要好好保重身体才是啊。”
贾赦见状,便不敢多言,只坐在一边静静地喝茶。
贾政摸着自己的下巴,深思了半天,向贾蓉和尤氏道:“侄子媳妇儿和蓉哥儿可有什么想法吗?”
那贾蓉还是个孩子,心中哪有什么主意,听贾政这么一问,跪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孙儿能有什么想法?任凭老爷们做主,想办法接了爷爷和父亲回来,孩儿也就心安了。”
尤氏虽然在心中怨恨贾珍,为了搭救郡主,竟然不顾多年的夫妻情分,要以正房礼仪迎娶郡主,本来还想着,到贾母跟前诉诉苦处,赢得了贾母的支持,也好维持了正房的身份。
不想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自己心中一时惊慌起来,倒也没了注意,心中只巴望着贾珍能够快点回来。
于是向贾赦和贾政行礼道:“一切全凭叔叔们做主,找回公公和大爷才好。”
众人又商议了半晌,贾母看看天色已晚,事情也不能再耽搁下去,于是向贾赦吩咐道:“今晚,让敬儿冷静一下也好,明儿个,你一早起来就去城外的道观里,接了敬儿回来。”
“是,儿子听老太太的。”贾赦有了前车之鉴,再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躬身答应着贾母的话。
贾母又向贾政道:“政儿,你即刻就去秦继业家里一趟,看看珍哥儿在不在哪里?”
“是!儿子明白。”
贾母见贾政点着头答应了,又向元春道:“春哥儿,你和你父亲一起去,和郡主说说话,毕竟你们年龄相仿,有什么话也好说一些。”
“老太太放心,春哥儿知道该怎么做了。”元春马上答应着,和贾政一起出发了。
贾政和元春来到秦继业家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秦继业见自己的上司亲临家中,连忙吩咐夫人准备晚餐。
事态紧急,贾政也顾不得客气,任凭秦继业的夫人去安排,自己则和元春一起被秦继业安排到书房坐了。
这秦继业,本是工部属下的一员小官儿,俸禄微薄,且又出身寒门,虽然做着一个小官,却只是比一般百姓家中略微宽裕而已。
这些年来,承蒙贾政的关照,日子才过得略微滋润了一些,家中也用上了一男一女的两个仆人。
秦继业看着贾政和元春在书房坐定,又连忙吩咐了小丫头烹了最好的茶捧上来。
贾政随身服侍的小厮和抱琴一起,一边一个地在门外站在,随时等候主人的吩咐。
贾政端起茶盏,习惯性地用盖子拨了拨茶叶,轻啜了一口,向秦继业道:“郡主近日可好?”
秦继业见问,连忙起身回道:“不瞒大人,这些日子,还真多亏了珍大爷的悉心关照,郡主的情绪才稍稍稳定了一些,不过,却也还是愁眉不展,令人焦心呢。”
贾政轻叹了一声,道:“小小的年纪,遭遇到如此不幸,实在令人痛心啊。”
元春才喝了半盏茶,听到秦继业和父亲的话,便起身道:“伯父,不知郡主在哪里,侄女儿想见她一面。”
贾政也向秦继业道:“让春哥儿见见也好,她们年龄差不多,又都是女孩子家,有些什么难言之隐,也方便说些。”
听贾政这么说,秦继业连忙唤了小丫头过来,带着元春去郡主居住着的西厢房。
抱琴尾随着元春也跟了过来。
秦继业的家,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靠北三间主房住着秦继业夫妇,东厢房中的两间做了书房,另一间住着小儿子秦钟,靠南的三间抱厦,一间做了厨房,另外两间便是下房,西边的三间厢房特意收拾了一番,给了郡主居住。
元春由小丫头引着来到西厢房前,小丫头刚想上前敲门,却听见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女子悲戚的哭声。
元春的心不由沉重起来,她的心中非常清晰,也许,多年之后,她同样会面临着和郡主一样的命运。
她的眼睛潮湿,心中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元春轻移着脚步走到门前,里边又传出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可儿,有我在,你就放心好了,我不会辜负了我们之间的这份情,我要堂堂正正地将你娶回家去。”
是珍大哥的声音,元春并不感到惊奇,示意小丫头上前敲门。
“笃!笃!笃!”
“小姐,贾府大小姐来看您了。”小丫头通报道。
贾珍开了们,一脸惊讶地望着元春,道:“大妹妹,你怎么来了?”
元春向贾珍屈膝行了一个常礼,道:“老太太不放心,让我和父亲来这里看看,父亲现在秦伯父书房喝茶呢,珍大哥,你去见书房见见他们,让我和郡主单独聊聊可好?”
贾珍回头望了郡主一眼,转身出去了。
元春看着贾珍走远,吩咐抱琴在门口候着,自己进了郡主的房间。
“元春向郡主请安!”
郡主见元春向自己行如此大礼,心中五味杂陈,连忙起身扶起元春,道:“大小姐快不要如此!”接着,又黯然道:“我再也不是那个身份尊贵的郡主,而是一个,小官吏的女儿,秦可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