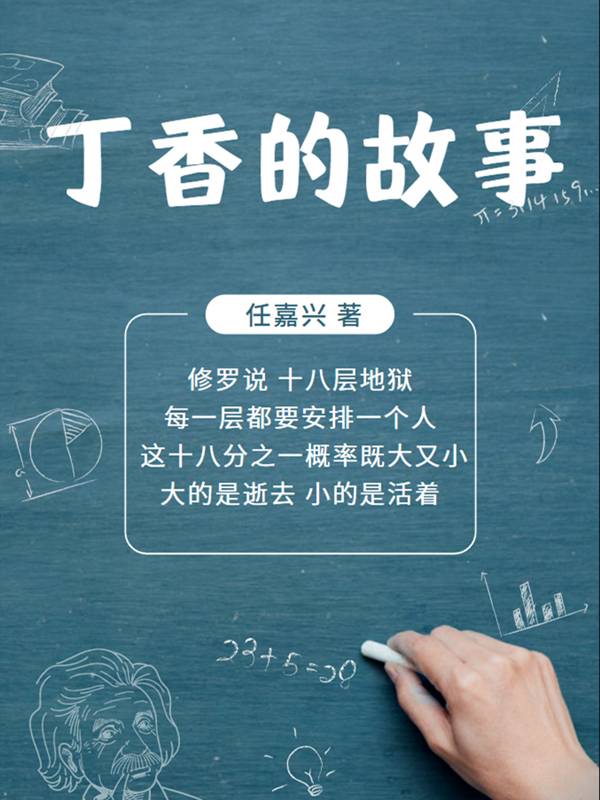其实这样的她不可不谓是狂妄的,苍月亿兆,她只在乎自己在乎的,这让内阁里听了她这话的这几位都不得不觉得一惊。
可对于他们听后的这表现,冷黎月却是一点都不觉奇怪,她边批着奏折,边说了一句:“就像绝说的那样,不变的将军流水的兵,战争总是要死人的,这并不只是适用在战场上,三尺庙堂也是个战场。也许身在帝王位上的人,无论是谁都没有与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人能同归的资格,我并不意外这必然的悲哀,可是苍月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如果各位不能与我同进共退,我自然可理解,也无需原谅,因为这并不是你们的过失,即使你们选择离开,那也不是背叛,我理解你们忠于生命的任何决定,可如果各位不选择离我而去,我在此承诺,我和诸位共享我苍月的一切喜悲成败。”
她这一言之下,内阁里的几位听了自然都已知道冷黎月一定是有什么大动作了,不然她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只是冷黎月却还是波澜不惊的批着她案头的奏折,她是如此的平静,却让他不由的心疼,心疼这出色到惊人的她,可是面上却没有丝毫的波澜。
冥玄这边还在心疼,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干预,才可最有效的自只是在转脑子,可天下间言性子,人人都是不同的,他这里可以不妄动,是因为他一向稳重。
可大将军王可稳重不起来,他是心一动就行动,自是只见慕容绝打破了这沉默的说了句:“月,你若不弃,我便不离,烽火硝烟的战场上,我们都一起过来了,还有什么是必须让我们对彼此放手的呢?”
而这他话刚罢,才刚回过神的明镜期也是不甘示弱的说了句:“月,我明家本就是商贾起家,既然有人愿意和我分享一切喜悲成败,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
他们的回答都在冷黎月意料之中的让她开心,觉得有这样的伙伴还真是不错,但再不错也不是她最看重的,因为他最看重的从来只有一个人的回应,故在此时冥玄的话也是冷黎月最想听的,可也是她深恐自己真的承担不起的。
而这时只闻冥玄也开口到:“月儿,我知道你一定有大事要说,不然不会这样问我们,不过我只说一句,苍月新立,又是女帝称制,变革是难免的,这不过是必然罢了,你不必有太多顾忌,反到困住了自己,只有你赢了,你所顾忌的一切,你才有可能去维护,所以你的顾虑不该困住自己,你是苍月之帝,自是苍月至重,没有任何人比你更重要。”
他平缓的说着这段话,可心下的复杂只有他自己清楚,可他知道此刻自己必须要平静,自己越平静,她才可能敢跟自己分享以后任何的不顺,那么自己才有机会去帮她,起码有这个可能,他这样想着迫使自己平静一些,再平静一些。
而冷黎月听了得他如此,她自然是开心,可开心归开心,帝王位上的太多事,在她以史为鉴可知兴亡的见识下,让她还是习惯性的试探着他的边缘,因为其实她也没有底,在此身里意外和圆满到底那个会先敲她的门?
这让她不由的合了合目说了句:“呵,那我若说,我不是最重要的呢?人生百年谁无死,我若死了呢?”
她似是戏言般的说着这一切,自然会有那一份属于她的不正经如影随形着她,可她的这话显然沒有说完,却被冥玄的一句:“月儿,我不许你说这个,只要我还是我,我不许你想这事,我让你如此出色 绝不是企图让你去死的。”
他这话说的认真,认真的让她也认真了起来,只见冷黎月也一收开玩笑的样子,极为认真的说着:“我了解你的意思,可玄你也该知道这是多奢侈的事,我不会去找死,虽然我厌极了这个皇位,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在这无常的生命中,我们必须要有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离我们而去的准备,这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它不需要任何情绪,虽然情绪是不可抗拒的,但在可控的范围里,我们至少应该能控制它这是毫无疑问的吧?”
她把这番话说得如此理智,这样的她无疑是他所熟悉的,这样的她不是坚强,只是忘心,那是她超越绝望后的不服,为此她忘记心下所有喜悲,摒弃了一切会影响到她的行为的杂念,而她如此这般只是为了掌握对事或人绝对的把控权,这样的她总是霸道的让他都诧异,却从来都舍不得责怪她什么,因为出生帝苑的他太明白,在尔虞我诈的宫中,能如此和敢如此是两件事,而敢明明白白如此的就绝对不会是小人,所以对于君子,他自然不舍得苛责太多,因为他知道做君子本就太难了。
可这样的她也让他实在难以继续平静下去了,故他来到她的身侧,夺过她手上的奏折道:“月儿,我不知道你在畏惧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安什么,可是我想告诉你,繁华建立前总是启于残垣断壁的这是常态,或者说这本就是必然,故以你的聪慧和透彻,本不该被这些所迷惑,你只管依着你自己的布局去下这局棋就好,而其他的一切就交给我们就是了,这不是因为你是个女孩儿,我才这么说,这不是我对你的格外宽容,而是人力有极,任何上位,但凡能在这位子上坐过满三天的人,处事往往都是这样的,甚至他们比这些做的还要过分,不也心安理得的居在这个位置上吗?秦皇汉武、古往今来、向是如此,你会不惯正常,所以你就不要太苛刻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