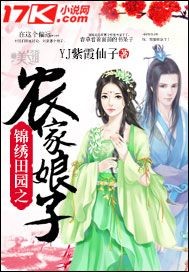说回郑国泰,那时他气鼓鼓地从茶楼出来,便遇见了约好了前来此处会面的严宪。严宪同为官宦子弟,也是国子监的监生。
“郑兄这是怎么了,这茶会还没进行,你倒先走了,还是特意出来迎接?”严宪忙上前询问到。
“气都被气饱了,那还有心思举办什么茶会。”郑国泰没好气到。
“郑兄到底因何事生这么大的气?”严宪自然看得出郑国泰一脸怒气,只是他也知道自己这位朋友向来跋扈,不管得不得理都是不轻易饶人的,他不去气别人倒还罢了,怎的今日被人气成这样,心中自不免好奇。
郑国泰正欲说起反讽一事,但想起此事不免有失自己的体面,便又把刚出口的话给吞回了肚子,但心中窝火自是不必说的,想了想便只让严宪陪他到郊外去散心。
见郑国泰欲言又止,严宪便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不然也不会这样生气,也懂得不要在老虎身上抓虱子,由其是发火的老虎,便只答应了一同前往,郑国泰真想说了自然会自己说出来,没得揭人疮疤。
两个人到了郊外便下了马车漫无目的地闲逛,走着走着郑国泰突然开口问起了并肩而行的严宪:“你觉得苏正居和许登科这两个人如何?”
作为同郑国泰国子监内外都走得近的,严宪自然去过梅香斋,只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郑国泰明显地瞧他二人不起,并未曾在他的面前提起过这两个人,怎的今日倒反问起他们来,尤其是在刚刚生过一场大气好不容易缓过来的情况下,于是说到:“不过去找郑兄的时候匆匆见过,并不曾真正注意,郑兄不是瞧他二人不起,怎的倒说起他们来了。”
“原是我错了,倒真的不能小看了这两个人。”郑国泰说着捡起石子在湖面上打起了水漂。
原来郑国泰不是无端提起此二人,想是同今日的生气不无关系,严宪本就打定主意不自己过问郑国泰生气的缘故,便只笑到:“小草岂能撼动大树,无论他们做什么或说了什么都不必理会,从前如此,以后更是如此。”
“从前如此,以后更是如此?”郑国泰心里默念着严宪的这两句话,虽觉有理,可是他又岂能轻易吞下这口气,一想起他们在自己面前借前事讽刺而自己却不知和缘故,不免又气从中来,一拳打在了一棵树的树干上,挂在树上摇摇欲坠的落叶簌簌地掉了一地。
见此形状,可见生气的缘故便是因为这两个人了,只是这事发生在茶楼倒叫人奇怪,严宪仍旧保持沉默……
“你就不问我为何提起他们?”严宪这一沉默反而吊起了郑国泰的胃口。
“郑兄若想说自然会说,不想说的我也不好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反倒落个没趣儿。”严宪笑到。
“就你心思缜密,也罢,今日难得一同出游,便不提这些事了,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吧。”郑国泰说着轻拍了拍严宪的肩膀,终于露出了笑意。
两个人在郊外闲逛了一个时辰便启程回城,在这段时间里,两个人再没谈起过有关苏正居和许登科两个人的事,自然也就没有涉及郑国泰冒火的原因。
郑国泰回到尚书府,刚进门便听管家说了爷爷有事找他,让他转告其从外面回来了便到书房中去找他。
郑国泰答应了一声,便往爷爷的书房中来,行了礼后只是轻松地问到:“不知爷爷唤孙儿前来所为何事?”
郑守礼指了指桌案旁的椅子示意郑国泰坐下,笑到:“非得有事才找,爷爷就不能让你来闲聊不成?见你刚从国子监回来便忙着四处应酬,实在不好打扰。”
“爷爷说笑了,孙子并无此意思,想来也已经许久没有同爷爷闲聊了,正好趁此放假的机会,本应该亲自来而不是等爷爷找。”郑国泰说着坐了下来。
“你刚才问的也没错,爷爷确乎有一件事要同你说,只不过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郑守礼意味深长地说到。
见爷爷突然如此说,郑国泰也警惕起来,端正端正了坐姿态问到:“爷爷果真找孙子有事,孙子洗耳恭听。”
“这事爷爷早就想同你说了,每每因为其他事情而作罢,你虽是尚书府嫡孙,行事做派更需要谦虚谨慎,不可太过目中无人。”郑方海顿了顿说到。
听了爷爷这话,郑国泰紧了紧心,爷爷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同自己说这样的话,定是听说了什么,忙为自己剖白辩驳到:“孙儿出到外面代表的是尚书府的颜面,行事做派难免不拘小节,然不至于爷爷所说,定是外头那些个小肚鸡肠的人在爷爷耳畔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子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是否如此心里最清楚不过,爷爷不过提醒你一下罢了,你不必急着为自己辩白。”郑方海说到。
见爷爷如此说,郑国泰也不好再为自己辩解什么,只得口头称是,心中却已经在盘算着会是谁在爷爷面前告状。
“在国子监这段时间学习生活如何?”郑守礼转而问到。
郑国泰楞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爷爷在问他,忙回答到:“不是孙儿骄傲,孙儿的功课连先生都赞许的。”
“那就好,生活上呢,有没有跟同窗好好相处?”郑守礼点点头,继续问到。
“同窗?”郑国泰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苏正居和许登科二人,一想到这两个人的小人所为,禁不住鼻子冷哼了一声。
“怎的,跟同窗相处不融洽?”郑守礼问到。
“虽谈不上融洽,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并无过多交流。”郑国泰莫名心虚,有些敷衍地说到。
“人有好恶本来很平常,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既知井水不犯河水,就仍按你所说的去做便是了。”郑守礼说到。
听到此,郑国泰不免又好奇起来,怎的爷爷好像早已知道了他与同窗之间的淡漠,特意引着他说了这么些话。
“你刚刚出府去了哪里?”郑守礼又转而问到。
“先去了茶楼,后来又去了一趟郊外。”郑国泰如实回答到,并不想提茶楼发生的事情。
“你去了这半天应该疲累了,爷爷也不多问,你回去休息吧。”郑守礼说着在书架上拿出书来。
“那孙儿就不打扰爷爷,先行告退。”郑国泰站起身来行了礼便带着满腹疑问从书房退了出来,暗誓定要把这告状之人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