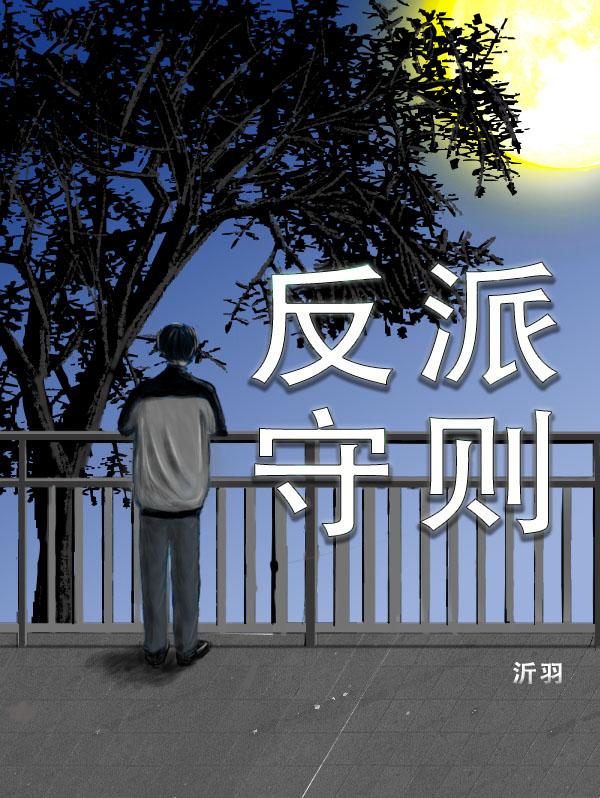网鸟的老农们离他们有近三十米的距离,他们并没发现这里的一切,只顾抬头寻找着被他们惊起的鸟群飞行的去向。
黄军大衣手中的猎枪举起又放下了,这个时候开枪无疑是想将这几个网鸟的老农们的视线吸引过来,那么,他们的抢劫行动就会提前暴露无遗。
“有人来了,”黄军大衣向两个同伙使个眼色,说,“快走!”
三名劫匪迅速跑向王利东还没有熄火的出租车,小平头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开车向齐河方向飞奔而去。
滚在沟底的王利东并不知道这三个劫匪为什么会突然跑掉了,他还真以为他们遵守诺言,没有开枪杀死他。他想爬起来,爬出沟底,手脚上的绳索却叫他无能为力。他几次站起来,又跌倒,直到筋疲力尽。
那几个网鸟的老农并没有看到刚刚发生的这一幕,天上一群群飞来飞去的鸟儿们叫他们既兴高采烈又心急如焚。鸟儿们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飞翔,可就是不落地,他们支起的黑色丝网形同虚设,鸟儿们看都不看一眼。好在他们早有心理准备,随身携带着扑克,闲得无聊之时,便席地而坐,打扑克消磨光阴,等待着鸟儿们下落的时刻,因为他们知道,再能的鸟也不会永远飞在天上。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晚霞烧化在蓝天里,风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刮起,忽轻忽重的风声使黄河坝区显得更加安谧。
鸟儿飞得再高,这个时候也要落枝栖息了。它们鸣叫着,在天空中交谈着,然后振翅飞向有王利东躺着的大沟旁的树林里。
王利东并没有发现鸟儿们的到来,鸟儿们欢快的啼鸣只能叫他的昏睡更加深沉。他挣扎累了就不再挣扎,口腔里的手机将他的嘴撑得大大的,使他面部的肌肉几近僵硬。他的呼吸还算通畅,两只鼻孔眼里不断有鼻水流淌出来,嘴巴的周围已经沾满了枯草,就像一个做工粗糙的燕窝。在他所有的努力失败之后,他突然便困乏至极,怒睁的双眼顿失光泽,他昏睡过去。
网鸟的老农们终于等到了鸟儿们下落的时刻,他们收拾起扑克,顺着鸟儿的去向,在大沟旁的树林里支起了网,并向大沟走来,准备以吼声将鸟儿们轰起,扑向那张黑色丝网,以便使他们不至于空手而归。
王利东嘴中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把他吓醒了,他一个愣怔,想爬起来,却再次没能如愿。手机嘀嘀嘀的鸣叫声在寂静的傍晚清脆而响亮,红灯透过胶带频频闪烁着,将他打扮成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
这是王利东的母亲打来的电话,按照平时的约定,王利东每天的中午和晚上都要往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而今天却没有。王利东没有回电话,他的母亲顿时有一丝不祥之感涌上心头,自从儿子开上出租车,她和老伴都在担惊受怕中生存,报上每一条关于出租车被抢司机被杀的消息都会使他们几天几夜难以合眼,他们天天都在面对苍天真诚地祈祷儿子平平安安。十分钟过去了,儿子还是没回电话。这时,他的母亲就把老伴也叫到电话机旁,等待着儿子迟迟不回的电话。又过了五分钟,王利东的母亲终于等不下去了,一连打了十几遍,然后一腚坐进了沙发里,看着挂在对面墙上的石英钟愣神。
王利东嘴里的手机拼命地鸣叫着,他好像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再次鼓足勇气挣扎起来,因为他知道,这时天色已晚,如果他再不被人发现,他就会冻死在这条大深沟里。
站在沟沿上正准备张嘴大喊的一个老农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听到过好多鸟的叫声,他甚至可以通过鸟的叫声判断出它是一只什么鸟。而这只鸟的叫声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奇怪的令人胆战心惊。那么,这是一只什么鸟?他抬头看着树枝,树上却没有鸟。他稳了稳神,侧耳聆听,却发现这声音发自身后的大沟里。他回过了头,寻声望去,便看到了一个被五花大绑拼命挣扎的人。他的抱头鼠窜是可以理解的,他一气跑出了十多米,才站下来,头却不敢回一下。
“怎么,看见了狼?”另一个老农见他如此失魂落魄的样子,就走过来,问。
“人!”他失声地说道。
几个老农马上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一带发生的刑事案件他们早有耳闻,只是让他们亲自碰上还是第一次。他们手拉着手,向大沟走去,就像一群刚刚放学的小学生。在大沟沿上,他们还停下了脚步,东看西望了一会儿,发现再没有叫人的东西存在,才向沟底走去。
这时候的王利东已经成了泥猴儿,黄土将他的头发染成了时髦青年的金色,他的眼睛已经被泥沙眯得睁不开了。几个老农战战兢兢地将他身上的绳子解开,撕掉了他嘴上的胶带,他想站起来却怎么也站不起来,四肢麻木的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属于他自己的只有惊魂未定。
王利东得救了,在几个老农的搀扶下,他来到最近的一处派出所报了案,并给父母回了电话,报了“平安”。他破财免灾,大难不死,实属万幸。
三天以后,水城的公安就破了案,三个冒充大学生的外地劫匪悉数被擒,而他的出租车早已被他们卖掉,一时难以追回。无车可开,王利东失业了。经历了这次劫难的王利东就像真的死过一回一样,他的脑海里始终有黄军大衣手中的那杆猎枪闪现,驱之不去,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无论是王利东自己的父母还是女朋友娟,在看到死里逃生的他时都是号啕大哭一场,然后跟着的就是责难。你为什么去?出了那么多事你就一点儿不知道?你就不长个心眼?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你要是真是把命丢了还让这些人怎么过?这些你就没想到?
一时间,王利东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只对酒感兴趣,在醉意朦胧中,那杆猎枪便会紧握在他的手上,使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与尊严。在他醒酒的时候,他甚至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想法,他要拥有这么一杆枪。这样,他就天下无敌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王利东的这只破烂不堪的手机救了他的命,它成了他的护身符,清脆的鸣叫与闪烁的红灯是他生命的旗帜。
现在,当马大刚发来的短信的时候,王利东掏出这只手机,用充满酒气的嘴深情地吻了它一下,然后给马大刚回了电话。马大刚告诉他,他正和几个哥们在英雄山下吃羊肉串,让他马上过来,因为有件事情求他帮忙。
王利东出现在马大刚的眼前时,马大刚都没敢认他,他一副无精打采半死不活的神态,叫人想起了重霜打过的秧苗。
“怎么了,哥们儿?”马大刚拍打着王利东的肩膀,将他的几个哥们介绍给王利东之后,说。
王利东在小马扎上坐下来,端起马大刚的啤酒杯子一饮而尽,说:“你说怎么了?我操,倒霉!”
马大刚想王利东能有什么倒霉的事儿叫他如此萎靡不振呢?是不是那个叫娟的歌女又被别人撬走了呢?现在的女人多的是,还非要一个歌女娟吗?
“倒什么霉?王利东,告诉我。”马大刚抬眼盯着王利东,手在腰部摸了下,说,“我帮你摆平。”
王利东发现马大刚的腰部有个硬邦邦的东西别在那儿,他马上意识到,枪,这是一把枪。
“叭!”王利东大喊一声,做出射击的手势。
马大刚被王利东的举动吓了一跳,他一把打掉王利东高举的手,说:“王利东,别瞎闹,先告诉我你倒的什么霉?”
王利东向马大刚要了一支烟,点上,猛吸一口,然后就把他差点送命的事说了。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不是强盗就有强盗来欺负你。”马大刚咬了口羊肉串,又抬手一指身边的一个哥们儿,说,“他叫杨威,可现在是阳痿了。他跟你差不多,前天去德州一个地下赌场赌钱,叫人家敲诈了三万块,还挨了一顿胖打,这不找我来了。明天咱们带上几个哥们儿杀到德州去,给他把钱要回来,再捎点利息。我们没会开车的,想起了你。”
“我的车不是叫人抢了吗?”王利东一听这种事情就紧张,说。
“我们有车,就是不会开,或者说,开不好,怕半路上出事,才让你帮忙。”马大刚龇龇牙,说。
尽管王利东产生了拥有一把枪的想法,但他只是一种想法而已,他并不想与马大刚有什么过多的交往,因为他知道,马大刚现在的名声已经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栽进去。
“不,马大刚,这种事我不想掺和。”王利东歉意地说。
“操,王利东,你吓傻了是不是?只让你开车,别的事不用你管。刚才的话就算我没说。我要到德州谈个生意,雇你跑一趟,总行了吧?”马大刚说。
“雇我?”王利东不明其意,说。
“对,雇你,跑一趟德州来回一千块。你干不干?”马大刚强调说。
一千块?王利东再次被金钱所诱惑了,为了钱而吃亏的人很少有接受教训的,好了伤疤忘了痛多半是指这种事,所以才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俗语。
“我只是开车,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管。”王利东弹掉烟蒂,说。
“对,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管。来吧,为了友好合作,干杯!”马大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