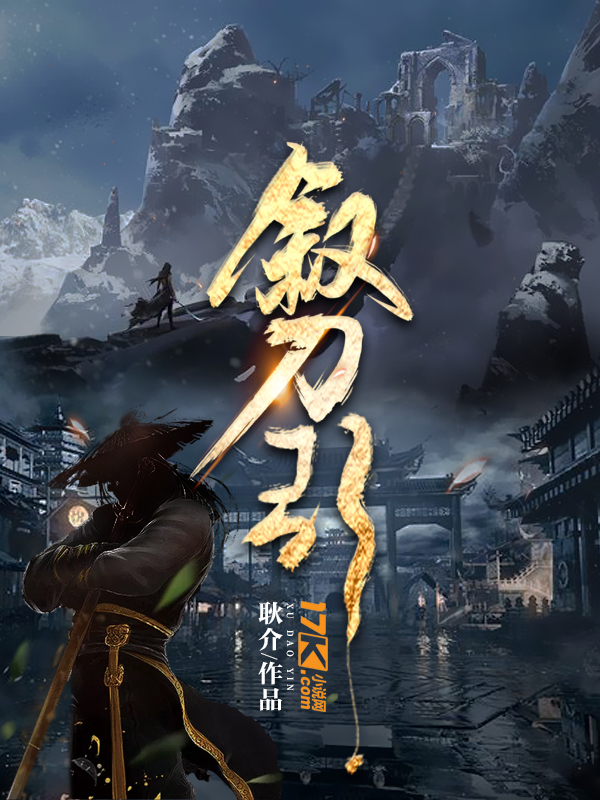这大街上并不是所有衣着光鲜的人都像这些少爷太太们一样,也有些腰上挂刀的人,还有些背上插剑的人,看上去也像是江湖中人,大多都板着面孔,严肃就严肃吧,但那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人家欠了他们很多银子似的,其实是人家欠了他们一刀,他们欠了人家一条命。
更有一些拎着一块香喷喷的花色手绢站在一个敞开的大门外嬉皮笑脸地招呼着过路小青年的年轻女子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花里胡哨,妆化的跟千年老妖或是百年狐狸似的,还没到得近前,就能隐隐闻到一股子混合着檀香杏仁臭豆腐爆米花的狐臊味。
其实,天下不凡逐臭之人,有些人就是喜欢吃臭豆腐,不臭还不给钱呢,越臭越好吃,越臭吃得越香,但越臭却并不是越多给银子哩。有些人便走了过去,像是闻着味儿过去的,这些人自然也是些衣着光鲜的人,他们一把搂住一个年轻的百年狐狸,咧开大嘴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嘴的金牙或是蛀牙,然后便转身从那扇敞开的大门走了进去。
大家要问这扇大门里面是什么光景,请看门楣,上面赫然刻着三个鎏金大字——怡香院,也就是青楼勾栏,俗称大妓院。
这里也是个繁华的所在,也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的天空也是蓝的,这里的树木也是苍翠的,这里的房屋也是土建筑,这里的小姐也是名不虚传的小姐。在这里也可以享受很多,只要你有足够的银两,也可以吃上山珍海味生猛海鲜瓜果梨枣,也可以买到绫罗绸缎真皮外套蚕丝裤衩子,也可以坐着八抬的大轿,也可以睡最美的娘们。
不多时,那骑着枣红马的两个家伙也停在了那家怡香院门前,早有伙计出来替他们拴好了马。这里居然也有伙计,这伙计居然是个男的。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有人喜欢同命花,自然就有人喜欢龙阳之好,正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三条腿的蛤蟆没见过,但未必就真的没有。
那两人回头看了看大街上来来去去的行人,似乎怕别人认出来,也似乎是怕被人跟踪,随即快步蹩进了那扇大门。他们那一眼显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但有一个探奇的人却正在一家粮店的檐下注视着他们。那是一个女子,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
叶紫梅抬眼看了看那扇大门上面的金色招牌,皱了皱柳叶弯眉,脸色也红了一下,那张美丽的瓜子脸瞬时就像是浸在油里的一张纯白的薄薄的纸。
她刚迈开一条腿,一下子就有人跪在了她的面前,直挺挺的跪着也倒罢了,偏偏那人拱背弯腰像是接下来要磕头如捣蒜。紫梅定睛一看,面目却不认识,但又不自禁地皱了皱那两道弯弯的柳叶眉,此时她的眉毛却像是天上那弯弯的月亮。
那人头发蓬松还打着卷儿,像是已有很多年没洗过头,脸上满是泥垢灰尘,脖子上一道一道的,那是汗渍冲刷污垢所留下的痕迹,显然他也有很多年没洗过澡了。看着他那张小花猫一样的脏脸,却看不出他的年纪,但还是看见他断了一条胳膊。那条空荡荡的袖子紧紧靠在身上,他的一条裤腿也是空荡荡的,显然少了一条腿。
他屁股下面是一个麻绳编织的蒲团,从这蒲团上连着两道麻绳,就挂在他的脖子上。显然,这蒲团对他而言很重要,所以只要他的脖子到哪里,他的蒲团就会到哪里。只是,这蒲团比他的屁股还要显小。
不过没关系,他并不是经常坐着,而是时常跪着。干他们这一行的,除了脸皮比常人要厚,就是要经常跪着作揖磕头,只有跪着才有饭吃,站起来就只能饿死。尽管这人看上去并不怎么显老,肯定也有不少力气,但他少了一条胳膊断了一条腿,那想来也是一条很粗壮的大腿,大腿上也会有很多茸茸密密的黑毛,跟他剩下的那条腿是一样一样的。
他只是跪着,但没有磕头,也没有作揖,因为他手里擎着一个花瓷大碗,碗边还镶着两朵喇叭花,开得正艳。但碗里却有铜板,已有小半碗,还有一个已经咬了一口的白面馍馍。
女人总是心软,最见不得这种事。紫梅忙从衣兜里摸出一块散碎银子放在了那个花瓷大碗里。那乞丐眼里登时放出了光,拿起银子放在嘴边咬了咬,嘎嘣一声,崩掉了一颗蛀牙,也是一颗前门牙,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他像是丝毫都不觉痛,抬起头嘿嘿一笑,然后把银子放进裤兜,随即拍拍屁股站起身,喜滋滋地扭头跑了,连声谢谢都没说。他是用两条腿跑的,甩开两条胳膊,飞也似的跑去了,连那个花瓷大碗都丢在了路边,几十个铜板滚了一地。
叶紫梅直是哭笑不得,刚叹了口气,便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蜂拥着去抢夺那满地的铜板,很快便扭打成一团,其间还有几个满脸油污的半大孩子。叶紫梅禁不住又叹了口气,随即迈步向前走去。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街上的行人也渐渐少了。叶紫梅拣了个阴影处,飞身上了房顶。她猫着腰,踏瓦而行,脚下却不起半丝声响,轻得像是二两棉花。
她知道像那两个骑枣红马的家伙绝不会在普通的房间,何况为了见他们的少主,必是在楼上的雅间。怡香院也不过是个二层的小楼,几十个房间。叶紫梅没走出几步,就会俯下身将耳朵贴在瓦上倾听,然后再往前走去。
突然,她止住了脚步,并轻轻挪开了一片瓦,房间内的一切尽收眼底。
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直是一个大厅,光八仙桌就有两张,花梨木的椅子也有十几把,橱柜都是崭新的,像是刚装潢的新房子,极其考究且有些金碧辉煌的味道,就连那盏灯的样式都是一般小镇上买不到的,那是一盏七彩琉璃灯,散发着橘红色的微光,房里便有了一丝朦胧的春意。
在怡香院里岂非到处都是春意?
然,房内什么家具都是一应俱全,却偏偏没有床。
怡香院是个什么地方,最不应该少的就是床呀,怎会落下了这最应用的东西呢?
更奇怪的是,房里也没有女人,只有男人,一个白净面皮的汉子,看上去至多三十来岁光景,隆准方正,萧疏轩举,脸刮得很干净,连那胡子渣残留的痕迹都看不出来。他头戴儒巾,身着一袭白袍,眼神明亮,处处透着一股子潇洒干练劲儿,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书卷之气。
此人没有携带兵刃,就像是个进京赶考的秀才,正在挑灯夜读。此刻,他也是正端坐在桌前,但没有读书,而是自斟自饮,喝的是上好的香茗。
他像是正在等人,显然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但一点焦急的神情都没有,脸上还流露出一抹淡淡的悠然。
他在等谁?他在怡香院里还能等谁?哪个窑姐有这等魅力,竟让一个读书人如此等候?
紫梅刚有了这个疑问,门上便响起了剥啄声,声音很轻,但那书生还是听到了,他等的人儿终于来了,紫梅不禁瞪大了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那两扇朱红漆的房门,她也想见识一下这书生要等的究竟是个怎样的美人儿。
这书生起身走出两步便驻了足,竟没有开门的意思,他冲着房门低沉着嗓子吟道:“一骑红尘妃子笑。”
这是一句唐诗,下一句自然是“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书生不愧是个书生,都这当口了还在卖弄斯文。熟料,门外传来了一个粗沉的男子声音:“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简直驴唇不对马嘴。然,那书生却像是找到了知音,登时满脸堆欢,上前拉开了房门。从门外走进了两个人,借着橘红色的微光,紫梅看得真切,正是那两个骑枣红马的人,也就是那个身躯高大的国字脸和那个尖嘴猴腮脸上有个拇指般大的红色胎记的人,紫梅跟踪的正是他们。
这两人刚走进去,那书生便关好了房门,关门前还探头望了望外面,显是怕有人看到。做这种事当然怕别人看到了,何况还是个书生,更何况是三个男人一台戏。
那书生回过身便一抱拳:“两位兄长一路辛苦,快坐下喝杯热茶吧。”
那国字脸哼了一声,眼神甚是轻蔑,也不答话,大踏步过去,自斟了一杯热茶,跟着一饮而尽。
那胎记却是和气多了,也是拱了拱手,说:“狄掌门久等了吧,小弟在此赔罪了。”
“不敢当,”那书生赶忙回礼,“折煞小弟了。在下久仰郑兄的威名,今日有幸得见,实是快慰三生啊!”
“狄掌门客气了。”胎记笑着说,“我没记错的话,好像狄掌门还比小弟年长几岁吧,那以后小弟就直接叫大哥了,怕是以后还得多多仰仗大哥呀。”
“郑兄弟快别这么说,太见外了,如有需要尽管吩咐,狄某无有不从。”那书生又拱了拱手,但也没再拒绝“大哥”这身份,脸上带着谦恭的神情。
“还是大哥忒见外了,小弟很是佩服大哥,今天见了面,说什么也得多亲近亲近。”那胎记仍是笑着说。
他虽然是一副尖嘴猴腮的模样,但那对乌溜溜的眯缝眼始终眯缝着,给人一种慈祥的感觉,像是一直在笑,他不笑的时候也像是在笑,也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不笑了。就是这种人最难缠也最阴险,通常是口蜜腹剑,谈笑间杀人于无形,也便是俗语所说的“笑面虎”。
“佩服我?此话怎讲?”那书生微蹙着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