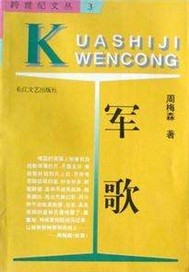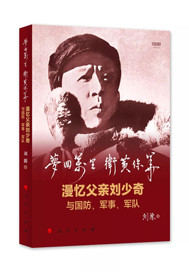说话来这店中的军官,却大有来头,原来是转任到保靖任达鲁花赤,名叫乌兰特,眼见这女店主柳江红颇有姿色,便乘着酒兴,欲行非礼,柳江红奋力挣扎,这乌兰特便想用强,却猛听一声怒吼:“畜牲!快把人放开!”这乌兰特一听,转眼一看,就见洪可郎物持长剑,怒气冲冲地立在他的面前。
这乌兰特自南下以来,还没有一个汉人胆敢如此对他这样说话,而且还手待凶器,一时愣了愣,待反应过来,不觉哈哈大笑,道:“今天是什么日子,遇到疯子了!”身边的几个元军见状,就挥刀上前砍来,洪可郎初生牛犊不怕虎,盛怒之下,哪管许多,杀心顿起,一时剑光刀影,不几个回合,便见两个元兵中剑而亡。乌兰特一见,大吃一惊,放下了柳江红,持了腰刀,如疯子一般向洪可郎扑来,洪可郎以剑相迎,见这乌兰特心急气燥,恨不得立时将对手置于死地,只好先是步步躲闪,不想对方步步紧逼,又见柳江红已吓得晕倒在地,一时气极,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大喝一声,手中的剑如电闪雷鸣,就听乌兰特一听惨叫,前胸已是中剑,血流如注。一旁的几个元兵一见,先是惊得目瞪口呆,接着也是呀呀叫唤着,一齐挥刀杀来。洪可郎已是杀得兴起,身似脱兔,剑如精灵,不到片刻,又一名元兵中剑倒地,一名元兵被刀砍掉一只左手,惨叫哀嚎。另两名元军见状,才知不是对手,正要夺路出逃,洪可郎哪容得他们逃出,一个箭步拦住了去路,两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便丢下了腰刀,双双跪地,连连作揖,道:“壮士饶命!”洪可郎一看,便收了剑,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敢来骚扰我店?”原来这两人也是汉人,一个叫薛豹,一个叫范林,这薛豹道:“刚才壮士杀的人,是来保靖上任的达鲁花赤,名叫乌兰特,我们几个都是护卫,护送他来此上任的。”
一时柳江红已醒来,一见这场面,又是差点晕了过去,还疑心自己在做恶梦。谁能想到,这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少年,竟有如此胆量和功夫!见可郎正在盘问两元兵,忙上前道:“这祸闯大了,你赶快逃了吧,要被官府晓得,怎么得了!”洪可郎哼了哼道:“我走了,你们怎么办?我堂堂一个汉子,怎能丢下你不顾而自己逃命!”柳江红只得劝道:“这祸也是由我而起,哪能连累你。”洪可郎道:“这个店,你还待得下去么,不如我俩一起,离开这店,远走高飞。” 柳江红一听,就有些犹豫,这薛豹机灵,却也劝道:“好汉还是快些走罢,要是官军来了,盛怒之下,不仅会杀个鸡犬不留,连这个店子,也会被烧个精光。”范林也点头道:“不光是如此,我等也会性命不保。好汉若是留下我等性命,我等愿意跟随壮士一同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柳江红一听,只是惊慌哭泣。洪可郎跺脚道:“事已至此,保命要紧,哭有何用!快快收拾了东西,赶紧走罢。”柳江红无奈,只得回店里,取了些细软财物及随身物品,洪可郎将柳江红抱上了马,同薛豹和范林骑上三匹快马,乘着月色,飞奔出城。
次日天一亮,店里的伙计回到店来,一见院内情景,早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去报官,保靖官府得知,大惊,忙令副将带领数百官军来到唐家饭店,将饭店包围得铁桶一般,只见乌兰特和几个护卫倒在血泊之中,搜查死者身份时,在那蒙人身上搜到一份上任保靖达鲁花赤的官符和昭书,这副将顿时吓得双腿发抖,忙一面派人去禀告知州,一面带人去追捕要犯。查问各城门官,有城门官禀报,昨夜有三骑从东门往东北方向去了。这副将怎敢迟疑,忙带领官兵向东北急追。幸好这东北方向都只有一条大道,沿大道追了数十余里,就见三男一女正在前面不慌不忙地行走。原来洪可郎出城后,因走的是夜路,只得沿着大道出逃,行走缓慢,天亮后又到一路边店吃了早餐,饭后上路,走了不久,就见后面尘土飞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洪可郎晓得是官军追来,见摆脱不了,只好对薛豹和范林道:“你们两个好好保护江掌柜先走,我来对付官军。”柳江红一听,道:“官军人多,你怎能对付?不如放下我,你们逃命吧。”洪可郎哪里肯听,一面吩咐薛豹等快走,一面调转马头,立马持剑,拦在路中间。
这副将一路追来,见一年轻人单身匹马,拉住去路,不禁惊疑,喝道:“你可是杀害达鲁花赤的凶贼?”洪可郎一听,冷笑道:“我不晓得什么达鲁花赤,只要见到有哪个欺负良家女子的,我必诛之!”这副将一听,不禁大怒,喝道:“好个逆贼,胆敢杀害官军,今日只好提你这头去祭乌将军了。”说罢,提抢杀来,洪可郎挥剑相迎,两个约斗十个回合,那副将哪是他的对手,被洪可郎一剑斩于马下,见这副将手中的长枪不错,便跳下马来取起长枪,又上了马,大吼一声,向官军杀来,这群官军见为首的副将被杀,早已吓破了胆,哪里还敢上前,又见他虎啸般吼着杀来,只恨爹娘没多生几条腿,打马回逃,转眼间已逃得无踪影。洪可郎见官军逃走,便打马向柳江红三人赶来,却见柳江红等三人并没有走远,而在后面远远看着,亲眼见洪可郎杀退了军官,三人面面相觑,惊叹不已。
洪可郎等为了逃避官府追捕,一路马不停蹄,昼夜行走,路经古丈、卢溪、辰溪、麻阳,行走半月有余,来到了黔阳交界之处。柳江红道:“这一路奔逃,总得有个尽头,我实在受不了了,不如就在这里找个地方落脚罢。”洪可郎点头道:“我等走了这么远,想官军也难寻了,到了这县城,不再走了。只因我的缘故,让姐失了祖传饭店,我也于心不安,不如就在这县城重操旧业,开个饭店如何?”薛豹一听,摇了摇头,道:“少主人,这饭店之事,是万万开不得了,若是开了饭店,人来人往,难免不被官府发现。”洪可郎一听,也觉在理,只得罢了,薛豹道:“小的有个念头,不知少主人见纳否?”洪可郎道:“你有何想法,但说不妨。”薛豹道:“我闻知衡州有股义军,已聚集数万之众,专门同元军和官府作对,攻城拨寨,一路所向无敌,少主人有如此功夫,不如继续南行,去投奔衡州义军,如何?”洪可郎一听,只得依了,便动身向衡州进发。
四人一路行来,到了黔阳与麻阳的交界之处,却又遇上了麻烦。原来此处有一个山寨,山寨为首的头领叫陈郁,纠集了一伙土匪,约有上百之众,专干抢劫沅水两岸的商客,有时也与船排帮作对,后杨蛟龙做了船排帮主后,整合了辰溪和黔阳的沅江水路船排帮兄弟好几百人,势力大多了,这陈郁便不敢与他们作对,只做陆上生意。这天探子来报,说有一行商客三男一女,三匹好马,那个女子还很有姿色,是位千众难寻的美妇。这陈郁一听,哪有不动心的,便喜孜孜道道:“今天一大早就听到门前喜雀叫唤不已,原来有这大喜之事!”忙吩咐手一下个小头目,集合山寨数十个喽啰下山,连人带货劫上山来。
这洪可郎走得正忙,哪知被这寨匪拦个正着。范林上前一看,情知不妙,只得上前拱手道:“请问是哪路好汉,我们乃过路的行人,并无钱财,可请好汉高抬贵手,借路让行?”这小头目一听,哈哈笑道:“这人好不识相!我都要凭你这几句话,就放了你等过路,我山寨这么多人,岂不活活饿死!你要懂事,乖乖随我等上山,免得吃亏。”洪可郎一听,火冒三丈,正要上前出手,薛豹忙拦住道:“少主人先别急,这个拦路的只是山寨一个小头目。主子还未登场。先让范林去收拾那厮就是。”洪可郎便点了点头。范林便打马冲去,为首的土匪和几个喽啰围上来便与范林厮杀,那小头目斗过数招,不是范林的对手,慌忙逃窜,范林也不追赶。薛豹道:“那寨主很快就会下山,我们若要走,这里路况不熟,他必然会在前面要害之处截我,不如我等找个四通八达之地,等着他们,即便打不过他们,也可夺路而逃。”洪可郎看了看前面的出路,只见前方山恋重重,道路通向山谷深处,深不见头,只好依了薛豹的话,寻了个开阔之处,等候那寨主找来。
不多时,果见陈郁率领大批喽啰,从前方道上回找过来,见了洪可郎等,喝道:“谁敢在本大王的地盘上行凶,是不想活了么!”洪可郎一见这大王,却也是个五短身材,腰粗如柱,面黑如漆,身着黑裤短袄,脚登豹皮短靴,肩扛宽叶大刀,蓬头散发。洪可郎便对薛豹道:“你与范林只管好好看护江掌柜,我去捉拿这黑鬼。”便打马上阵前,冷笑道:“你是哪里跳出的夜叉鬼,敢挡爷的去路。”陈郁一听,大怒,也不打话,挺刀杀来,洪可郎也挥舞刚取得那杆水磨钢枪相迎。好一场厮杀。但见得:
一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一个自幼拜师艺成下山,一个手持大刀气势汹汹,一个水磨钢枪咄咄逼人,一个要夺路出走,一个要拦路抢劫。刀枪相拼金光闪,生死相拼杀声厉。
两个一气之下斗了十来个回合,只见那陈郁一把宽叶大刀使得呼呼作响,再看洪可郎一杆水磨钢枪犹如急风暴雨,又战几个回合,那陈郁已是汗流如溪,如同河中水鬼,自知不敌,便想弃阵而逃,洪可郎哪里肯罢休,大喝一声,一枪挑去陈郁的宽叶大刀,就见那大刀脱手抛上空中,落入江里,洪可郎猿臂一提,生生将陈郁活捉过来,令范林和薛豹捆个结实。洪可郎便对众喽啰喝道:“还有何人上来送死!”众喽啰一看,吓得纷纷丢下兵器,跪地求饶。洪可郎便命众喽啰带路,押了陈郁,走上山来。
一时上了寨,看这山寨是一排排吊楼木房,打扫得到也干净,寨内钱粮富足,五谷油盐,也够一百多号人吃一年有余,抢得的金银珠宝也不少。到了山寨,看前方是一片丘陵,山川河道尽收眼底,田野村舍,炊烟袅袅。洪可郎不禁羡慕,道:“陈郁这厮到有些眼光,会挑地方。如果去掉匪气,这里到是个神仙居住之地。”便对薛豹、范林道:“我等有这么个好地方,还去投什么义军!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如何?”薛豹、范林哪有不依,一个个欢喜点头。柳江红一听,又是犹豫,道:“如此一来,我等不也成了打家劫舍的土匪了么?”薛豹道:“夫人有所不知,如今这乱世,官府贪婪,官兵欺压,土匪横行,有多少良民百姓不都被逼成了土匪!何况我等已是官府追杀之人,不占山自保,哪里还有我等容身之地!”柳江红一听,无言以对,只得认了。
这洪可郎便上得厅来,坐上了陈郁的太师椅,令喽啰把陈郁提上堂来,洪可郎一见陈郁还被捆得像粽子一般,一时也怜他,忙亲自为他解索。道:“小弟出手得罪,还望陈头领见谅。”那陈郁见状,便叹息道:“我陈某自立寨以来,还没有受此屈辱,壮士功夫如此高强,今日我输得心服口服,壮士既不杀我,从今以后,愿随壮士左右,绝无二心。”洪可郎哈哈笑道:“陈头领有所不知,我洪可郎只是为了我夫人,杀了官军,才逃难至此,小弟只想借这栖身之地,过个安静日子。这山寨是陈头领一手所创,还是你作主罢。”陈郁一听,摇了摇头,道:“壮士这等说,陈某就更无地自容了。壮士生擒陈某,山寨众兄弟已是亲眼所见,陈某如此败相,还有何面目身居壮士之上。壮士要是硬要陈某来做山寨之首,陈某无颜面对众兄弟,只好独自下山了。”薛豹一听,只得劝道:“小主人,陈头领一片诚心,我看就别推辞了。小主人就做个大头领,让陈大哥就做个二头领吧。”洪可郎还想推让,就见陈郁高声对众喽啰道:“快快请各位兄弟进厅,拜见洪寨主!”在下的众喽啰一听,慌忙呼地跪倒,齐声喊:“拜见洪寨主!”洪可郎见状,只得从命,命陈郁做二头领,薛兄与范兄分别为三头领和四头领。一并让柳江红做了个压寨夫人。”众喽啰一听,欢声雷动,柳江红哭笑不得,只得认了。陈郁也是欢喜,令大摆筵席,欢迎新寨主。
洪可郎自从当了两界口山寨的大当家后,不到半年,名声大震,不但打败了杨蛟龙的船排帮,就是官军的粮食物资在这沅江通过,他也敢抢,并没有哪个能斗得过他。山寨从上到下,对洪寨主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天探子来报,说是杨蛟龙的船排帮接了一趟大买卖,有五六十多匹好马,装载了不少钱财,现已分成几条大船,逆水而来。洪可郎一听,不禁惊疑,道:“自从我打败了这杨蛟龙的船排帮,数月来再也不敢从这水路做如此大的生意,难道这姓杨的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么?”薛豹头脑灵活,极有心机,洪可郎封他为军师。他一听,也道:“这杨蛟龙能接下这桩大买卖,必有强人联手,要不然,就再借他他杨蛟龙十个胆子,也不敢在这两界口做这笔生意。”陈郁道:“如此说来,这趟买卖不做了?”洪可郎哼了哼道:“管他强人不强人,他要敢做,我就敢抢!”薛豹道:“虽是这等说,我们也得留个心眼,多防备几手。好在这船是逆水而行,必由纤夫拉行,我想在杨蛟龙船队来到两界口之前,大当家和二当家各带一支人马,分别埋伏江面两岸,待船队到了伏击点,先放炮,我炮声一响,船上的马群必受惊跳入江中,我等再将在江边拉船的纤夫抓住,拉住纤绳,把控了船只,将船拉向岸边,再一面多准备弓箭和投石手向船上的人投射,一面派出善游水的兄弟,游向船上,制服船上的人,防止船上的人丢货毁船,同时把江中的马匹弄上岸来,以保劫货顺利得手。”
洪可郎一听,连连点头,便道:“此计虽好,只是这江面宽阔,投石手无法投及。”薛豹道:“此事不难,可令投石手站在两岸高处,多备绳索,梱上石头,手持绳子一头飞转抛射,可比平常抛石要远数倍。”洪可郎一听,大喜,道:“就依薛兄弟之计而行薛兄弟负责放箭投石捉拿马匹,范兄弟看守山寨,你等各自准备去罢。”众人领命,各自准备,不提。
且说杨蛟龙得知碧云、刘尚等身份,又拜了兄弟,对护送孙碧云等人自然万分小心,不敢丝毫马虎,自己亲自出马,从船排帮几百弟兄中挑出了一百五十个扦夫拖船,一百水手划桨,五十人看马护船,一切安排就位。就请刘碧云、刘尚等如何对付劫匪商量对策,刘尚问道:“我等在船上的马匹若遇到劫匪袭击,如何使马不受惊吓,跳水逃命?”杨蛟龙道:“这到不难,这些马匹分别装在几条船上,每条船上固定两排木桩,可把马匹扣在木桩旁,分别由船排帮水手负责看护,前后由两条船保护,中间一条大船给兄弟们乘坐。”刘尚点了点头,道:“江上行船就由大哥和四弟负责,保护盟主和两员女将就由方云负责,再挑选一班水性好的兄弟协助。我与兴阳各带一队人马,沿劫匪活动区域的两界口江岸悄悄跟进,一旦发现劫匪出现,你们只管前行,我们来对付他们。”杨蛟龙一听,大喜,道:“如此安排,我心里就有底了。”于是刘尚吩咐,众人二更造饭,三更出发。杨蛟龙点头应诺。
一时船队按时启航,当夜正遇顺风,船行得快。到了第三天下午申时,就进入到两界口,刘尚、兴阳等也悄悄分别在沿江两岸跟船而行。杨蛟龙亲自坐在船头,细心观察动静,此时已是无风,便命纤夫进入两旁水中,拖船行驶。
正行进间,就听轰地一声炮响。船上的马匹听到炮声,一匹匹跃动嘶鸣,好在其被紧系木桩上,动弹不得。杨蛟龙心里早有防备,也并不惊慌,一面向两旁的纤夫和后面船只发出信号,河岸两侧的纤夫一听信号,忙弃了纤绳,向江心船中游来,杨蛟龙令一面紧抛锚,防止船顺水失控逆行,一面令砍断纤绳,防止被两岸的劫匪将船拉向岸边。此时,就见沿江两岸,无数支弓箭向船队射来,接着又是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投向船队,杨蛟龙冷笑道:“这些旱鸭子,也只会这点本事!”便忙命水手取了盾牌,护着左右和头上方,因江面宽阔,那弓箭射到船中,已劲力大减,只是那石块凶猛,就有数人防备不及,被砸得头破血流。就听洪可郎和陈郁各带一队喽啰从两岸上齐声向江中呐喊:“杨蛟龙休走!”紧接着一队懂水性的喽啰,个个喝足烧酒,向江中游来。船上的碧云、方云及两位女将,怎肯放过这杀匪的机会,就见碧云、月芳的飞刀一片片闪电般飞去,方云及两位女将挥舞兵器,见靠近一个杀一个,刹时就见江面被血染红,杨蛟龙吩咐船排帮兄弟全力保护好盟主,决不能让匪徒靠近盟主所乘的船只,并亲自带一队水手跳入水中,与土匪搏斗。
刘尚与易兴阳听到炮声,晓得杨蛟龙、方云等与土匪接上了火。两人分别从左右两岸向两界口奔来。右岸易兴阳遇上陈郁,见是一个蓬头散发面如锅底的五短粗汉子,一把宽叶大刀在太阳光下照射闪闪放亮,不禁大笑,道:“这是哪里来的杂毛黑鬼,我当是个叫化子哩。”陈郁一见对方又是一个比自己少得多的年轻人,这样嘲笑自己,不禁气得怒气冲天,火冒三丈,喝道:“哪里来的蟊贼,不知天高地厚,敢来戏弄老子,你死到临头了。”说着挥刀砍来,易兴阳一杆长矛接住陈郁的大刀,两人过了十余招,陈郁见对方手段高明,不是他的对手,正准备逃离,哪知兴阳早已识破他的动机,一杆长矛步步逼紧,不离陈郁前后左右,杀得他是拼不过逃不出,满身臭汗,透湿数层衣甲,已是狼狈不堪。想丢下大刀向对方屈服,然一个做了十几年的山大王,当着众喽啰之面,哪里拉得下这个脸面,只好以死相拼,易兴阳斗得了个不耐烦,一声怒吼,如似雄狮啸山,猿臂一伸,把陈郁高高提起,然后用力一抛甩在地下,叫人捆了。可笑这山大王,不上半年,又活活做了一次俘虏。
左岸的刘尚,正遇上洪可郎。刘尚曾听杨蛟龙说起这人武功了得,今日一见,真是英雄出少年,高鼻虎眼阔面,身着一身紫色战袍,头顶一块白色绸布,骑着蒙古马,手持一杆水磨钢枪,耀武扬威。这洪可郎一见刘尚,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汉子,年方三十有余,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手持一杆三尖刀,晓得此人必有些来头,便道:“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我洪可郎的枪,不杀无名之辈。”刘尚一听,不禁呵呵大笑,道:“见你小小年纪,口气倒不少,我也不想让你年纪轻轻就死在我的手中,若识趣,就放下枪,有话好说。”这洪可郎哪知高低,也是没有遇过对手,不免狂妄,冷笑道:“就听你说的这些狂话,我岂能饶得你!我倒要看看,今天是到底谁死在谁的手中!”说罢,挺枪来战,刘尚一听,只得挥枪相迎。只见得:
巍巍两界山,映照双枪闪银光;滔滔沅江浪,奏出两将吼声急。一个南山猛虎,双臂似虎爪盖天扑,一个北海姣龙,两手如巨掌铺地擒,一个游僧高徒,学尽天下奇功;一个石洞少侠,练出盖世深功。直战得,两岸猿猴满山惊,江中鱼鳖遍水逃。
两个各施手段,一气之下斗了约三十余招,不分胜败,刘尚不禁暗暗称赞,这少年功夫,还真是名不虚传,不仅力大无比,还枪枪点滴不漏,不免有心想收这少年入义军的念头,便是攻少防多,不相伤害他。只是如此一来,要想取胜他,也还要费些功夫,二人只在厮缠不停。
此时,碧云、方云、月芳、小红、杨蛟龙等人早已打退前来上船打劫的水匪,上得岸来,把薛豹所带的喽啰杀得四处奔逃。易兴阳押着陈郁来到右岸,同碧云、方云及月芳、小红会合,观看刘尚与洪可郎厮杀。易兴阳见刘尚久战不下,按捺不住,就要上前相助,被碧云阻止道:“我见刘尚战那对手,明显是故意让着他,想是有意不伤害他,有收服其为我所用之意,我等只在些观战即可,不可相助。”兴阳一听,方罢了手。
一时薛豹见势不妙,忙逃到山上禀报夫人柳江红。柳江红闻知二当家被捉,其他兄弟败下阵来,自己男人还在同对方厮杀,不分胜败,急得眼冒金花,半天说不出话来,当转过神来时,便道:“你快快领我去江口观战,要死,我也要同他死在一处。”薛豹劝阻无用,只好领了柳江红往江边奔来,见沿江两岸,全是黑压压的船排帮兄弟,那洪可郎正与对方厮杀拚命,眼见自己的男人已不是对方的对手,危在旦夕,忙问薛豹:“这对手竟是何等人,如此厉害?”薛豹道:“我隐约听人说,他们好像就是衡州义军的人。”柳江红道:“你不是说过,原要去投奔这衡州义军,为何还要同他打斗?”薛豹道:“先前哪里知晓,现已惹了祸,他们还能放个我等?何况,还不一定认定就是衡的义军。”柳江红一听,救男人要紧,哪顾得了许多,急忙奔扑到阵前,喊道:“可郎和那英雄请住手。小女子有话要说!”那洪可郎战到此时,已知自己不是这汉子的对手,再战下去,必死在这汉子的手下,又碍于面子,不想轻易认输,只得强打精神死顶,一听自己的夫人一喊,想夫人真正是自己的救命人也!正好骑驴下坡,忙收了枪,听柳江红道:“请问这位英雄可是衡州义军。”刘尚一见这妇人也算是一位美貌女子,想应是这少年的夫人,不禁也是称羡这女子胆识,便道:“我便是衡州义军兵马大元帅刘尚也!”柳江红一听,忙奔向刘尚,双膝一跪道:“小女子柳江红向元帅陪罪了!请原谅夫君年少不懂规矩,冒犯元帅虎威。”一旁的孙碧云一看这女子不过二十出头,说话如此口子玲利,礼数周道,胆识过人。忙上前扶往道:“你是这少年的夫人么,怎么晓得我等就是衡州义军?”这柳江红一听,一时止不住泪流满面,道:“夫人有所不知,小妇人一言难尽,请容小女子慢慢说来!”便将自已当初如何经营饭店,如何认得可郎,如何杀了欺负自己的官军,如何前来投奔衡州义军,又如何在半路被劫等等,一一说细细说了。碧云等一听,也不禁心酸,忙令刘尚等放下兵器,不可再伤人,那可郎也慌忙放下了枪,向刘尚施礼,道:“小的该死,不知元帅驾到,冒犯虎威,请受克郎一拜。”说着便要下跪。刘尚忙扶起他道:“一场误会而已,不必多礼。”这正是:
英雄斗得鬼神惊,不及弱女问一声,
都是道上落难人,相逢一泣恩怨明。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