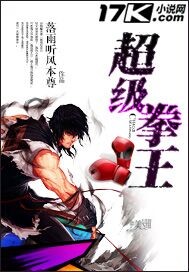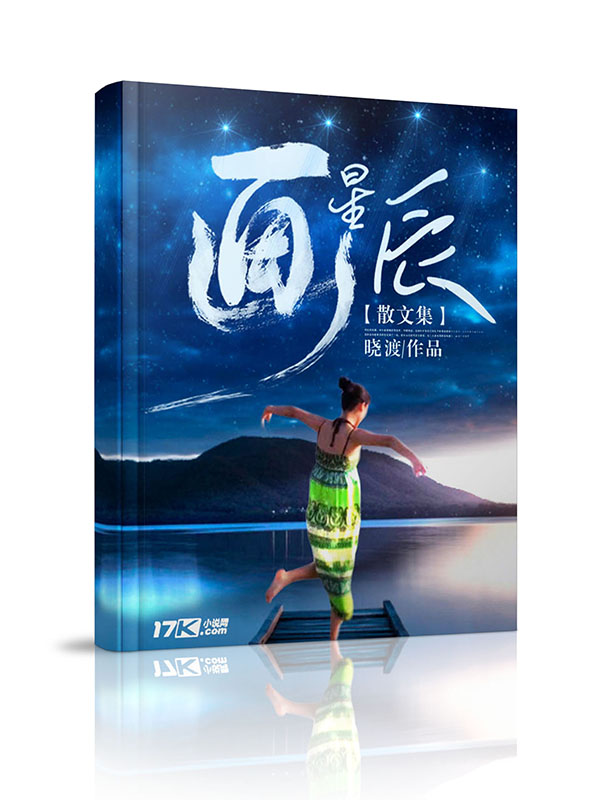他展开手帕,回想起在家时同阿雪朝夕相伴的日子,喃喃念起那首词来:“一路有你,相伴天涯去,畅浪游,两荡天际,心心相偎依。”这是临别在即,他送给阿雪的词,现在他离家出走,当兵作战,至今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家中老父老母固然不知道是何番摸样,便是阿雪,如今也已是四十出头了,恐怕早已嫁为人妇,孩子都有孝义那么大了。
而自己这些年来的牵挂和思念,却无时无刻不在心里作祟,有时这颗心就像是被铁索缠住,不能跳动,疼痛难言。
他想着这些不如意的事,竟是越发精神起来,忘却了连日来的劳顿疲惫。又念起另一首词:“怅望孤鸿,情争乱麻绪,不足取,清清楚楚,看君闯天地。”朝天遥想当日情景,似乎又看见了阿雪那执著的眼神,她是想用一生来等待他回去的,他却已没有力气再回去了,但是无论如何阿雪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即使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她也还是会对他日夜牵肠挂肚的。
想到这里,心里流过一阵暖流,心却越发痛了,他思潮迭起,意念乱飞,时而信感温馨时而又大觉落寞,如此想事情到了半夜,才迷迷糊糊睡去,做起梦来。
梦中自己像是回到了童年,在家里百无聊赖,就跟娘亲说要出去玩耍,方走出门来,见阿雪立在门前,笑看着他。见她一身雪白衣裳,那般美妙的姿势,俏然袅然,笑容甜甜,漫出一股扑鼻的香气,一时竟看得呆了。
阿雪被他看的不好意思,羞怯说道:“你瞧什么,痴痴呆呆的,以后便叫你作发呆吧。”朝天道:“我在瞧你的样子,一身衣裳洁白如雪,笑容圣若白菊,你恐怕一生和这白字断不得干系了。”阿雪道:“我这衣裳不好看么?”朝天笑道:“好看是好看,只是让人难以接近,就连碰你一下,都恐弄脏了你的衣服,玷污了你的高洁。”
阿雪道:“你只管吹牛,就不怕别人听了会笑话。”两人相视一笑,一起散步谈心。过不多时,听得有人说村东八里有余的蒋氏村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两人游兴大起,相携往去游览,途行八里,很快到了蒋氏村。两人自村西而入,径往村中走去,见有一条小溪,宽不盈米,深可及腰,两人于是鱼贯潜水而行,溪边竖一根铁丝,东西向贯穿而上,似乎专供游人顺溪潜行之用。
半时,来到村西前面,有几个场院,地形颇似地庄村前一带。两人游兴正浓,见场院边上有大石数十块,于是跳上去玩耍,不意石下竟发出“隆隆”响动,展眼间,大石尽数变为石棺,棺盖轰响,死尸将要顶翻棺盖而出。朝天急急牵着阿雪的手,大喊快跑,两人径直向村东逃窜。村东有一条南北向的大街,街上铺位栉比,却阒寂无人。
两人走到大街南端,终于看见有两个人正在墙脚挖洞,待上前看时,确是宋小胖和焦贵。小胖见了他急忙向他要酒,朝天拿出挂在腰间的酒壶递了过去,暗暗奇怪自己怎么出来时还拿了酒壶,心感疑惑,更加奇怪小胖的举动,问道:“你俩挖洞来做什么?”小胖说:“僵尸要来,挖洞好藏身。”喝了口酒又转过身去继续挖洞了。
移时,洞挖好了,几人接踵钻入,朝天却忽然发现身边的阿雪不见了,闻得僵尸群然而来,气势汹汹,心中急如火燎,慌忙又钻出洞去,寻找阿雪,一路跑向村北,见一人迎面走来,朝天看此人身穿漆黑长袍,面色如铁,颧骨高悬,形状有些像花洛。朝天正欲向他询问有否见过一个女孩,那人却怒气冲冲向他扑来,抓住朝天双肩,怒骂连连,状如疯狗,只听他说道:“你知道我们蒋氏村为什么叫做蒋氏村吗?那是因为村中满是僵尸,蒋氏乃是僵尸的谐音罢了。”
朝天更不搭话,心想蒋氏一定会被我们打败,他心中牵挂阿雪安危,只想尽快摆脱开他,于是伸手抓住他的脸颊,用力拉扯,只见他的一张脸,被自己拽得老长,就如两边各一根血管,中间悬一个苦胆一般,即使这般,那疯子犹自疯话连篇,滔滔不绝说个没完。
朝天又用双手抱住了他的头,用力旋转,大约转了两周,把他脑袋转了下来,他才不再讲话了。朝天摆脱开这个疯子的纠缠,又急匆匆寻觅阿雪,可惜遍寻村北仍不得结果,心中正在急切,却见阿雪站在村北山的一处山岗上,见到朝天,忙向他跑过来。朝天拉了她手,又向村南洞处跑去,孰料竟跑到了自己村中,回头一望,那蒋氏村雾气弥漫,已经满村都是僵尸。
两人跑到朝天的姑姑家,见到史劲图正站在姑姑家门口,史劲图在门上挂一个牌子,见两人到来,急急走了,脸上还带着笑意,待看那张牌子时,只见上面写着斗大的“阿雪”两个字,下面有两行小字,写道:“不孝恶人水朝天,离家征战二十年,高堂撒尽哭儿泪,白骨露宿湟水边。”
朝天看后心情大落,又想起母亲来,一时伤感难禁,泪水夺眶而出。阿雪拍了拍朝天的肩膀,以示安慰。朝天却益发伤心了,哽咽半晌,感到头痛欲裂,于是醒了过来。
水朝天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对自己一夜里放松了戒备无奈一笑,骑上青海骢,向南奔行,他想绕道地庄的西泡子,从草帽山侧赶去弯子村,心中推测宋小胖定然藏身在弯子村中,自己也想去看看弯子村的情况。
来到西泡子,见水面上,尚有天鹅戏水,心想在这个时候,候鸟竟还迟迟不想返家,又发一阵感触。
回头,见草帽山山坡上有一个老者,那老者正赶着一头老牛,扶犁翻地。
朝天心道,虽是秋获季节,不少麦田都已收割,正是翻地的时候,但这战乱时期,民不保命,人争相食,四野不见人影,这老者竟还敢只身在旷野翻地,真是咄咄奇事。
他勒马住缰,停在原地,细看那老者,见他双目合闭,却是正在睡觉,那拉犁的老牛,慢慢而走,翻过一遭来,转头再翻一遭,不用人管也能做活。
老者手扶犁杖,跟在后面,边走边睡。朝天看得奇怪,一时也不想走了,呆在原地看了良久。
那老者睁开眼来,扛起犁杖,赶着老牛,说道:“干完活了,咱们回家去。”一人一牛来到朝天近前,也不理会朝天,只顾向路边的一口枯井走去,到了井边,那老者道:“狂沙盖地,怒水朝天,本大凶之相。该干的活都已干完,剩下的自会有人来干,还有什么留恋之处?”说完牵着牛飘然进入枯井。
朝天听那老者所说之话,似乎言外有意,眼见得老者进入枯井,是那么自然和谐,以朝天的性格,竟都未去施救。
苦思半时,也毫无头绪,耳听得后面有大队人马过来,他不暇多想,忙催马躲避,一路驰回孤松岭,回头见那队人马有几百人,也向孤松岭这边赶过来,他又跑向十三太保下面的草房中躲藏。过了半时,听得马蹄声渐渐远了,才放下心来,决定今晚就在这草房里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