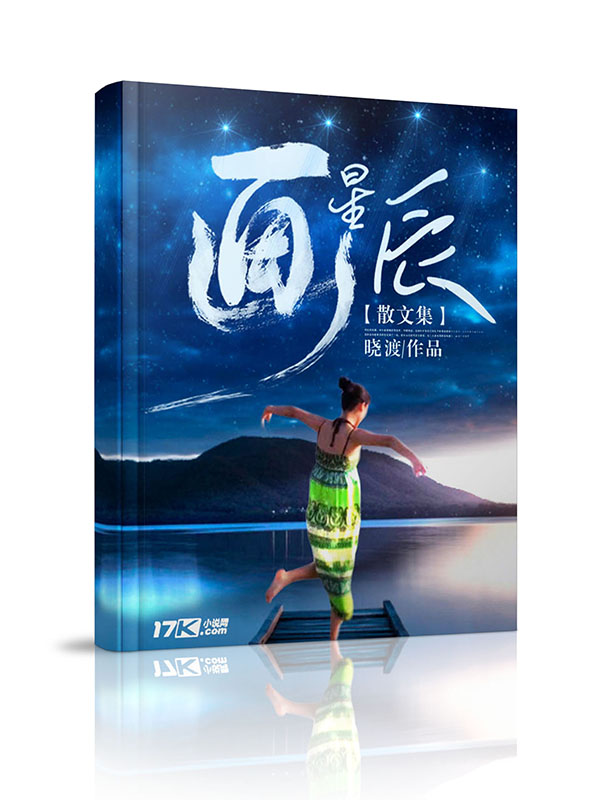那个妇女正是春花。原来她回到娘家后,依然不能为人所容,村人都把她看做是扫帚星,避之唯恐不及。在娘家勉强过了几十天,就又回到地庄来了。她心想,回到地庄后,自己只过自己的日子,再也不去理会旁人的冷眼。她回到那所荒芜已久的房子时,见院中荒草连根,殊不能入,连房顶上都生出蒿子来。不由得又自叹命苦,哭出声来。这些天来每遭他人冷眼,固是习以为常,却使得她老了许多,四十多岁的女人却头上生出了白发,脸上也出现了皱纹,身形佝偻,步履蹒跚,俨然有六十多岁的形象。她进入院中,着手收拾起来,不一会,见天色将暮,只好先腾出一间房子住宿。屋子里久不住人,扫将起来,尘土飞扬,蛛网飘飘,一股凄凉之意袭上心头,她又涕堕垂膺,不可休止。
这天晚上,久不成眠,眼前总浮现出家里原来的模样,一再想起丈夫尿壶生前的言谈身影,更加愁苦难言。俗话说人过四十天过午,春花正值盛年,狼虎之季,如何耐得过这杀人的寂寞。她思绪乱飞,心虑风起云涌。索性不再努力睡觉,起身披衣,踱步走到屋外去,坐在门口观赏风景。是夜晴空如洗,银河高耿,明月在天。她看了会星星,心里总算清凉了许多,才又回屋睡觉。然而屋中景象实在牵人忆往,枕边人语恍然如昨,以往情景历历在目,辗转反侧,又睡不着,如此烦乱焦心,实是难堪。直到东方泛白,仍未能睡上一觉。
翌日,春花将院子收拾完毕,见着几个邻居,慌张地向她们打个招呼,见她们却并不理会,只在墙外切切私语,指指划划,心里好不是滋味。将近傍晚,又害怕起来,守寡生活,每每最惧天黑,独居空房,难以入睡,委实不易,春花索性又不去睡,再把房子里外收拾了一通,出屋将院子也收拾了一遍,觉得再也无事可做了,这才回屋歇息,只是依旧不能入梦,苦思焦虑,顷刻间把自己从小到大能记起的都回想了一通,仍然毫无睡意,心中不禁恼火,想到准是家里的坟地风水不济,弄得人财两空。地庄风水最好的要属孤松岭,地庄人大部分坟地都安置在那里,所以家家人财两旺,生活美满。只怪自己家的尿壶太懦弱了,争不到孤松岭的土地,只好在草帽山上取一块地当作坟地,一定是那里风水犯冲,以至酿成大祸。春花想到这里,气愤难平,当年为了争那块孤松岭下的坟地,杨有林骂了尿壶整整三天,最后还是杨有信出面制止,他才罢休。那块坟地却谁也没能弄到手,成了公家的草场。春花恨杨有林,她恨他快恨到骨子里了,杨有林在地庄口才出众,骂起人来语落如珠,虽然不假思考,却从来不骂出两句一样的话,即使全地庄人集合在一起都未必骂得过他。杨有林不积口德,骂尿壶骂得天花乱坠,从第一辈到第一百零八辈祖宗,一一骂过来,又骂过去,词语之损,无与比肩。所以春花现在依然恨他入骨。
春花恨着恨着,竟不知不觉间睡着了。她在梦中依旧恨杨有林不止,杨有林也依旧骂着尿壶不止。奇怪的是,杨有林骂完了尿壶,却向她走过来,压在自己身上,口中不停,下面也开始动了起来。春花觉得恶心,却苦于推他不动,使尽了力气,还是只好由他抽动。
次日一早,春花醒过来,她更加恨杨有林了。她躺在被窝里,并不起床,想着自己家坟地的风水如何才能转好。起初,尿壶找人看坟地时,风水先生曾说过,如果没有孤松岭的古松,草帽山也是一块风水宝地,两边坐落土帽山和孤松岭,三山环绕,有醉翁畅怀向天之态,日夜吸收天地灵气。但是孤松岭有棵松树,俯视山下万物,意有相冲。春花突然灵机一动,如果把孤松岭那棵百年古松砍了,草帽山岂不成了地庄风水最好的地方?她于是起床穿衣,也不梳洗,拿起斧头就奔孤松岭去了。这正是发呆和王小飞看到春花的那天。她来到孤松岭的白岩之下,当年梁九刻的诗还赫然其上:
遥遥来者空竟催,
纷纷去者不可追。
安得我执随风杳,
不去釜中见米炊。
她走到白岩旁边的那棵苍松下面,抡起斧头就往树上砍去,却见斧锋过处,血痕昭然,汩汩流出鲜血。她大惊失色,以为自己眼花没有看清楚,定睛再看,那斧痕长约半尺,宽不盈寸,真有殷红色的液体流出来。春花又举起斧头,准备再砍,突然头疼欲裂,昏厥过去。等她醒来时,天色已晚,她心想,既然砍不成树,也就算了,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自己天生的贱命,怎能居于贵穴?当下用一只手捂着头,艰难地走了回去。
春花回到家里,心里反而坦然,苦也受了,也反抗过了,有没有变化再也用不着去理睬。只是头还是痛得厉害,一阵阵地像是要爆炸一样,那棵松树被自己砍得流出血来的情景时时浮现在眼前,她以为自己是被吓坏了,休息两天,不再想起这桩事也就过去了。不料过了两天,病情反而更坏,几乎堪撑不住,她心想,可能是触动了神灵,那棵古松历经百年不死,定是神物。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而百年者,实属罕见。她只好去弯子村找香头看病。春花走到弯子村李香头家,对她把事情的经过交代清楚。李香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双手合十,锁眉闭目,良久,忽然睁开眼睛,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全身发抖,又喊又叫,又良久,戛然而止,说道:“孤松岭上那棵松树的确是神物,你不慎冒犯神灵,当有此劫。”春花急忙道:“那要怎样化解?”李香头不说话,只顾大摇其头。春花大骇,焦急之中把带来的一筐鸡蛋推到她面前。李香头眯眼看了下鸡蛋,说道:“安得我执随风杳,不去釜中见米炊。”春花茫然道:“什么意思?”李香头道:“放弃你想做的事,把锅砸了,贴在松树伤痕处,从此不必在用锅做饭了。”春花问道:“那用什么做饭?”李香头哈哈一阵怪笑,说道:“锅都用来给树疗伤了,你以后再也没有用锅的命,那就别用了,当乞丐去吧。”
春花匆忙回到家里,把仅有的一口锅砸碎,拿起一些碎片,又到孤松岭那棵古松旁边,见那道伤痕犹自流血不止,便一片片贴到斧痕处,却贴不住,刚贴上去,不一会就掉下来。春花大急,只好捡起一块石头,硬将锅片砸进树皮里,这才将血止住。
春花再回到家里时,见到家里的锅没有了,一时间还很感奇怪,怎么居家过日子的,连一口锅都没保住呢?她呆呆地看着灶堂,心里说不出的凄凉,这一年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委实比前四十年的还要多,而且件件致命。春花又想起尿壶来,尿壶虽然一辈子畏缩鼠怯,丝毫没有男子汉气概,只要他人在,那毕竟是一个人,是注定要陪自己走过一生的男人,是自己唯一可以倾心信赖的人,只要他在,这家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还是个家,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现在尿壶不在了,自己还怎么过日子?不说别的,连锅都没有了,以后只好出去要饭了。春花想着想着,大哭起来,她坐在灶堂旁边,哭到抽搐。她突然很后悔,后悔尿壶在世时自己和他吵那么多架,后悔自己一定要尿壶买那匹天杀的马,然而这一切再也毫无意义。她哭着,嗓子哑得发不出声来,哭到伤心处,竟又转哭为笑,而且狂笑不已,从此以后这女人便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