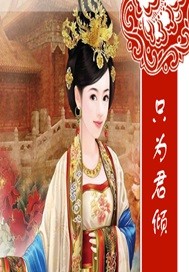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锔》
《第一章》
“锔盆子锔碗锔大缸,锔得那破碗不漏汤,……”
她支起耳朵,仔细地听,一时心跳如擂鼓。
那悠长的带着唱腔的吆喝声渐行渐近,似乎勾去了她的魂。
她慌忙抻抻衣服上的皱折,掸掸线头,对着镜子抿了一下略显凌乱的头发,打开了院门。
锔碗匠正挑了挑子,站在胡同口里拉长了唱腔吆喝着,一双微微上挑的桃花眼不住地向她的院子张望。
听到她的开门声,慌乱地移开了目光,借着擦汗掩饰着满脸的不自在。
“喂,小碗匠,”她冲着他招手,“你上次给我锔的碗咋不中了呢?”
“咋会不中?俺给你看看。”他裂开嘴笑,略有黑红的面膛映衬的一口白牙格外显眼。
她敞开两扇门,侧着身子,“院子里喝口水吧。”
锔碗匠颤悠颤悠地挑了担子,擦着她跟前,进了院子,收拾出家伙什。
她探出身子瞥了一眼斜对门的院子,又仔细侧耳听了听动静,反手将院门栓了,手心里已经沁出细密的汗来。
“大嫂,来了两趟咋滴不见大哥呢?”他低头调试着金刚钻上的弦,貌似不经意问道。
她歪着身子靠在屋门口,手里“哧拉哧拉”纳着鞋底,不时用针尖蹭蹭头皮。“俺是他家童养媳,俺家小男人没长成就没了。”
小碗匠手里一滞,抬头望了一眼她挽起的发髻,“那你……?”
她将额前松散的一绺头发挽到耳后,头也没抬,“俺家婆子怕老了没人养,让俺跟她家的公鸡拜了堂。”
他叹了口气,又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安慰,索性沉默低了头忙活手里的活计。
气氛一时尴尬起来,小碗匠把手里的弦拉的如同二胡一般如泣如诉。
她听得有些着了迷,偷偷地望一眼他,裸露在汗褂子外面的肌肉被阳光晒得黑红油亮,结实健壮,挂了汗珠子,充满了陌生的令她眩晕的味道。
“喂!”她轻声唤道,“你的褂子肩头都磨破了,脱下来俺给你撩两针。”
“要不得,要不得!大嫂,”小碗匠擦了一把脸上的汗,“俺一身的汗臭味。”
她利落地将麻绳换下来,重新认了针,“穿着缝,万年穷,还是要讲究的,快点扔过来。”
小碗匠不好意思地将衣服脱下来,团成一团,扔给她。一股浓郁地令人窒息的男性气息迎面扑过来,她慌乱地接了,使劲咽了口唾沫,压下扑通扑通直跳的心。
“大嫂,碗补好了,绝对滴水不漏,你看看。”
她慌忙放下手里的针线去接,正碰上小碗匠的指尖,心里一抖,手便滑了。小碗匠疾忙接了,厚实带茧的手掌包裹了她细腻的指尖,然后顺着指尖紧紧地攥住了她的手。
她的心便跃到了嗓子眼。
小碗匠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凸起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然后呼吸便粗重起来。
她在他温热的气息间,融化成了一摊泥,被打横抱起。
锔好的碗孤零零地丢在了院子里。
《第二章》
她坐在炕上飞针走线,就着昏暗的煤油灯。
那小碗匠的褂子委实破旧得太厉害了,她从箱底翻出一块婆子生前织染的土布,给他裁剪了一件对襟褂子。
听他讲,他也是被弃的孤儿,他的师傅,一位朴实的老补锅匠收养了他,将这走街串巷的糊口手艺传给了他。
他第一次跟着师傅来这个屯子补碗时,因为生的秀气,又羞涩腼腆,被一群大胆泼辣的小媳妇围了打趣。
她捧着家里裂成两半的面盆,站在人群后面,看他面红耳赤支支吾吾的样子觉得甚是有趣,抿了嘴笑。
李婶抬手唤她,指着她对小碗匠说,“这是我们屯子里最水灵的丫头,你若是不收我的补锅钱,我就给你说媒,中不?”
她羞嗔地瞪一眼李婶,扭身就跑,被李婶眼疾手快一把抻了袖子,在她耳边悄声道,“傻妮子,那老婆子能让你伺候一辈子?你就不为自己以后的日子想想?”
她的脸“腾”的一下如同火烧灼了一般,恨不能把头埋进胸膛里,她感觉到,那小碗匠一双好看的桃花眼,正偷偷地在她身上溜来溜去。
她慌里慌张地逃回了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婆婆狠厉地训斥她,她嗑嗑巴巴地说,“锔锅的人太多了,要排队,我怕耽误家里活计。”
后来,小碗匠接过了师傅的担子,亮着嗓门在各个胡同口带着唱腔吆喝,“琅哩个琅哩个琅哩个珰,锔盆子锔碗锔大缸……”。他的手艺不如师傅熟练,但是眼神好,活精细,碎成几瓣的茶壶或者花瓶,经过他的仔细雕琢,能打磨出一枝好看的梅花样来。听说有大户人家故意将黄豆浸泡在新买的紫砂壶里,将茶壶撑裂了细纹,请他去做手艺,锔些好看的花样。
不知是不是他当初上了心,他经常来屯子里转悠,给李婶做活时,格外殷勤,会少收或不收李婶的钱,有两次大雨,他还留宿在了李婶家。她借口去借绣样,李婶冲她咬耳朵,“那小碗匠心里头惦记上你呢。”
她再听到小碗匠的吆喝声时,便故意摔裂了盛粥的碗。
小碗匠用带了钩子的眼神打量她,“大嫂,你这碗碴口不好对,恐怕要费些功夫呢。要不,我做好了给你送家里去,行不?”
她指了自己的家门。
近天黑时,小碗匠才把碗送过来,并且锔了好看的花型,令她赞叹不已。
最后,他却只收了她一文钱,她给他包了几块刚烙好的饼。
她和小碗匠商量过了,两人都没有什么亲人,成亲的时候就由他师傅主婚,李婶做媒,吃顿饭就成了。
以后,她守着家里几亩田土,小碗匠农闲时走街串巷挣个积蓄,日子绝对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