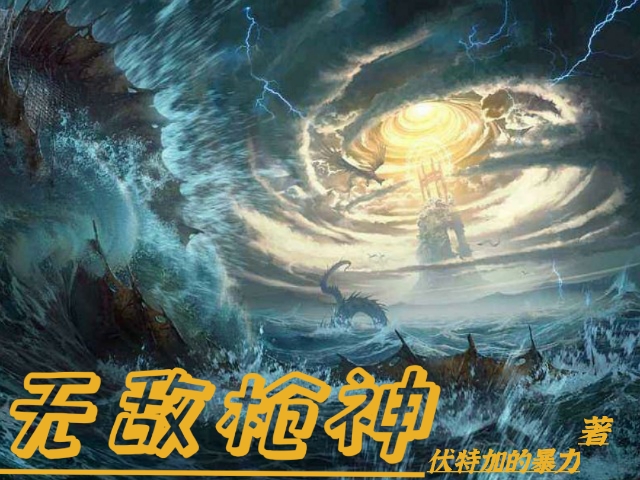——一场江南烟雨,谢了繁华永世
生在水乡江南,原本,最爱江南的朦胧烟雨。
最是痴迷那缠绵绯恻的烟青色调,氤氲着轻柔的凉意,把江南细笔勾勒的青石小巷,乌篷水岸,渲染成一副泼墨丹青。
我生于阴凉的二月末,出生那日,一夜春风细雨,催开了院里的一树杏花,春意繁茏,风姿娇艳。
我的乳名就唤作杏儿,只是如今这名字弃了,无人再提,我叫顾安生,取“安然一生”之意。
今日清明,这片园子里的杏花开的正好。轻柔淅沥的烟雨晕染了成树的胭脂,粉白娇嫩。
我的鞋子和曳地的裙摆一路走来,早已经被草地上的雨水濡湿了,麻凉直透心尖。
我把手里装着纸箔贡品的篮子放在地上,将纸伞撑起盖在上面,便有被雨水打落的花瓣纷纷扬扬掉在我的头发上和脖颈里,沁骨的凉意令我不由自主瑟缩了一下双肩。
以前,同样的凉寒天气,同样飘摇的杏花雨,却是我最大的期盼与乐趣。我会淘气地故意摇动花枝,任凭浸润了清雅花香的雨滴和轻盈的花瓣掉落一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如今睹物思人,同样的光景却只觉凄清冷寂。
眼底不觉氤氲起朦胧的水汽,逐渐凝结成泪混合了冰冷的雨水。
闭上眼睛,听簌簌落雨声,心底一阵揪痛。
“姑娘莫动!”伴着一声低沉焦灼的声音,一道月牙白的身形疾闪而过。一条翠绿黄睛的青蛇被甩到旁边的草丛里,疾速游走了。
我身后半尺处的树枝仍在颤悠悠地晃动。
一位修眉朗目的俊雅公子侧身而立,紧捂了手腕处,微蹙着眉峰。
“还好只是一条竹青蛇,不过也有毒。”我走近他跟前,一股好闻的龙涎香味混合了雨水的潮气充斥了我的鼻端。我拉过他的手,将织锦团绣的衣袖绾起,露出如玉润泽的手腕来,上面两个清晰的毒蛇牙印。
“有匕首么,拿出来。”我淡淡地说道,接过他递过来的匕首。转身从篮子里拿出火折子,晃燃了,将刀尖处仔细炙烤,熟练地在他的伤口处划开一个十字口,把黑色的毒血尽量挤干净。
他静静地看着我的动作,问我,“你是大夫?”出口温润,却不是绵软的江南口音。
我取出手绢,将伤口处的污血擦拭干净,“此地多蛇,即便七八岁的稚童都懂得应对方法。想来公子不是江南人了?”
他点头“嗯”了一声,“在下长安人氏,我叫景辞。”
温热的气息就呼吸在我的脸上,令我双颊如被烧灼一般。
“景公子,你的伤口虽然处理干净了,但恐怕体内还留有毒素,回去后用蒲公英白芷等熬一点凉血解毒的药来喝。”
他笑着望我,“听姑娘的就是,劳烦姑娘了。”
他的谦恭有礼顿时令我心如鹿撞,“是我应该多谢公子援手之恩。”
他看了一眼我身后的篮子,温和地说,“春雨寒凉,在下的马车就在园子外面,姑娘想要去哪,让在下送上一程可好?”
我低身道了个万福,捡起地上的油纸伞,柔声道,“我是路过被这一片杏花林迷了眼,还要去祭奠一位故人,就不劳烦公子了,风凉雨急,您多保重。”
我拎起地上的篮子,复又欠身道,“就此别过。公子相救之恩,改日必当相报。”
他颔首算作应答,站在原地,似是望着我出了杏花林,又急忙开口道,“姑娘,我们还可以相见吗?”
我停下脚步,回头向他轻浅一笑,“我叫安生,顾安生。”
(二)
今天难得是个晴好的日子,春日里的暖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我躺在杏树下的藤椅上,索性用书遮了脸小寐。心里只可惜那杏树枝干单薄,否则栓一架秋千在上面,也不会这般沉闷无聊。
府里的日子本就无趣,今日里父亲说要有贵宾来访,叮嘱我们安分守己,不要在府里四处走动,以免冲撞了贵客。
连日里的缠绵阴雨天气,我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能滴出水来,闷生了霉味儿。时日再久,恐怕头发里要长出鲜嫩的蘑菇来。便命下人在园子里支了藤椅,晒着暖阳看书打发时光。
看日头,早已过了午时,丫头小悠去厨房里端饭还没有回来。听说今日那客人身份尊贵非常,屈尊留在府里与父亲饮酒,厨房里忙得人仰马翻,哪里顾得上府里诸人的饭食。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两声,索性丢了书,揽过旁边绣墩上的酸梅罐子,丢了两颗在嘴里,酸得我眯了眼睛。
肚子却叫唤得更加厉害。
身后有轻稳的脚步声。我把罐子重重地丢到绣墩上,“悠悠,你总算回来了,小姐我都快饿瘪了。那讨厌的客人还没走么?一个人就能折腾得府里鸡飞狗跳的。”
脚步声一顿,似是愣在了原地,有清润的打趣声,“那讨厌的客人原本想走的,可是如今见到小姐改变了主意。”
我惊坐而起,来不及吐出的酸梅核卡在了嗓子眼里,咳呛出了眼泪,说不出的狼狈。
“我比那毒蛇还可怕吗?竟然能吓得小姐花容失色。”
我终于咳出了酸梅核,用手绢掩着嘴吐了,顺了口气方才察觉自己失态,急忙从藤椅上站起来,敛了衣襟,道个万福。
“一时失态,让景公子笑话了。”
他爽朗一笑,幽暗深邃的眼睛变得明澈了几分。“姑娘姓顾,想来就是顾大人的千金了?人生何处不相逢,你我也是有缘了。”
我羞赧地点头,“刚才的无心之言还请公子莫要见怪。”
“哪里哪里,小姐直言快语,而且事实也确是如此。顾大人兴师动众,盛情相待,景辞不胜惶恐。”
他双颊微红,应是带了几分酒意,言谈间依旧进退相宜,温和守礼。
他环顾四周的杏林竹屋,“这是小姐的院子么?如此清净雅致,莫非景辞唐突了?”
“喔,不是的,只是我喜爱吃酸杏,所以央求父亲种了这片园子。”
他的鼻翼噏动,眸光微闪,“满园芳菲竟然也遮不住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儿,哪里来的?”
我恨不能将脸埋进胸前,烧灼得厉害,说出口也是桩羞人的事情,难为情的很。“是我自幼身体不好,大夫给开了方子,每日里泡半个时辰药浴,身上总是有难闻的苦味。”
他也不好意思地轻咳两声,如今虽然世风开放,但沐浴这词总是有点旖旎,会令人遐想,多少带了点暧昧。
正两厢尴尬时,父亲慌张地自园外小跑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小女粗陋,不懂规矩,多有冲撞,还望景王恕罪!”
我的心底不禁一惊,父亲身为此地的父母大人,我自然知道景王爷乃是当今皇上现在唯一的胞弟,传言中文韬武略,云端高阳,却是无心朝堂,只寄情山水,随性潇洒,做了个闲散王爷。
怪不得,那日里感觉景辞这名字莫名的熟悉,他隐去了国姓,景辞是他的名讳。
父亲向我挥了挥衣袖,怒声冷斥道,“抛头露面,成何体统,还不赶紧退下!”
父亲对我一向娇宠,今日却平白这般疾言厉色,我感到一阵委屈,红着眼圈退下了。
景王大概也没有想到父亲竟然对我这般严厉,急切劝道,“是本王醉酒鲁莽,打扰了小姐清净,况且小姐知书达理,惠质兰心,顾大人莫要责怪。”
他竟是这般善解人意,一句话如三春暖阳,十里春风,和煦了我的感伤。
(三)
夜里时,月色清幽,我正与院里丫头们围坐在泥炉边煮竹沥茶,一阵悠扬婉转的笛声穿透夜色,如泣如诉地盘绕在耳根。
“府里竟然还有下人这么会吹笛子,叫过来解解闷吧。”
小悠掩嘴一笑,“小姐恐怕请不动呢。”
我抬了抬眉,“谁有这么大的谱?”
小悠还未回答,旁边便有丫头抢先道,“听方向,应该是杏林院子传过来的,难不成是景王爷?”
我的心里一颤,手里的茶差点泼出来,“他竟然没有走吗?”
“听说他原本宿在驿馆的,后来说是醉酒,留在了府里,就住在小姐的杏林竹屋。”
小悠也插嘴道,“我今天从远处偷偷看了那景王一眼,竟然难得的俊朗,气宇不凡。听说当今皇上曾为他指过好几位朝中重臣的女儿,都被他婉拒了。他说自己并不在乎门第之见,只想找一位兴趣相投的姑娘白首。如此这般深情专一的男人委实稀罕。”
我的脸竟然莫名地红了起来,唯恐被人察觉,慌忙低垂了头,用眼角偷看几个小丫头,脸蛋竟也都是白里透红,双眸晶亮,应该是炉火太旺了。
我啐了一口道,“怪不得让你去厨房端个饭菜,半晌不见人影,原来是去偷看景王去了。”
众丫头一阵调侃,将小悠羞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
笛声一直响到夜半,景王好大的雅兴,将《梅花引》,《凤求凰》,等几首小调翻来覆去地吹,令我夜里辗转反侧,竟然好久不能安睡。
第二日清早,还未洗漱,父亲便亲自来我的院子,说是昨日里扬州城的姑妈来信,几年都未见我,想念的紧,要我去她那里小住一段时日。母亲早起就去置办乡土礼品去了,一个时辰后便启程。
我夜里没睡好,有些困倦,借口身子不舒坦,改日再走。
父亲态度很坚决,不容我拖延片刻,转身吩咐丫头们打点行李,让小悠去厨房里装些茶点路上食用。
马车即将出发的时候,景王一袭月牙白紧袖长衫,淡紫团绣披风,自大门内信步而出。见到门口的马车明显怔了一下。
父亲赶紧上前恭敬地行礼问安。
景王伸出双手扶了,淡然道,“顾大人客气,本王昨日多有打扰,醉酒失态,还请包涵。”
父亲忙惶恐地谦让了。
景王抬眉望了我一眼,疑惑地道,“顾小姐这是要行远路么?”
父亲垂首答道,“小女想去扬州城舍妹府上小住几日。”
景王欣喜道,“竟然这般赶巧,本王也正要与大人告辞,去那扬州城,正好顺路。”
我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确实够巧的。
父亲慌忙拒绝道,“女孩子家身子娇气,不堪劳顿,一路上走走停停,可不要误了王爷行程,微臣吃罪不起。”
景王爷朗声笑道,“我一个闲散王爷,本就是游山玩水,顾大人可是信不过在下?”
“哪里哪里,”父亲赶紧摆手,一脸惶恐,“小女顽劣,一路若能得王爷费心,老臣求之不得。她若有何失礼之处,还请王爷不要怪罪。”然后吩咐母亲道,“安生粗野惯了,你要好生叮嘱几句。”
母亲唯唯诺诺应了,转身对我殷切叮咛,无非是些循规守矩,谨小慎微一类的话,我温顺乖巧地一一应下。
临行时,母亲为我细心地整理了衣领和发髻,凑近我的耳边低声道,“景王危险,切莫显露你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