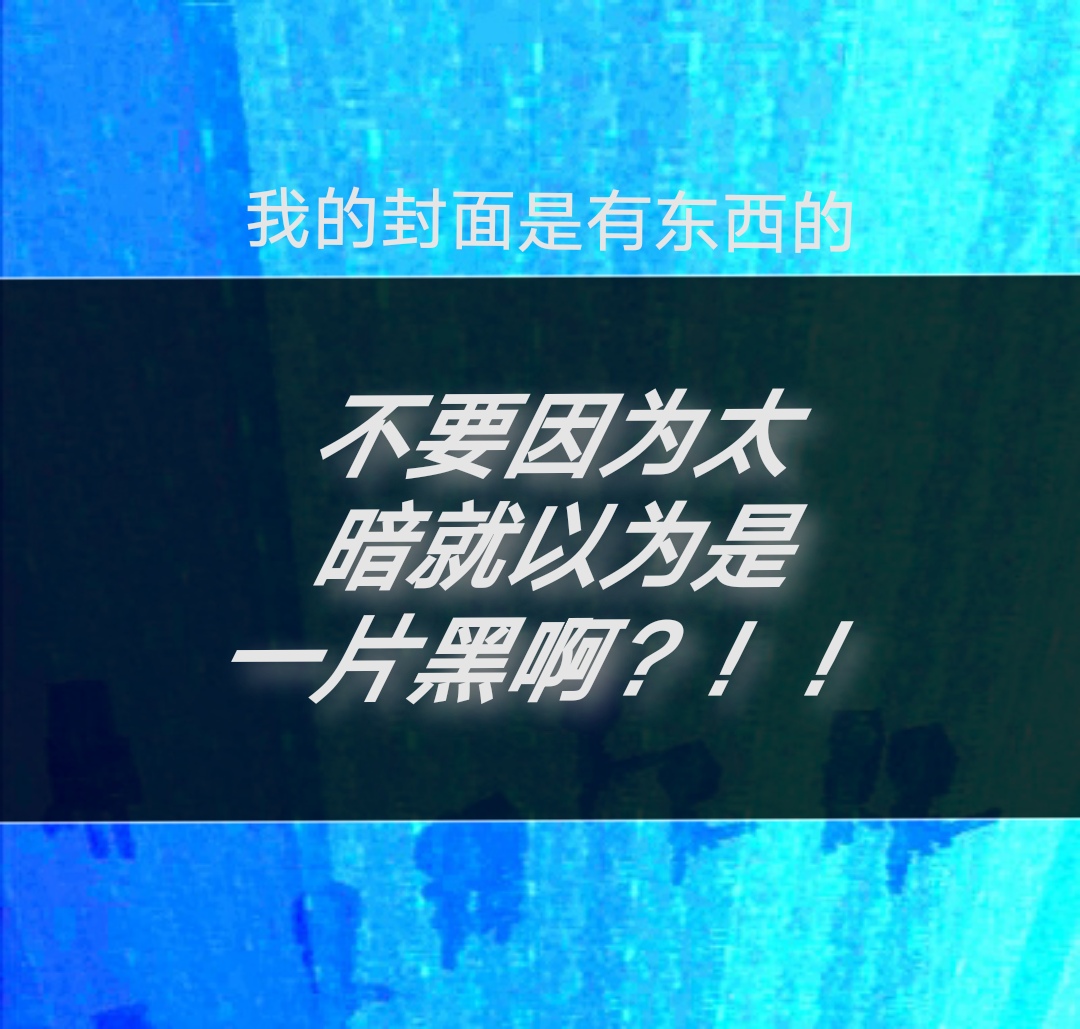次日清晨,陈剑第一个起身,挨个去叫熟睡中的其他五人。
“我们去跑步如何?”陈剑看着五人揉着惺忪的睡眼被自己叫醒,笑道。
“大清早的,跑什么步?”郑志雄嘟囔着。
陈忠良醒了醒神,“为何要去跑步?”
“唐凌每次都不给我们时间操练,我们就必须自己找时间。按你们所说,我们先锋伍的人作战的时候都是做先遣部队打探消息,所以,奔跑对于我们完成任务尤为重要。只要跑得比别人快,就算任务失败,逃命也可以快点不是?”陈剑一直保持着一种很和善的微笑看着还微闭着双眼的五人。
五个人慢腾腾坐起身,看到面前的陈剑,有了一小段的沉默。
他们五人被发配到死囚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刚来这里每个人都想着上阵杀敌哪天保不好立了战功便可以免了这死罪侥幸留命回家,谁曾想没几天这些念头便被生生折断。
在死囚营,他们完全没有体会到作为一个兵士的神圣,这里只有涣散的军纪和一群蝇营狗苟的死囚,这里的人生死无人问津,只有在大战之前才会有人想起到这里找几个人做先锋,说的好听是去探敌,其实就是被人当做敝履,运气好的活命回来汇报些军情,运气不好的死在敌营也没有人过问。
面对着如此场景,众人那本有的一腔抱负便转瞬被摧残殆尽,每个人都是按部就班,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只是他们的头上,一直悬着一把刀,什么时候被派出去打探敌情了,也许就是这种无尽难熬之日的终结之期。
既然改变不了现实,人就会想着改变自己,每个人到了这里不久,就忘却了自己曾经的抱负,融入这一汪死水,再也没有了丝毫的波澜。
然而,虽然屈从于现状,但是每个人的心中,却还是暗暗隐藏着原本的初念。
如今,陈剑用最简单的求生渴望小小的挑拨了他们一下,马上如小石落入河中,激起了小小的波澜。
只是,对于陈剑,他们的心中总有着一丝隔膜。
这个人,本不应该在死囚营,却甘心呆在这里等死,这让他们想不通。
见大家犹疑的神色,陈剑知道五人对他还有芥蒂。
既然已经被怀疑了,再解释也是徒然,陈剑笑了笑,“如果哥哥们觉得我说的在理,就跟着我一起,如果哥哥们还信不过我,我也不强求。”甩甩胳膊,陈剑也不再劝说,自顾自跑出了居所。
五人看着陈剑离去,谁都没有动,只是少顷之后,蒋兴宗便穿戴好衣物,一个人默默地跟了出去。
很快,便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房中只剩下陈忠良一人。
沉默片刻之后,陈忠良站起身,走出房间。
山脚下,飞起一只鸽子,扑腾着翅膀往山那头飞去。
接下来的几日,营地的值守士兵,每日清晨都能看到有六个人绕着营地在一圈又一圈地奔跑,士兵们对先锋伍的人的这种行为均不以为然。
反正早晚都是一死,何必浪费精力在这种无用功上,还不如享受现在活着的日子。
而身为营长的唐凌,每日都姗姗来迟,他眼里所见到的只是先锋伍的六个人规规矩矩进兵器房擦拭兵器,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陈剑。
看到陈剑每次点卯之后都跟随六人而去,对自己也谨守着基本礼仪,唐凌很纳闷。
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子怎么突然这么守规矩了?
看来是上次自己对陈剑用的军法起了威慑作用,再犟的小犊子在严刑之下也只能低头。
想到此,他不禁暗暗得意。
几日之后,先锋伍的人在晨跑的时候腿上又多了几块石头,依陈剑的说法,此举是为了增加大家的腿力,虽然五人对陈剑还存有疑虑,但是对于陈剑的建议,他们并没有拒绝,毕竟勤于操练对自己也有好处。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习惯这种操练的方式,郑志雄和陆浩杰没过几天便因为在晨练之时没有调整好气息,小小地崴了一下脚。
来军营已经差不多半月了,陈剑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为了不引起他人怀疑,他白日里尽量隐藏自己的内力,只在夜半时分,自己偷偷起床,运息调理。
只是久而久之,唐凌也知道了六人每日清晨的锻炼,他看着六人的神色似乎有了些变化。
就在陈剑带领大家每日勤练的时候,这边厢,上官云瑞却坐在一个深谷中稳如磐石。
当初他与风雪月双双坠崖之时,万幸地掉落到崖边一处凸出的泥石处,泥石松散,并不牢靠,但是所幸可以有个借力点。上官云瑞就凭着这个借力之处运足内力将风雪月推上了崖边,自己则随着碎裂的泥石一起坠落。
不过,他的命不是那么容易丢的,崖下并没有尖石林立,而是一汪碧水。上官云瑞在掉落之时也没有闲着,抓住任何自己可以抓住的东西,东一扯西一拉,极大地减小了自己的坠落之力。所以,他掉进水中时,并没有伤及经脉,只是被强大的压力弄折了一条腿。
从水中游到岸边之时,上官云瑞抬头望了望高耸的崖壁,知道自己暂时上不去,便也安了心,坐到地上运息调理。
气息稍微顺畅一些,上官云瑞便拖着一条腿,开始四处打探出去的路。然而,结果很让他失望,自己所在的地方四处悬崖峭壁,根本没有通向外界的道路。
一番转悠下来,伤到的腿又开始隐隐作痛。上官云瑞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不再胡乱走动,保存着自己的体力。
天很快黑了,上官云瑞肚中饥饿,苦寻一番却没有找到任何裹腹之物,无奈,他用双手舀了些潭中之水充饥。
在找到出路之前,自己必须减少任何消耗体能的事情,所以,他不再走动,而是直接在水潭边躺了下来。
枕着冰冷的寒石,看着头顶上方那高不可见的崖顶,上官云瑞深深吸了口气。
他想到了风雪月,不知她是否已经得救,自己与她,终归是有缘无份。
他又想到了陈剑,这小子回平阳府之后过得是否还安好,经过上次那番风波,估计他的日子又难过了。
他突然又想到了玄凌,在冰谷中的那几年,虽然寂寞,过得却是这一生最安心的。
想着想着,他便沉沉地睡去。
接下来的几天,上官云瑞都是每日在谷中寻找出路,然而,一次次地失望让他的动力有了些许动摇,精神也开始萎靡。
光靠水已经完全不能抵挡饥饿之感,虽然他用内力支撑着身体的行动,但也是一日不如一日,饿的急了,上官云瑞见东西就往嘴里塞,树皮、鲜花,能咽下去的他都死命往肚子里吞。
不过就算如此,却也不是长久之计,没出几天,上官云瑞就撑不住了。
自己一世英名,难道真的要饿死在这连鬼影都没有的地方?
又到了深夜,这一夜,上官云瑞没有睡,而是坐在水潭边发呆,虽然身体一直在强烈要求他休息,但是他的意识在一直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千万不能睡,不能睡,睡了也许就醒不来了。
天上的明月亮晃晃地在头上散发莹莹冷光,照得谷中的事物都披上了一层银色白纱。
夜凉如水,上官云瑞感到身体一阵发冷,他回过神,却突然发现水潭上方的崖壁上,在隐隐发亮。
回转身,上官云瑞惊讶地看到,崖壁上显现了几行字。
恶行昭昭,天理不容,杀妻灭子,人神共愤,立此为证、誓报大仇!
字里行间的意思很明白,是一个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在这里刻字自激,只是,这些字是从何而来?
沿着光线的方向,上官云瑞很快发现了这些字的源头。
这些字,被刻在水潭边一块髙起的岩石上,只是,这刻字的方法很不同。
这些字是有人用极强的内力将寒气汇聚成冰贴附在岩石上,寒冰反射着月光,投向对面的崖壁。
寒气凝结成冰,遇热不化,这种手法?怎么会这么像师门的武功?
难道?
还没有想明白,上官云瑞便突觉脑中一片空白,身体内仅存的一丝精力耗尽,他头一歪,便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上官云瑞感觉到耳边有人在呼唤。
睁眼一看,他看到了一张自己熟悉的脸。
“上官哥哥,上官哥哥,你醒醒,你醒醒!”风雪月在使劲摇晃着自己。
一阵眩晕,上官云瑞便重又昏迷过去。
再次醒来,上官云瑞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武林苑的居所,他的身边,风雪月眨巴着一双大眼焦急地看着他。
“上官哥哥,你终于醒了,终于醒了,太好了,太好了。”风雪月见上官云瑞醒转,眼一红,豆大的泪珠便不可抑制地滴落下来。
上官云瑞没想到风雪月看到自己醒转会激动如此,心头一热,“我没事了,你莫伤心。”
“你没事才怪,一个人在深谷里没吃没喝的那么久,要不是我找到你,你就死在那里了。如果你死了,你叫我以后一个人怎么办?”狠命抹了一把眼泪,风雪月嘟起了嘴。
“是---你救了我?你怎么找到我的?”上官云瑞发现自己身体有了些许力气,便托住床沿缓缓坐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