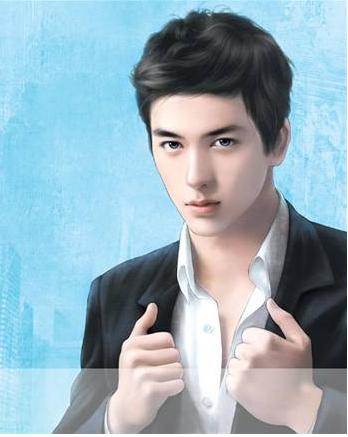房间里还打着空调,凉水顺着我的头发流进了嘴里,脖子里,衣服里,就连胸口都传来冰冷的寒意。我不禁打了个冷颤,额前的伤口也开始疼。此刻应该说我浑身都是疼的:手脖子疼,弯着的腰疼,摔伤的屁股疼,腿疼,没有哪里是不疼。这些身体上的疼,都抵不过心里死寂般的绝望。
我用尽全力,挣脱开来,头发上的水也甩在了他的脸上。
夏景轩眼眸变的幽暗,深邃的让我猜不出深意。我伸手扯了个毛巾,将脸上的水擦干,狠狠的扔在他的脸上,我想报复他,从这一刻开始。
他不是说他最在乎的是我吗?那我就让最在乎的东西烟消云散…也让他尝尝心底绝望的那种痛彻心扉有多折磨人…
“景轩。”我声音轻不可闻。
冷静的气氛凝固了身边的一切,包括仍在发怒中的夏景轩。我觉得耳朵里依然传来哗啦啦的自来水的水流声,包括来自胸膛间扑通扑通的心跳声。空气中有细微飘荡的粉尘,在我们之间来回晃动。我很少这么只唤他的名字不带姓,我们之间不到半米的距离,我清晰的看见他眼底明明亮亮的晶莹和厚重的呼吸声。
“我想洗澡。”我打破安静宁谧的气氛。
“好,我去放水。”他喉结动了动,转身便走进了卫浴。
此刻我们都分外的冷静,冷静的连空调制冷的风速都听的清晰。我转身埋进不大的衣柜里,企图找到合身的衣物,左顾右盼之间,黯然叹气,除了夏景轩几件换洗的衣物,并没有合身的。只好挑了一件男人平日穿的白衬衫。
走进浴室,热水已经放好,夏景轩目光越过我手上的衬衫,停留在我的脸上:“没来得及准备你的衣物,你先去洗。我去附近商场看看,随意挑几件,很快就回。”
“嗯。”我轻哼了一声,表示同意。
很快男人好像终于找到了人生方向似的,飞奔出去。
待他出门,我将浴室的门锁上,狭小的浴室刚好够放一个抽水马桶加一个长长的浴缸,只是二者之间被一块透明的玻璃隔了开来。
我将目光停留在洗漱架上的剃须刀,薄薄的刀片闪烁着锋芒,可见刀片是新换上的,刀刃锋利无比。夏景轩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喜欢手动的刮胡刀,至少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从未见他用过任何电子设备的剃须刀。
我将自己清洗干净,换上了那件白净的衬衫,刚好盖住我的臀部。这让我想起了很多电视情节上让人意淫的片段,大多一夜情的女主次日醒来都会穿着男人宽松的长衬,性感撩人的长度恰到好处的将该遮住的地方遮的严严实实,但是又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的把她与AV女主联系到一起…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若是让夏景轩见识到,我保证我会晚节不保。我这样想着,冷清的眼眸撇了一眼刀片,那种夺目炫耀的光亮像是把吸铁石一样将我吸引中
…
我从新换了一遍水,光着脚丫子,躺进了浴缸。
水的温度刚刚好,像初为人母的怀抱,安心的让人陶醉。
我曾特意百度自杀的方法,各种千奇百怪的死法多的让我咂舌,可唯独只记住了这种躺在浴室里的死亡方法。
这种躺在浴缸里割脉自杀的方法有多种益处,对于想死而又畏惧疼痛的人来说。
第一:是死的不痛苦,大量血液流失人会感到冷,而在浴缸里面的热水会保持你的温度从而减少对死亡的恐惧。
第二:由于有水温,所以血小板不凝固自杀容易成功 。
第三:一般的浴缸设计形状是呈U型,人的血液容易集中出来,这样死的快。
第四:浴缸是人类最放松的地方之一 自杀时情绪也能稳定和缓。
我不知道前三者是不是真的,至少现在躺在浴缸里的我,享受着温水给予的亲和,情绪真的前所未有的缓和。所谓黎明前的寂静形容的就是此刻的我。
我合上眼睛,睫毛轻颤,水蒸气将我的脸蒸的通红,我想此刻我的脸色应该是白里通红分外好看的。我笑了起来,带着一种解脱将攥在手心里的刀片对准静脉的位置,准确无误的一刀下去,就一刀,很快,鲜血顺着手臂的走势汩汩而出。
原来死比活着容易。不需要费多大的事,只需轻轻的一用力,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可以就地解决。
该何如形容自己如此短暂的一生:
活着的时候也曾如红花一般绚丽夺目,死的却如浮萍一般沧桑飘零。想到我就要死了,竟然连个给我收尸的亲人也没有,心底的悲怆比起眼前血红的液体更让我觉得凄惶。
我该如何形容自己的爱情,开始的刹那芳华,转眼沉睡在青春里,而后消失在时间里,最后埋葬在自己的心田里。
越走越远的世界,漂泊的春夏秋冬的轮回,让俗世沧桑停留在心,然后再随风飘散而去吧…
爱与恨,终究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太苍白无力……
我的自杀并未如愿以偿,夏景轩肯定是打着飞碟去的商场然后再开着火箭回来的。他的速度之快,让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死。
男人在浴室门外毫无察觉的轻唤我:“都买好了,我给你递进去?”
我虚弱的连眼皮都动不了,只是听他继续在外面唠叨:“你放心,我不看。你只要把门拧开一个小缝就好…”
“苏苏…苏苏?女人,怎么水还在流?说话…shit…”
门外一阵暴躁的叫唤,而后一声巨响,浴室门被踹开,而我也昏死了过去。
我没有死成,可是心情却大好,我躺在病床上有一种自虐报复的快感。
林安看见我醒了,强撑着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苏苏…”她哽噎,小声抽泣,“吓死我了,你怎么那么傻,呜呜…”
输液有些凉,水流慢慢的随着压力进入我的静脉里。
我恢复了些体力,努力将头向林安这边靠了靠:“林安,你怎么在这?”
“呜呜,侯子旭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只说你出事了,叫我赶快过来,然后我就来了…”林安摸摸眼泪,眼睫毛也花了,黑黑的挂在眼皮底下,可爱又滑稽,“侯子旭还在手术台上,我这边待了老半天了,现在都是半夜了。”
“还有谁?”我小心的试探。
“啊?”林安疑惑的顿了顿,“就我跟侯子旭。噢,对了,娘娘腔李主任晚上来看过,然后医生说你没事,就回公司加班了。临走的时候说咱们广告部门再不拿点看家的本领,都得喝西北风。”
我虚弱的笑了笑,娘娘腔李猛也确实不容易,顶着5000万微电影广告拍摄的压力,还能抽空出来看我,也算师徒一场真的有心了。
“苏苏,你饿吗?我去外面打包一份小混沌。”林安说着,就起身拿着包包出去。
我眼底感觉温暖,害怕自己煽情的哭出声,只哼了一声:“恩。”
林安走了没多久,手机铃声响的此起彼伏,我看了下十几条未读短信提醒。
打开文件夹,死死的凝视着那个号码,凝视的那样用力,似乎这样就能把号码的主人千刀万剐了似的。
最后还是如梦初醒,嘲笑自己的天真。我按下全选打钩,然后一键删除。
我捂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眼前幽暗,似乎一闭上眼睛,世界就此清静了。
林安出去的空隙,单人病房门把手拧动了一下。因为躺着视线受阻,只看到一双黑色软胶皮鞋膝盖往上是白大褂
。儿时熟悉的气息,闻着味就知道是侯子旭来了。我们都太熟悉彼此,熟悉的有些疏离!
我一直忘了交代侯子旭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我的发小。这种从小光着屁股一起玩泥巴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逃课的情谊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的清。就像是一锅已经炖烂的山药排骨汤,喝的人只觉得香,却不知过程曲折。
那些被自己轻易忽视掉的儿时记忆,其实随着年华老去而会变的日渐清晰。我们都不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懵懂无知的少女,我们都不再年轻。如果非要跟青春搭上点关系,那就是我们还在这辆叫做青春的末班车里庸人自扰般的活着。看年华老去似水流长,时光里留下的剪影分外清晰透亮。
我觉得自己的心真的是苍老了好多,所以愿望也变的更加简单而又不真实。我想让时光倒退,停留在池塘边,榕树下,草丛里或者是卖冰棍的老爷爷面前。那时候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抓知了抓蛐蛐,一起吃一根冰棍喝一瓶汽水,吃一根香蕉……却美好的全世界都黯然失色…
我抢在侯子旭的前面,虚弱的说:“手术结束了。”
侯子旭走近,就势拉了一把椅子,靠这床沿坐了过来。黑框眼镜下面是一双憔悴的眼睛,明亮的灯光从他幽深的眼眸里反射出来,说不出来的静谧。这该是我第一次见过这样严肃的侯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