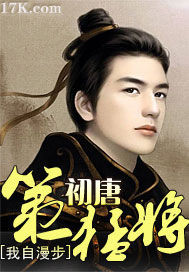漫漫长夜,促膝长谈。
原来慕容冲虽是这平阳一郡太守,日子过得可并不是随心所欲;先前韩延曾说到郡内情势复杂云云,亦不是空穴来风。
平阳郡属并州治下,而北边晋阳城里的并州刺史,正是邓羌本尊。这位性格顽固的老军头素来对鲜卑人好感欠奉,自然对平阳郡守慕容冲不甚“放心”。于是平阳郡中多有安插邓羌亲信,借以掣肘慕容冲。比如最要紧的兵事——自燕国灭亡,平阳已算不得边郡,郡中不设都尉,兵事本该由太守自理,如今却是由邓羌的族侄、平阳郡丞邓同主理。这安排名不正言不顺,只因邓羌强势,一郡之内竟无人敢于指摘。那邓同也是个能干的,长袖善舞之下,在郡中处处与慕容冲分庭抗礼,弄得慕容冲极是难堪。
双方不说势如水火,总也少不得明争暗斗,在城中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正因如此,城中市井萧条,兵丁却多。恰好段随这时跑了来,一开口就说到了慕容冲,更要命的是,还提了“燕国中山王”几个字样,可不就让人起了疑心?于是身为慕容冲心腹的韩延急急赶来探查,这才有了先前那一幕。
其后慕容冲见到段随,表现的冷冷淡淡,却是他担心府中有邓同安插的奸细。须知邓羌恨死段随,这事儿在秦国人尽皆知,这平阳郡也算是他邓羌的地盘,若是让邓羌晓得段随在此,还不知要惹出什么祸事来!
“石头,你乖乖在晋国当你的大将军不好么?何苦跑去长安做什么使者?你说说你,运气好没在长安叫苻坚砍了脑袋,偏生又跑来并州这龙潭虎穴。。。”慕容冲话中似有抱怨之意。
段随眉毛一扬:“凤皇你晓得我在长安的遭遇?我。。。”话说到一半生生咽了下去,寻思:对啊!凤皇连我生了娃儿都知晓,怎会不晓得我大闹长安的事儿?心中陡的一暖:原来凤皇从来不曾轻忽了我,我的情形,他可是了如指掌呢!
果然慕容冲语气悠悠,轻喟道:“我晓得。。。都晓得。我晓得你在晋国过得风生水起,在外位高权重,家有娇妻贵子。。。”突然间声音变得阴沉:“所以你已然把姊姊忘得一干二净了么?”听起来,慕容冲应当知晓段随与乃姊慕容燕的关系。
慕容冲的目光冷森如刀,段随一个激灵,忙摆手道:“凤凰休要胡说!我心中从无有一日敢忘了燕儿!我只恨时至今日,犹自不能杀进长安,宰了苻坚救回燕儿!”
“杀进长安宰了苻坚?哼!那你为何又巴巴跑去长安求和?”
“我。。。”段随支吾不言,也不知该不该把实情告知慕容冲,踌躇间就见慕容冲的脸色越来越冷,无瑕的脸孔在月下看来仿佛戴上了一副白玉面具。段随一咬牙,沉声道:“凤凰你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瞒你。我明着是来通和,其实根本就是来搅局的。邀天之幸,这次事儿办得不赖。凤凰若是不信,只须安静等候,秦晋不久必有一战!”
慕容冲眼中明灭不定,盯着段随看了良久,忽然神情一松,莞尔一笑道:“石头,你莫非忘了?我可是大秦的平阳郡守!你口口声声要坏了两国通和之议,还要杀了天王苻坚。。。你就不怕我当场擒了你问罪?”
“这世道,别人或许会那般无情无义。。。”段随哈哈大笑:“可凤皇又岂是别人?我甘冒大险、千里迢迢跑来看他,只因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最好的兄弟。。。”慕容冲眼睛里闪过一道精光,随即又黯淡下去,声音也低沉不少,几近喃喃:“最好的兄弟。。。”忽然他面孔扭曲起来,声音变得嘶哑:“石头!你可知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这一刻慕容冲的表情极是痛苦,段随看得一阵难过,呐呐道:“凤皇,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罢。。。”
“不可能!”慕容冲咬牙切齿:“你想杀苻坚。。。哼哼,我比你更想杀了他!”
“凤皇!苻坚定然是不会放过的。。。”段随温声道:“然则你也不要太纠结于过去之事。。。”
慕容冲恍若未闻,自语不止:“我还要杀了石越,这厮最是可恨!还有邓羌,当初我失手被擒,全拜这老贼所赐!嗯,还有扶余蔚那个反复小人,若不是他卖主求荣,邓羌何至于大费周章四处抓捕我等?对了,还有。。。”
一连串的名字从慕容冲口中跳出来,段随听得既感心伤,更觉心惊:原来凤皇心中夙怨竟至如此之重,可想而知苻坚伤他何等之深。他本就是个极孤傲的人,这般下去,怕是要变得越发阴郁偏激!
没等段随想出什么话语宽慰凤皇,只听“呼啦”一下,慕容冲长身立起,此刻他已是双眼充血,俊美的脸庞变得凶怖异常:“这些还不够!我定要屠尽天下姓苻的每一个人!不!我要屠尽秦国每一个人!”说到这里,简直状若疯魔!
段随一跃而起,一把抱住慕容冲,猛力用劲,叫道:“凤皇!醒过来!别发疯了!”
慕容冲吃他大力一箍,一个激灵回了点神,怔怔看着段随说不出话来。
“你疯了么?这北国天下千千万万人,你杀得完么?苻坚固然罪大恶极,可又关其他姓苻的何事?”
慕容冲用力一挣脱开段随的双臂,气鼓鼓道:“姓苻的可没一个好人!石头你不用劝我,我。。。”忽然一道倩影在他脑际闪过,清丽动人,叫他心中一阵松软,再也说不下去。半晌,他叹息一声,说道:“石头,我乏了,今夜到此为止。你就不要出去了,且在我府中安生几日,容我探探外间情势如何。若无甚么风声,你便可启程回转江东。”
“也好。。。噢对了,我的坐骑还存在城中一间客栈里,明日我还需跑上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