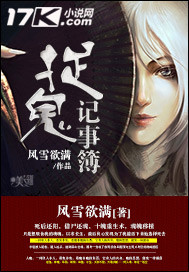(三十三)
我有些疑惑道:“大师,这具骷髅骨,就是这个河中事件的原凶吗?”
“象是,你看他骨头有许多绿色的枯管,这是咱们国内所没有见到的,前些年,我曾听一个缅甸僧人给我讲过,他们那里有一巫术很是邪门,唤作什么降头蛊!就是魂魄受了符咒,能在多年以后为恶。如果,我猜在不错的话,这具尸骨临死前,肯定受了降头蛊!因为死后!被佛爷的消罪真言与六字真言镇压,才不能不致害人,只是这两道真言,必须有法器才能镇压,而法器就是佛患子!”
我惊问道:‘佛患子是什么!”印光呵呵笑道:“佛患子又名木患子,民间叫作念珠。佛言:‘若欲灭烦恼障报障者,当贯木患子一百八,以常自随,若行若坐若卧,恒当至心无分散意!”
我一拍脑袋猛然醒悟:“他的法器就是那一串念珠,念珠线在水底朽断,于是什么消罪与六字真言,竟不攻自破,那我们一把火将他烧了,不就一干二净了!”
印光还没做声,一旁的张教授却道:“这具枯骨现在看来,已管不了多少用了!就是烧了也于是无补!他的怨灵,已不知附于什么物什上。必须先找到附有怨灵的物什,才能将这怪物连根除了,否则尽是制标不制本!”
“那怨灵会不会附在那五具尸体上?”我喃喃的言道。
张教授听了叹了口气道:“不知道!只有看过才能明白!”印光听了也是点头。
于是,我连忙找连长要了车,在政委的陪同下,一行四人去了军区医院。
到了医院,验过手续,我们跟着管理员去了殓房。这里的殓房在地下一层,通往殓房的走道又阴又冷,日光照发着惨白的光线,照在人们脸上,让本已栗惧的心又落了层寒霜。
管理员打开了殓的大门,人还没有进去,一股潮湿刺骨的寒气,夹着一股消毒水与尸臭的味道,直种人们的肠胃,竟让人打了一个哆嗦之外,还有一阵阵恶心。地上正是云南四月,阳光灿烂的日子,而这里,却是如入寒冬,更象步入了九幽黄泉。管理员带我们来到一排柜子前,轻轻将一只大抽屉拉出,却见里面躺着一具塑料袋封装的女尸。透过塑料袋可以看到,那姣好苍白的面颊,挂了一层冰霜。
“张丽英,就是她——就是她啊!”杨婶声音嘶哑喊了几声,便扶着抽屉抽抽咽咽的哭了起来。塑料袋被管理员打开,往下拉了拉露出死者的头部。张定疆与印光低头看了看尸体,道:“她真是死了几十年吗?”杨婶边抹眼泪边应了声是。却听印光道:“一具尸体能在几十年后,还如此完好,这本身就是邪魔歪道!”
杨婶边哭着,边抚摸着尸体的脸,我听着她絮叨着那些沉年往事,心里也觉一酸。这个尸体确实象刚刚死去一般,虽然远没有在刚出墓时鲜活,但这么美的死尸,却是很少见的。杨婶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死尸的脸上,我正想询问印光与张教授,是不是查着些蛛丝马迹。
这时,却听身后有一个声音冷冷的道:“哭什么,跟我们一同去吧!就为了等你,我们这些年才一直栖在水底的!”声音非男非女,金属磨擦般刺耳。
我回头急看,原来声音出自那个管理员,却见他双目里似是有一团雾水,迷迷离离没有一点神采。却听印空道:“他被脏东西附了体!小心些!”我心头却有些发怵,却听“喀叭”的一声轻响,我顺声音看去,却是政委已将手枪打开了保险。
张定疆道:“他是鬼附体,不能用枪,否则这个管理员会死的!”他的话让政委一呆,竟自将枪收起。
“孽障!你该回头了,这些年来多少人为你们枉死,回头是岸哪!”印光望着那个管理员道。
“回头!我们向那回头!我只想用你的血来暖暖身子!”他边说边缓缓向我们走近。
猛得,那个管理员一侧身,一双手直扣向杨婶的脖子,我吓得“啊!”了一声,正要施救,却见杨婶身上红光一闪,那个管理员竟直摔了出去,我正在惊奇,却见那个管理员哼哼唧唧的从地上爬起,道:“我——我这是怎么啦!哎哟!好疼!”边说边揉屁股,看来是摔着不清。
我扶住杨婶的胳膊问道:“杨婶,你没事吧!”杨婶低低的说了一声:“没事!”却听张教授吼了一声:“快闪开!”只觉身子被人猛撞了一下,不由主拉扯着杨婶倒在了地上,却听“呯”的一声枪响,正打在刚才杨婶所站的地方,我抬头看去,却见政委又抬起了枪,指向杨婶,就在千钧一发的关头,一个灰影撞向了政委,却听又是一声枪响,子弹正打在天花板上,政委口中‘嗬嗬’作响,又要举枪再射,只见他手上一阵金光灿然,只听政委一声尖叫,这种又尖又细的声音根本不象从他口中发出。手枪已掉在了地上。细看,原来他的手腕上,竟挂了一串暗红色的念珠。随着印空手势一动,一点黄影掷入政委口中,而印空的一双手,已掩在政委的口上,随着政委的手脚一阵脚乱挣乱动,却听“扑哧”一声,一股臭气散了开来,却原来政委屎尿齐流,我正要上前问个究竟,印空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却听张定疆笑道:“你用符咒打散那东西的魂魄,又用手印封住政委的口鼻,让那东西不得不随粪便拉出,让它永世不得超生,这个做法,似乎狠了一些!一会政委醒了,让你赔裤子,我看怎么办!”却听印光淡淡地道:“除恶务尽,既然佛法不能将他们点醒,那只能让它永世再难超生了!”
我扶起杨婶,想去再看看政委,却听政委在地上说:“好臭,好臭,是谁拉了屎了!”边说边从地上坐起,却听他惊叫了一声道:“我——我怎么——!”他的话没有说完,已是满面通红了。原来,直到他坐起,才觉得屁上粘呼呼的,竟是自己弄了一裤裆黄白之物。
这时,杨婶已将脸扭向一边,我只得笑着示意政委赶紧将裤子脱了。就在这时,殓房中的日光灯“啪”地一声爆响,紧跟着屋中一片漆黑,却听身前一阵“哗啦啦”乱响,一只只存尸柜,竟自己跳到了地上。张定疆大吼一声:“大家小心!”却见眼前一亮,定睛再看时,只见一张黄纸,正在他右手二指间燃烧。就在我们身侧不远处,停尸柜中一个个死尸竟自站起,胳膊一阵乱抓,便将套在身上的塑料袋扯碎。然后,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印空和尚大袖一挥,正要动手,却听张定疆道:“大师!你看我的!”说着,又一张黄纸燃起,他向前一跃,正拦在一个僵尸身前,身子向旁一侧,躲过僵尸的一抓,手势微晃,手中那即将燃尽的纸符,正按在僵尸两眉之间,那僵尸一声低吼,一跤摔倒,只见手足一阵抽搐,便再也不动了。那张振疆的一番动作,直看的我桥舌不已。却见他也不停留,只在这些死尸间,左一闪右一晃,手中的符纸不断亮起,片刻的工夫,地上已横七竖八尽是倒尸。
却听,印光道:“刚才我掩政委口的时候,发变原来这几具女尸,是被一根草叶封了魂魄,找找那几具女尸,只要将那根草叶,从她们口中抠出,便都一切正常了!”说着站起,便同张定疆一齐搜索起死尸来了。
这时,那个管理员已经吓得半死,手软脚软的趴在地上呼救,我上前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道:“全都没事了,你还在这儿叫唤!在装死我叫个死尸,卡死你!”我的话还挺灵,声音才住,他竟一下从地上跳起哭求道:“尸大奶奶——鬼大姨妈,你们千万别杀我呀!你说什么我都听你们的就是了!”我听着好笑道:“你们这有应急灯吗!”却听那个管理员应了一声“有”。我急叫他打开。
灯光在门口上方亮起,却见印光与张定疆站在一具尸体旁,我一眼便认出那具尸体,正是我们班长许大山的,我由于好奇,竟走到了他们后面。看见张定疆正的用手指,揉按尸体的腮边,他每揉按一下,尸体的口竟张开一些,只一会工夫,那尸体竟将口张的大大的,一股粘恶的臭气从口中散出,我用手掩住口鼻,却听张定疆道:“大师确实如你所说,他们的舌头已变成了水草的叶子,只是他的比较明显,连背上都生出了水草,邪门邪术!真是邪门邪术!”
印光合什道:“阿弥陀佛,按贫僧来看,他不过水草的茎叶,那真正的根系,却是那五具女尸与棺底的白骨。”
我听了十分惊奇,问道:“大师你怎么说他们是根系茎叶,我可让你们闹糊涂了!”印光又育了一声佛号道:“怪棺底上的骷髅,用水草捕住五女,吸了她们的魂魄与血气,只留下她们心里的怨灵,做为它的茎,然后五女尸再捕食其生人魂魄与血气,也只留下他们心中的怨灵,做为茎上的枝叶,它们象是一株不死不灭的植物,叶子捕到食物后,吸取血食,供给茎,茎再将血食自己留一部分,剩下的再供给最后的根系,而这个根系,便是八百年前被斩杀的波岩,倒底这具骷髅,是受了什么符咒,其目的为何咱们不得而知。当时,施以符咒的人,其用心真是险恶。现在,他的茎与叶都没了,而那骷髅的怨灵,只能靠自己去寻找食物了,这也是你们连队命案连连,但倒底骷髅的怨灵附在何物上面,那得要细细察找了。”我听了不由一默然,这个连环命案,皆由骷髅的怨灵而来,只是那怨灵隐匿在何处,却又不得而知。
看完了尸体,我们几个人一齐动手,将这些死的不能再死的死尸,装入抽屉,塞入了存尸柜。就在出来的时候,我见政委下体怪异。细看之下,我竟差点笑出声来。原来,他竟用裹尸体的塑料纸,将下体围起,活象傣家人穿的筒裙,只这种材质的筒裙,虽说能遮住一些羞处,但那种朦胧美还是能看到的。见他这个样子,我心里却有了分教,此正是:政委含羞莲步摇,顾盼生春臭且骚!
好在出了殓房,政委向管理员借了条裤子,便一头扎进卫生间,卫生了好半天才肯出来,只是一见我们眼光怪异,自是尴尬非常,在一阵玩笑声中,众人登上了车,却向连队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