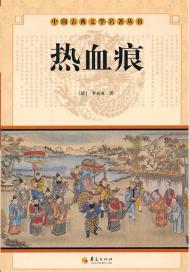却说黄子文搬到了大栈房之后,过了几日,又在新马路华安里租了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又去租了两房间外国木器,搬了进去,陈设起来,居然焕然一新。黄子文诸事没有动手,先把一块洋铁黑漆金字招牌,钉在墙上,做个媒头,招牌上大书“兴华书局”,天天引的那卖机器的掮客,卖铅字的掮客,来了一批又是一批。黄子文却毫不理会,只是吃他的酒,碰他的和。人家问问他,他总说是:“这事其难其慎,不是旦夕可以奏功的!”人家也懒得问下去了。
黄子文在上海如此胡闹,早有人传到了他的家乡。他家乡是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一个什么村上,家里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母亲,守着几亩田过日。这回听见人家说儿子在上海发了财了,便和邻里们商量。邻里们撺掇道:“你何不自己去找他?”
他母亲道:“他在家的时候,常常要与我吵闹,如今我去找他,他倘然不认我呢,这便怎处!”邻里们道:“老太太,凡是人总有个见面之情。何况你们自己少爷,这是天性之亲,有什么不认的?”他母亲摇头道:“我那不肖儿子,动不动就讲什么‘命是要从家庭之内革起的。’那一派话头。所以和我吵闹起来,便睁着眼睛,捏着拳头说:‘我和你是平权,你能够压制我么?’常常这个样子。此番前去一定受了气回来,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家里也不知道作了什么孽,生出这种后代。祖宗在阴司,想也在那里淌眼泪呢!”说到这里,这老婆子便呜咽起来,众人连忙劝祝过了几日,他母亲忽又心活,将门户交代了一个小丫头。
检点检点,带了个小小的包裹,趁着便船,过了江,到了钱塘门。由钱塘门雇乘轿子,直抬到拱宸桥租界大东公司码头。老人家是鼠惯的,只趁烟蓬,只得一天半,到了上海。可怜她举目无亲,只得借住在一爿小客栈里,慢慢的打听。打听了三四天,方才打听着,问明了一切。次日起来,算清帐目,背了小包裹,拄了根拐杖,一步一步的直摸到新马路华安里来。
且说黄子文因为这两天将近中秋节了,堂子里担盘送礼,络绎不绝。人家是要躲掉她们,可以省花两块钱;他却在家里候着,以示阔绰。然而两天之内,已去了几十块了。这天起来之后,心里想道:“如何没有一个送盘来的?算算还有小桃红、张媛媛、王宝宝、周雪娥等二十余家,难道她们约齐了才来么?”一会儿在楼上踱踱,开开柜门,取出一瓶香水,细细抚玩了一番,心里想道:“这瓶香水是要留着给张缓缓家小阿金的了。她得着了这瓶香水,不知如何快活呢!”正在胡思乱想,听得楼下呀的一声,像是一个人推门进来。又听得喘喘吁吁的声音,赶上楼来。心里吃了一惊,将香水瓶放在桌子上,刚要想自己下去看,那人却早上来了,先叫了一声“儿啊!”黄子文这一惊,如青天掉下霹雳来一样。定睛一看,不是他的母亲还是何人?惊定了,气便跟了上来。老人家已经挨到写字台边坐下,唠唠叨叨,埋怨个不了。黄子文一声都不响,立起身来,关了柜门;又把钥匙开了铁箱,把所有钞票洋钱,尽行塞入身边,登、登、登的头也不回,下楼而去。他母亲这一气,气得几乎发昏,女人家有什么见识呢?无非是哭而已矣!
且说黄子文出得门,气得脸都发了青了,有人招呼他,他也不看见。本来想到四马路去的,看看越走下去越冷落。止住脚步一看,原来快到张园了。心中想道:“我气了一气,走路都会走错了。看来养气功夫尚差。”于是拨转身来,叫了一部东洋车,拉着如飞而走。到了迎春坊口停车,给了一角小洋钱,大踏步径到张媛媛家。上了楼之后,房间里却是静悄悄的。媛媛尚睡在床上。一个老娘姨在那里揩台抹凳,见了子文,招呼进去,在炕床上坐下。
那个老娘姨去叫醒了张媛媛,便去舀脸水。媛媛道:“大少,耐倽能格早介?”子文道:“舍故歇辰光勿作兴打茶围格?”媛媛道:“作兴格,作兴格。”一面说,一面跨下床来,趿了拖鞋走到炕床面前,揉揉眼睛,对着子文着:“耐是勒亻舍场化住仔夜出来哙?面孔浪难看得来。”子文道:“勿要瞎三话四,倪是再规矩呒不!”媛媛拿嘴一披道:“啥人相信!”
子文道:“真格勿骗耐。”媛媛道:“耐拿面镜子自家照照看吧。阿像格来?”子文道:“耐阿是说我面色勿好看啊?格是刚刚搭倪老太太拌仔两句嘴舌落。”媛媛道:“倪曾勿听见耐说歇该搭有倽老太太呀。”子文道:“还是今朝勒绍兴来格勒。”媛媛道:“大少,格格是耐勿是哉!唔笃老太太第一日到该搭,耐就搭俚呒不好说话,格是算亻舍一出?倪堂子里格人,也勿造至于哙!耐大少是读书人,亦懂洋务,只怕中国外国才呒不格种理信格!”
这番话说得黄子文良心发现,满面通红,只得挣扎着说道:“依耐末那哼介?”媛媛道:“依倪末蛮便当格:拍拍俚格马屁,请俚看看戏,吃吃大菜,坐坐马车,白相白相张园。老太太哚曾勿到歇上海来格,看见仔格种,自然勿开心也开心哉。”
子文摇头道:“勿局,勿局!我有戏勿会自家看,我有大菜勿会自家吃,我有马车勿会自家白相张园,倒去让格格老太婆写意?俚也勿曾生好格副骨头!”媛媛道:“耐格种人呀”又用手指头指着子文道:“真正是只众生!”子文拿脸一沉道:“耐骂我亻舍哉?”媛媛正待回言,老娘姨已掇了脸水进来,说:“先生揩面吧。”媛媛过去盥漱,方才打断话头。媛媛盥漱之后,小阿金与她解开头发,坐在窗下梳头。子文无精打采,坐在那里呆呆的思想。
看官,你们道黄子文想什么?原来是出脱他的母亲的念头。
左想不好,右想不好,到后来想定了一条绝妙主意,不觉眉飞色舞起来,登时立起身来。媛媛道:“再坐歇去。”子文连道:“勿哉,勿哉!”媛媛只得听他扬长而去。
他出了迎春坊,看看天色尚早,便一人踱到金谷香,吃了几样大菜,签过了字,仍回新马路华安里。推门进去,新雇的小使名唤来喜,迎着诉道:“老太太刚刚住哭。少爷你什么地方去的?为何弄的她老人家这样的伤心?”子文听了,心里也有几分过意不去,急忙赶上楼去,看见他母亲正坐在他那张铁床上,垂头丧气,默默无言。
子文见了他母亲,便自靠在台子上,和他母亲说道:“一个人总要自立,你苦苦的来寻我做什么?”他娘正没好气,对他道:“来寻你做什么?寻你要吃!寻你要穿!”子文道:“既然要吃要穿,更不可不自立!”他娘道:“你张口自立,闭口自立,怎样才叫做自立?”子文道:“自立是全靠自己,不依仗人家的意思。”他娘道:“我这样大一把年纪了,天上没有掉下来,地上没有长出来,难道还叫我去当**不成?”子文道:“胡说,胡说!谁叫你当**?我只要是叫你读书。这读书就是自立的根基,这里头什么都有。”他娘道:“真正笑话!这不成了‘八十岁学吹鼓手’了么?”子文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城里有个强种女学堂,学堂里都是女学生。可敬啊,可敬!她们都是牺牲其身而报国家的,你老人家要是进去了,于我的面上光荣不浅。”他娘道:“我只要有饭吃,有衣服穿,不要说是女学堂,就是仁济善堂、广济善堂,我也去的。”子文听了,不胜之喜。当下又窝盘了他娘几句,他娘的气也渐渐的平下来了。
子文当下写一封外国信给城中强种女学堂,说:“今有家母要来念书,伏乞收留。”等语。午后,差了一个出店的送了去。良久,良久,方得回信,说:“后天是开学的日子,可请老太太前来,敝处当拭几候教。”子文看了无话。
原来这强种女学堂总理羽衣女士接到子文信后,心里想道:“他的老太太一定博学多才,这回进来,是要来作教习。”刚好堂上出了一个教习的缺,便与监院、监起居那些人商量。大家一听是黄子文的母亲,有什么不造成的?当下商议定了,才写这封回信,所以下这“拭几候教”四字。黄子文虽然通彻,他老太太从小种田出身,却是一字不识,黄子文当下又教导了她许多规矩,说:“不要叫人家笑话,扫我的脸。”他母亲只得一一记下,专等开学那天,便去念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