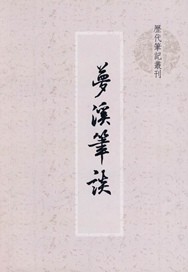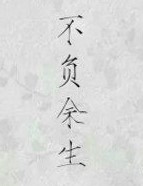且说雪畦听了森娘一席话,目定口呆。心中只不信有这等老实的人,更不信有这样一个老实人,便有那样一个好外国人。
一面想着,把中的牌都忘记看了。定了定神,方才一面打牌,一面说道:“我不信有这等好外国人。”能君道:“这也论不定的。就是蔡以善,他初到上海时,不过在近今洋行账房里做茶房。一天,大班到账房里寻买办说话,那蔡以善土头士脑拿了一枝水烟袋,装上一口烟,递给大班。谁知外国人是不吃中国水烟的,对他摇摇头,他却把装好的那点烟挖了出来,依旧放在烟盒里。那大班见了,说他鼠惜物,便对买办赞了他两句。
那买办看见外国人都赏识了他,便叫他去读外国书、学外国话,读了半年,略略懂了两句‘也斯哪’,买办便告诉了外国人,叫他做了写字楼细崽。一则也是他福至心灵,处处懂得巴结,二则也是人才难得,近来居然升了二买办了。”
四个人一面说笑一面打牌,不觉直到天亮。玻璃窗上透出白光,方才收场,算了算账,却是子镜大赢。子镜便道:“好,我今夜请客,诸位务必要到。”诸人未及回答,忽听得外面门声大震,有人打门。森娘忙叫人去开时,那丫头和阿宝都已睡了。幸得楼下同居的,出去开了门,外面急匆匆走了一个人进来。直到楼上,问:“木子镜有在这里没有?”子镜忙应道:“在这里。什么事?”那人便到房里来,道:“出了一个大窃案,失赃值到二三万。此刻外国人恼的了不得,叫找你呢。”
子镜道:“不要紧,我就去。”说罢那人先去了。森娘一面叫起丫头阿宝泡水买点心,云旃早钻到床上去睡了。三人洗过脸,吃了些点心,方才下楼。雪畦留心看时,原来楼下是裁缝店,三人出门分手。
雪畦回到成章栈,要想略睡片时,却偏睡不着。闷极无聊,便走到三马路去看又园。叩了两下门,只得一个蓬头亦脚的丫头出来开门。雪畦问:“又园可在家?”丫头道:“才起来呢。”雪畦走了进去,只见又园就在客堂里一张半榻上睡觉,此时已经起来,却还坐在榻上用一张被窝盖了下身,上身穿了一条打补丁的破小袄,手里拿着一件已变成灰色的白洋布裤子,一只手拿着针线,看见雪畦进来,一面欠身招呼,一面放下针线,一面把裤子缩到被窝里去。半晌方才下地,道:“花兄好早。”
雪畦道:“我昨夜一夜未睡,早上无聊之极,所以来望望你。”
又园道:“为甚一夜不睡?”雪畦便把赴席打牌情形述了一遍。
又园道:“花兄,阔得很,结交的多是阔佬。”雪畦道:“甚么阔佬不阔佬,不过都是同乡罢了。像蔡以善,我还记得他是在澳门阉猪的。隔别了不多几年,他居然是二买办了,无非是一步运气罢了。”又园道:“说起运气来,真是气死人。言能君那厮,他本是一个木匠,因为工艺不好,生意总不如别人。前年年底下穷的和我一般,身边剩了一块寡洋钱,恰好我也有一块洋钱。我两个同到赌台上去。”雪畦道:“这里也有赌台么?”又园道:“为什么没有。你才说的木子镜便是赌台上保标的头儿。那回我和能君同去赌,我便没运气输了。回来他却一口气中了五回宝,一块洋钱就变了二百多。我要和他借两块过年,他都不肯。过了年之后,听说他也是有赌必赢,就开起一家言合隆木匠店来,此刻居然老板了。我们这些穷朋友他一发不认得了。”雪畦听到这里,猛然省悟,暗想道:“他此刻穷到如此,我何苦来望他?这总怪自己阅历不深之故,万一和他厮混的多,他向我借钱起来,若是借给他呢,正不知何时始还,若是推托了,又未免结怨这等小人,还是远避的好。”想罢,正搭讪着要走,又圆又道:“不似你,到底是个好人。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来看我两次。我今天就要动身,到福州去了。”雪畦道:“你到福州做什么?”又园道:“前回我不是和你说过的么。隔壁那咸水妹的东家是做兵船上生意的,此刻那兵船要开到福州去。恰好他向来用的细崽是宁波人,宁波家中有信来叫了他回去,所以那东家就叫我跟了去,好歹也赚他七八块大洋钱一个月。先混起来再说,只是此时身边零用钱一个都没有,求你借我一两块钱。我到了福州挨到一号,支了工钱,就寄回来还给你。”雪畦道:“这个可以使得,但是我身边没有带着,回来送来罢。”又园道:“不敢,等一会我来走领。船要到三点钟开行,我一点钟到船上去,一点钟以前我到你栈里去吧。”
雪畦答应了,又拖延了良久,方才出来。便走到庆云处,托言亲来多谢。坐了许久,又出来到能君所开的合隆号里去,谈了半天,问了子镜的住址,又去访子镜,子镜一见了雪畦,便拍手道:“来得好,来得好,我在这里请伙计吃饭。俗语说的好,相请不如偶遇,请坐罢,马上就要摆席了。”雪畦道:“你不说晚上请客么?怎么请吃中饭起来?”子镜道:“我此刻是请伙计。今天绝早不是有人来叫我么?因为昨天晚上出了窃案,失赃值到两万多。失主五点钟报案,我六点钟到巡捕房里去,问明白了公事,八点钟就破了案。巡捕头喜欢的了不得,一连赞了我五六声“拉姆罢温”好不威风有体面。然而这件事我是全仗众伙计之力,所以特地请他们吃一顿。好了,你代我陪客。”雪畦乐得答应。一会儿摆开了两桌,请了那一班伙计入席畅饮,却与昨夜的局面不同。所有的菜都是肥鱼大肉,那一班伙计又都是歪了帽子、散了扣子、束腰带束在马褂外面的。
不一会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吃个馨荆吃完,便都散了。雪畦此时喝了两杯酒,加以昨夜未睡,所以十分困倦了。要想回居章栈睡觉。看看子镜家里所挂的钟只得十二点一刻,恐怕又园来借钱,只得强打精神延时刻,等过了一点钟时候,方才回栈,睡了一天。等到夜来,子镜请客时,他还是关门睡觉,竟错过了。闲话休提。
且说雪畦自从与那一班人结交之后,每日领略些发财秘诀。
便约了一个姓袁的同乡,合出资本开了一家米店。雪畦馨其所有,只得三千金。姓袁的出了七千,合成万金资本,当下两个订了合同,雪畦不会写字,央人代了笔,念给他听了。姓袁的画了押,雪畦也勉强画了十字。从开了这家米店后,倒也年年顺利,四五年间,无不赚钱。雪畦便把家眷接来上海,只有姓袁的生性孤峭,又且平日视钱如命,恐怕接了家眷来费了开销,所以向来只有一个人在店里,生平又绝少交游,朋友也不多一个,被雪畦看在眼里,早就存了一个不良之心。恰好这一年夏天,上海闹时症,姓袁的染了一病,死在店中,雪畦自少不得买棺盛殓,送入山庄,那时广肇山庄只怕还是初成立呢。
且说雪畦打发姓袁的后事既毕,回到店中寻着了他的钥匙,把他的箱子打开,先寻着原订的合同用火烧了,又寻出了好些股份票及钱庄存折之类,一股脑儿都收拾到自己腰里。然后发信到广东给姓袁的儿子,直等到半个月后,那儿子方才赶到。
其时那米店已经弄得有岌岌可危之像了。及至查考起数目来,雪畦非但把合股的事赖过,还说姓袁的亏空了数百元,少不得父债子还,要向他儿子索龋开出箱子来,除了几件衣服之外,竟是一无所有的了。他儿子要争论时,又苦于没有证据,此时雪畦的羽党极盛,如陶庆云、陶俯臣、言能君、舒云旃、陶秀干、蔡以善等辈,一个个都是近来几年新发大财的,加以木子镜是个办公人役的头儿,言能君又有一个换帖兄弟金行瑞是做御史的,都帮着在场恫喝。姓袁的儿子没法,只有忍气吞声,扶了灵柩回去。雪畦就安安稳稳的干没了这一注巨款,撇了那米店不做,另外开了一家字号,专做客货。
开张那天,一班发财朋友都来贺喜。恰好魏又园从福州回来方到了,脸上气色十分光彩,与大众一一相见,叙了些契阔的话。雪畦置酒相待,席间问起又园别后之事。又园道:“说来也是惭愧。自从别后跟了两年东家,后来船上的管事故了,东家便派了我做管事,十分赏脸,也十分信用。不多几时,福州的福山洋行缺了一个买办,东家便把我荐了上去。承新东家的美意,也十分相信,此刻又荐到上海有利银行来,这都是托列位老朋友的洪福。”庆云呵呵大笑,道:“什么朋友洪福,这都是东家的栽培。我们同在**时,虽是人人心中巴望有今日,却不敢说是一定有今日。此时巴望着了,列位知道其功在那里。”蔡以善道:“这是各人靠本事去干出来的。”舒云旃道:“全靠会看东家颜色。”庆云道:“你两位的话都不错,然却不曾说到根本上来。”能君道:“什么根本?”庆云道:“根本就在懂说话。你想如果不懂说话,就有本事也无从干起。就会看颜色,也轮不到你看,所以我历年以来所著的那部学外国话的书,近日已经发刻了,不久就可以刷印成书。成书之后,我卖四块洋钱一部,等我们中国人看了,都从这书上学起话来,好叫一个个的中国人都懂了外国话,发了洋财,那时才知道外国人的好处呢。”能君不服道:“未必,未必!就以坐中而论,我和雪畦都是不懂外国话的人,难道也靠外国人?子镜是懂了外国话的了,何以他反不及雪畦?”庆云道:“雪畦是例外的,十中无一。至于你呢?因为不懂外国话,每年所包工程,暗中吃亏的也不知多少。外国人是好人,断不欺你,只是在当中代你翻译的,你知道他都靠得住么?子镜呢?你莫说他不及雪畦,他开的那伙食行,一年要做到四五十万的生意,也就可观了。”
能君正要驳话,忽听得座上一人说道:“不错埃”正是:抑己扬人莫怪此公饶舌,欧风美雨至今已遍中原。
写雪畦自结识了那一班朋友之后,每日领略些发财秘诀,下之紧接约了一个姓袁的同乡云云,是写雪畦发财,实得陶庆云以次诸人之心传也。故只写雪畦干没,雪畦发财,其余诸人是毋庸再写,亦足窥其发财历史之一斑。今人有欲发财者乎?隐窥秘诀,于是乎得之矣。雪畦虽默得诸人之心传而发财,然窥其心迹,已具有发财之资格矣。于何见之?于其待魏又园见之。若士君子之以朋友为性命者,实穷相乞儿所为耳,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