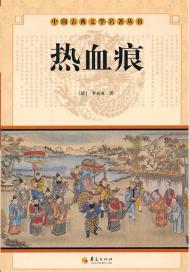“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
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惭?擎一既结集其文,复欲为作小传。余谢之曰:“若某之行谊经历,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若必不获已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谭浏阳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宁效颦焉。”作《三十自述》。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
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顾闻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于阴德,力耕所获,一粟一帛,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王父讳维清,字镜泉,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宝瑛,字莲涧。夙教授于乡里。母氏赵。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
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三岁仲弟启勋生,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
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祜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舶,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
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挚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粤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着《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着《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着《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弃养。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
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
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着《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赞,力辞之。
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丁酉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着《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陈中丞宝箴,江督学标,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就之。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复生亦归湘助乡治,湘中同志称极盛。未几,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余颇有所赞画。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刘裴邨、林暾谷、唐绂丞,及时务学堂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树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暾谷、叔峤、裴邨,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去国以来,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己亥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即今之清华学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絷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国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
留沪十日,遂去,适**,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东,环洲历一周而还。辛丑四月,复至日本。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1902年12月)
杂答某报(节录)
此问题含义甚复杂,非短篇单词所能尽也,此略述其所怀,若其详则异日商榷之。
中国今日若从事于立法事业,其应参用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之精神与否,别为一问题;中国今日之社会经济的组织,应为根本的革命与否,又别为一问题,此不可混也。
今先解决第一问题,次乃附论第一问题。
吾以为中国今日有不必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会革命之理由。
于本论之前,不可不先示革命之概念。凡事物之变迁有二种,一缓一急。其变化之程度缓慢,缘周遭之情状,而生活方向,渐趋于一新生面,其变迁时代,无太甚之损害及苦痛,如植物然,观乎其外,始终若一,而内部实时时变化,若此者谓之发达,亦谓之进化(Development of Evolution)。反之,其变化性极急剧,不与周遭之情状相应,旧制度秩序,忽被破坏,社会之混乱苦痛缘之,若此者谓之革命(Revolution)。吾以为欧美今日之经济社会,殆陷于不能不革命之穷境;而中国之经济社会,则惟当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请言其理。
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者何也?彼欧人之经济社会,所以积成今日之状态者,全由革命来也。而今之社会革命论,则前度革命之反动也。中国可以避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为再度之革命。夫谓欧人今日经济社会之状态全由革命来者何也?
欧洲当十七八世纪之交,其各国人之有土地所有权者,于法不过四万人,于英万九千人,于奥二万六千人,合今日耳曼诸邦,不过二万人,他国略称是。而当时全欧总民数,既在一万六千万人以上,于一万六千万人中,而为地主者不及二十万人。盖欧洲前此之农民,大半在隶农之地位,是其贫富之阶级,早随贵贱之阶级而同时悬绝矣。幸而彼之个人土地私有权,发达甚迟缓,未全脱前此部落土地所有权之时代,(英国自一七六○年至一八三三年凡七十余年间,有所谓“共有地”者渐次改为私有地,其地凡七百万英亩。一英亩约当我四亩六分余也。)故贫民稍得以此为养。农业以外,则手工业亦颇发达。其习惯有所谓工业组合者,约如我国各工业之有联行。**之对于农业、工业,皆制为种种法律以保护干涉之,故虽不能有突飞之进步,然亦相安而致有秩序,此欧洲旧社会组织之大略也。及斯密亚丹兴,大攻击**干涉主义,而以自由竞争为楬橥,谓社会如水然,任其自竞,则供求相剂,而自底于平。此论既出,披靡一世。各国**,亦渐为所动,前此为过度之干涉者,一反而为过度之放任。其骤变之影响,既已剧矣。
同时而占士·瓦特发明蒸汽(一七六九年),未几李察又缘之以发明纺绩器,于是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而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Revolution)之时代以届。前此人类注其筋力之全部以从事制作,虽或间附以牛马力等,然利用自然力之器械,殆可谓绝无。及汽机发明,其普通者视人力加十二倍,或乃加数百倍至千倍,则试谉其影响于社会之组织者何如,生产之方法,划然为一新纪元。以一人而能产前此十二人乃至数百千人之所产,则其所产者之价值必骤廉,前此业手工者,势不能与之竞,而必至于歇业。前此执一艺者,所得之利益,自全归于其手,偶值其物价腾,则所得随而益丰,但恃十指之劳,苟勤俭以将之,虽窭人可以致中产,故于工业界绝无所谓阶级者存。及机器既兴,无数技能之民,骤失其业,不得不自投于有机器之公司以求糊口。而机器所用之劳力,与旧社会所用之劳力又绝异。前此十年学一技者,至是而悉不为用,而妇女及未成年者,其轻便适用,或反过于壮夫,而壮夫愈以失业。
前此工人自制一物,售之而自得其值,今则分业之度益进。与其谓之分业,毋宁谓之合力。每一物之成,必经若干人之手,欲指某物为某人所制,渺不可得。而工人之外,复有供给其资本与器具者,又须得若干之报酬。故欲求公平之分配,终不可期,不得已而采最简单之方法,行赁银制度。即出资本者,雇用若干之职工,每人每日,给以庸钱若干,而制成一器,所得之赢,悉归雇主。
而雇者与被雇者之间,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划然成两阶级而不可逾越,此实旧社会之人所未梦见也。夫物质界之新现象既已若是矣,使思想界而非有新学说以为之援,则其激变尚不至如是其甚。前此在工业组合制度之下,其物价或以习惯或以法律羁束之,若有一人忽贬价以图垄断,则立将见摈于同行而不能自存,于其物之品质亦然,大率一律,而竞争之余地甚狭。及机器一兴,生产额忽过前此数倍,非低廉其价值,改良其品质,则将无销售之途。适有自由竞争之学说出而为援,前此之习惯法律,一切摧弃,无所复用。制造家惟日孜孜,重机器以机器,加改良以改良,其势滔滔,继续无限,以迄今日;一般公众,缘此而得价廉质良之物;而社会富量,亦日以增殖,其功德固不在禹下。然欲制价廉质良之物以投社会之好,彼无资本者与有资者竞,则无资本者必败;小资本者与大资本者竞,则小资本者必败;次大资本者与更大资本者竞,则次大资本者必败。展转相竞,如斗鹑然,群鹑皆毙,一鹑独存。当其毙也,则感莫大之苦痛,牺牲无量数之资本,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然后乃造成今日所谓富者之一阶级。(大资本与小资本竞,而小资本全致亏耗,故曰牺牲无量数之资本。无资本者虽有技能不能自存,此牺牲劳力者一;当小资本与大资本竞时,各雇用劳力者,及小资本失败,而所雇用之劳力者,随而失业,此牺牲劳力者二。故曰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呜呼!一将功成万骨枯,今日欧洲之经济社会当之矣。然军事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犹得有休养生息之时;经济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乃永沈九渊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论所以不能不昌也。而推其根原,则实由前此工业组织之变迁,不以进化的而以革命的,如暴风疾雨之骤至,应之者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任其自然,遂至偏毗于一方而不可收拾。而所谓应之失措者,其一在**方面,其一在人民方面。其一在**方面者,则放任太过,虽有应干涉之点而不干涉也;其在人民方面者,多数人民,不能察风潮之趋向而别循新方面以求生活也。美国经济学大家伊里(R.T.Eey)曰:“使当工业革命将至之前,工人有识见高迈者,能合多数工人为一团,置机器,应时势而一新其制造法,是即地方之组合也,即一种之协立制造会社(Coperative Factory)也。果尔,则工业组织之过渡可以圆滑而推移,而后此之骚扰革命可以免。惜乎见不及此,墨守其故,终至此等利器,仅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驯至今日积重难返之势,可叹也。”
其意盖谓使今日劳动者阶级,当时能知此义,则可以自跻于资本家之列,而奇赢所获,不至垄断于少数也。此诚一种之探源论也。虽然,吾以为当时欧洲之多数人民,即见果及此,而于贫富悬隔之潮流,所能挽救者终无几也。何也?彼贫富悬隔之现象,自工业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业革命以后,则其基益巩固,而其程度益显着云耳。盖当瓦特与斯密之未出世,而全欧之土地,本已在少数人之手,全欧之资本,自然亦在少数人之手。其余大多数人,业农者大率带隶农之性质,所获差足以自赡耳。其业工商者,赖其技能,以糊其口,虽能独立,而富量终微。逮夫机器兴,竞争盛,欲结合资本以从事,则其所结合资本中之多量,必为旧有资本者所占;其余多数中产以下者,虽悉数结合,而犹不足以敌彼什之一。故彼工业革命之结果,非自革命后而富者始富贫者始贫,实则革命前之富者愈以富,革命前之贫者终以贫也。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现象者,原因盖有数端。一曰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其贵族大率有封地。少数之贵族,即地主也,而多数之齐民,率皆无立锥焉。生产之三要素,其一已归少数人之独占矣。(经济学者言生产三要素,一曰土地,二曰资本,三曰劳力。)故贵族即兼为富族,势则然也。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此后虽死灰偶烬,而终不能长存。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尽,虽以亲王之贵,亦有岁俸而无食邑。白屋公卿,习以为常,蓬荜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而富力之兼并亦因以不剧也。二曰行平均相续法。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自法兰西大革命后,虽力矫此弊,而至今迄未尽除。夫长子相续,则其财产永聚而不分,母财厚而所孳生之赢愈巨,其于一国总殖之增加,固甚有效,然偏枯太甚,不免有兄为天子、弟为匹夫之患,一国富力永聚于少数人之手,此其敝也。我国自汉以来,已行平均相续法(此事余别有考据),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沾之。其敝也,母财碎散,不以供生产,而徒以供消费,谚所谓“人无三代富”。职此之由,盖拥万金之资者,有子五人,人得二千,其子复有子五人,苟无所增殖而复均之其子,则人余四百矣,非长袖则不足以善舞。我国富民之难世其家者,非徒膏梁绔袴之不善保泰,抑亦制度使然矣。虽然,缘此之故,生产方面,虽日蹙促,而分配方面,则甚均匀,而极贫极富之阶级,无自而生,此又利害之相倚者也。三曰赋税极轻。欧洲诸国,前此受贵族教会重重压制,供亿烦苛,朘削无艺,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而一切负担,全委诸齐氓。及屡经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积弊方除,而产业革命已同时并起,无复贫民苏生之余地矣。中国则既无贵族教会梗于其间,取于民者惟一国家。而古昔圣哲,夙以薄赋为教;历代帝王,稍自爱者,咸凛然于古训而莫敢犯,蠲租减税,代有所闻;逮本朝行一条鞭制,而所取益薄。当厘金未兴以前,民之无田者,终身可不赋一铢于**,劳力所入,自享有其全部。夫富量由贮蓄而生,此经济学之通义也;而所贮蓄者又必为所消费之余额,又经济家之通义也。然则必所入能有余于所出,而后治产之事乃有可言。欧洲十八世纪以前之社会,齐氓一岁所入,而**、贵族、教会,朘其泰半,所余者仅赡事畜,盖云幸矣。
中国则勤动所获,能自有之,以俭辅勤,积数年便可致中产。故贮蓄之美风,在泰西则学者广为论着以发明,**多设机关以劝厉,而其效卒不大;观中国人人能之,若天性然,亦其制度有以致之也。勤俭贮蓄之人愈多,则中产之家亦愈多,此又因果所必至也。
凡此皆所以说明我国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有绝异之点。而我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其理由皆坐是也。虽然,我国今后不能不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势使然也。既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则必须结合大资本,而小资本必被侵蚀,而经济社会组织不得不缘此而一变,又势使然也。然则欧人工业革命所生之恶结果(即酿出今日社会革命之恶因),我其可以免乎?曰:虽不能尽免,而决不至如彼其甚也。盖欧人今日之社会革命论,全由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而欧人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之不完善,又由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我国现今经济社会之组织,虽未可云完善,然以比诸工业革命前之欧洲,则固优于彼。故今后生产问题,虽有进化,而分配问题,乃可循此进化之轨以行,而两度之革命,殆皆可以不起也。(欧人前此之工业革命,可谓之生产的革命;今后之社会革命,可谓之分配的革命。)请言其理:夫生产之方法变,非大资本则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株式会社)起。
此欧人经过之陈迹,而我国将来亦不能不敩之者也。然欧人之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旧日少数之豪族也;中国今日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现在多数之中产家也。此其发脚点之差异,而将来分配之均不均,其几即兆于是也。夫欧人岂必其乐以股东之权利尽让诸豪族,使如伊里所言,合工人以组织一协立制造会社者,岂其无一人能见及此,而无如其前此社会之组织,本已分贫富二途,贫者虽相结合,然犹以千百之僬侥国人与一二之龙伯国人抗,蔑有济矣。故昔日之富者,因工业革命而愈富;昔日之贫者,因工业革命而愈贫。(虽间有工业革命后由贫而富、由富而贫者,然例外也。)何也?非大资本不能获奇赢,而公司则大资本所在也。有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富。无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贫,公司股份为少数人所占,则多数人遂不得不食贫以终古也。而中国情形则有异于是。试以最近之事实证之。粤汉铁路招股二千万,今已满额,而其最大股东不过占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耳,其数又不过一二人,其占十股以下者乃最大多数(每股五元)。盖公司全股四百万份,而其为股东者百余万人。此我国前此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表征,亦即我国将来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联兆也。诚使得贤才以任之,复有完密之法律以维持之,杜绝当事之舞弊,防制野心家之投机,则公司愈发达,获利愈丰,而股东所受者亦愈多。股东之人数既繁,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其所贮蓄以投于公司;生产方法,大变而进于前;分配方法仍可以率循而无大轶于旧,则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为发达的进化的,而非为革命的矣。夫今者欧美人见贫富阶级悬绝之莫救也,以是有倡为以公司代工人贮蓄,将其庸钱之一部分代贮焉,积以为公司之股本,他日公司获利,彼得分沾,则劳动者兼为资本家,而鸿沟或可以渐图消灭。然在积重难返之欧美,此等补苴,不能为效也。而我国则此事出于天然,不劳人力。盖工业革新以后,而受庸钱之人,半皆兼有资本家之资格,此殆可以今日之现象而测知之者也。(其不能举一切劳动者而悉有某公司之股份,此无待言。然举国无一贫人,则虽行极端社会主义之后,犹将难之。但使不贫者居大多数,即经济社会绝好之现象矣。)此无他故焉,现今之经济社会组织,其于分配一方面,已比较的完善,而远非泰西旧社会所及。由现今社会以孕育将来社会,其危险之程度自不大故也。而无识者妄引欧人经过之恶现象以相怵,是乃谓杞人之忧也。
然又非徒恃现在经济社会组织之差完善而遂以自安也。彼欧人所以致今日之恶现象者,其一固由彼旧社会所孕育,其二亦由彼**误用学理放任而助长之。今我既具此天然之美质,复鉴彼百余年来之流弊,熟察其受病之源,博征其救治之法,采其可用者先事而施焉(其条理详下方),则亦可以消患于未然,而复辙之轨,吾知免矣。所谓不必行社会革命者,此也。
所谓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者何也?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请言其理:夫今日东西列强,所以以支那问题为全世界第一大问题者何也?
凡以国际的经济竞争之所攸决云尔。经济学公例,租与庸厚则其赢薄,租与庸薄则其赢厚。(土地所得曰租,劳力所得曰庸,资本所得曰赢。此严译《原富》所命名也。日人译之曰地代,曰劳银,曰利润。)故拥资本者常以懋迁于租庸两薄之地为利,不得则亦求其一薄者。欧人自工业革命以来,日以过富为患,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其在欧土,土地之租与劳力之庸,皆日涨日甚,资本家不能用之求赢,乃一转而趋于美洲、澳洲诸部新地。此新地者,其土地率未经利用,租可以薄,而人口甚希,庸不能轻,于是招募华工以充之,则租庸两薄而赢倍蓗矣。乃不数十年,而美澳诸地昔为旧陆尾闾者,今其自身且以资本过剩为患。一方面堵截旧陆之资本,使不得侵入新陆以求赢,而旧陆之资本家病;一方面其自身过剩之资本,不能求赢于本土,而新陆之资本家亦病。日本以后起锐进,十年之间,资本八九倍于其前,国中租庸,日涨月腾。而日本之资本家亦病,于是相与旁皇却顾,临睨全球。现今租庸两薄之地,无如中国,故挟资本以求赢,其最良之市场亦莫如中国。世界各国,咸以支那问题为唯一之大问题者,皆此之由。我国民于斯时也,苟能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机器),利用我固有之薄租薄庸以求赢,则国富可以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而不然者,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而东西各国,为经济公例所驱迫,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柙,其将何以御之?夫空言之不能敌实事也久矣,两年以来,利权回收之论,洋溢于国中,争路争矿,言多于鲫,然曾未见一路之能自筑,一矿之能自开。而日人南满洲铁道会社,已以百兆之雄资,伏东省而阘其脑,而各处枝路,尚往往假资于外人,而各国制造品之滔滔汩汩以输入,尽夺吾民之旧业者,又庸耳俗目所未尝察也。夫自生产方法革新以后,惟资本家为能食文明之利,而非资本家则反蒙文明之害,此当世侈谈民生主义者所能知也。曾亦思自今以往,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生之一日。彼欧美今日之劳动者,其欲见天日,犹如此其艰也,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其时,举国中谁复为贫,谁复为富,惟有于中国经济界分两大阶级焉:一曰食文明之利者,其人为外国人;一曰蒙文明之害者,其人为中国人而已。于彼时也,则真不可不合全国以倡社会革命矣。虽然,晚矣,无及矣,此非吾故为危言以悚听也!夫宁不见今日全国经济界稍带活气者,惟有洋场,而洋场之中国人,则皆馂外商之余也。
月晕知风,础润知雨,而况乎风雨之已来袭者耶!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当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虽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今乃无故自惊,睡魇梦呓,倡此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之社会革命论,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寝假而国民信从其教,日煽惑劳动者以要求减少时间,要求增加庸率,不则同盟罢工以挟之;资本家蒙此损失,不复能与他国之同业竞,而因以倒毙;他之资本家,益复惩羹吹韲,裹足不前,坐听外国资本势力,骎骎然淹没我全国之市场,欲抵抗已失其时,而无复扎寨之余地;全国人民,乃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箠之下以糊其口。则今之持社会革命论者,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矣。
此非吾故苛其词,实则居今日而倡此不适于国家生存之社会革命论,其结果必至如是也。要之,吾对于经济问题之意见,可以简单数语宣示之,曰: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何则?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由此言之,则虽目前以解决生产问题故,致使全国富量落于少数人之手,贻分配问题之隐祸于将来,而急则治标,犹将舍彼而趋此,而况乎其可毋虑是也。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夫欧美人之倡社会革命,乃应于时势不得不然,是姊丧尚右之类也。今吾国情形与彼立于正反对之地位,闻其一二学说,乃吠影吠声以随逐之,虽崇拜欧风,亦何必至于此极耶!夫无丧而学人尚右,不过为笑,固非害于实事;若病异症而妄尝人药,则自厌其寿耳。今之倡社会革命论者,盖此类也,所谓不可行社会革命者,此也。
所谓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者何也?欲为社会革命,非体段圆满,则不能收其功;而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后,犹未必能行之,而现在之中国更无论也。今排满家之言社会革命者,以土地国有为唯一之楬橥。不知土地国有者,社会革命中之一条件,而非其全体也。各国社会主义者流,屡提出土地国有之议案,不过以此为进行之着手,而非谓舍此无余事也。如今排满家所倡社会革命者之言,谓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者,因为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一若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其详别于下方驳之。)近世最圆满之社会革命论,其最大宗旨不外举生产机关而归诸国有。土地之所以必须为国有者,以其为重要生产机关之一也。然土地之外,尚有其重要之生产机关焉,即资本是也。而推原欧美现社会分配不均之根由,两者相衡,则资本又为其主动。盖自生产方法一变以后,无资本者万不能与有资本者竞,小资本者万不能与大资本者竞,此资本直接之势力,无待言矣。若语其间接之势力,则地价、地租之所以腾涨者何自乎?亦都会发达之结果而已。都会之所以发达者何自乎?亦资本膨胀之结果而已。彼欧洲当工业革命以前,土地为少数人所占有者已久,然社会问题不发生于彼时面发生于今日者,土地之利用不广,虽拥之犹石田也。及资本之所殖益进,则土地之价值随而益腾,地主所以能占势力于生产界者,食资本之赐也。(如某氏演说称:“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须知伦敦城何以扩张,由资本膨胀故;伦敦地租何以腾涨,由资本膨胀故。若无工业革命后之资本膨胀,则今日之威斯敏士打,亦无从有敌国之富也。其他同类之现象,皆可以此说明之。)又况彼资本家常能以贱价买收未发达之土地,而自以资本之力发达之以两收其利,是又以资本之力支配土地也。(美国人占土比儿于二十年前,买收汶天拿省、华盛顿省诸土地,而自筑大北铁路以贯之。彼时此等土地,皆印度红夷出没之所,殆不值一钱;今则其最闹之市,地价骎骎追纽约、芝加高矣。近太西资本家,率无不用此术。)要之欲解决社会问题者,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且土地问题,虽谓为资本问题之附属焉可也。若工场,若道具(机器),其性质亦与土地近,皆资本之附属也。质而言之,则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若其一部分为国有,而他之大部分仍为私有,则社会革命之目的终不能达也。然则圆满之社会革命论,其新社会之经济组织何如?以简单之语说明之,亦曰: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为竞也。夫同为劳动者也,何以于现在则苦之,于革命后则甘之?
诚以如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彼劳动所得之结果,地主攫其若干焉,资本家攫其若干焉,而劳动者所得,乃不及什之一。若革命以后,劳动之结果,虽割其一部分以与国家,而所自得之一部分,其分量必有以逾于今日。且国家所割取我之一部分,亦还为社会用,实则还为我用而已。如此则分配极均,而世界将低于大同。此社会革命论之真精神,而吾昔所谓认此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者(见本年本报第四号),良以此也。
而试问今日之中国,能行此焉否也?此在欧美之难此主义者,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其他此类之问题尚夥,不缕述。凡此诸问题,皆欧美学者所未尽解决,而即此主义难实行之一原因也。今中国且勿语此,惟有一最浅易最简单之问题,曰: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
就令如彼报所言,我国人民程度已十分发达,而此等**,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以持久而无弊乎?此问题,绝无待高尚之学理以为证,虽五尺之童能辨之。论者如必谓中国今日能建设此等**也,则强词夺理,吾安从复与之言。若知其不能,则社会革命论,直自今取消焉可也。夫论者固明知社会革命之不能实行也,于是卤莽灭裂,盗取其主义之一节以为旗帜,冀以欺天下之无识者。庸讵知凡一学说之立,必有其一贯之精神,盗取一节,未或能于其精神有当也。彼排满家之社会革命论,自孙文倡也,某报第十号,载有孙文演说,殆可为其论据之中心,今得痛驳之以为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之左证。
(1906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