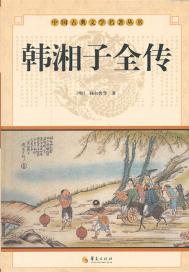同一书也,考据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考据之材料;词章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词章之材料;好作灯谜酒令之人读之,所触者无一非灯谜酒令之材料;经世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经世之材料。同一社会也(即人群),商贾家入之,所遇者无一非锱铢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无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达者入之,所遇者无一非诌上淩下、衣冠优孟之人;怀不平者入之,所遇者无一非陇畔辍耕、东门倚啸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谓世界之大,已尽于是,此外千形万态,非所见也,非所闻也。昔有白昼攫金于齐市者,吏捕而诘之曰:“众目共视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时只见有金,不见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难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佣一蠢仆执爨役者,使购求食物于市,归而曰:“市中无食物。”主人曰:“嘻,鱼也,豕肉也,芥也,姜也,何一不可食者?”于是仆适市,购辄得之。既而亘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鱼也,豕肉也,芥也,姜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仆曰:“市中除鱼与豕肉与芥与姜之外,无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虫,必待显微镜然后能睹者,而蠢仆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观世人所谓智者,其所见,与彼之攫金人与此之蠢仆,相去几何矣?李白、杜甫满地,而衣袚襫、携锄犁者,必不知之;计然、范蠡满地,而摩禹行、效舜趋者,必不知之;陈涉、吴广满地,而飨五鼎、鸣八驺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则直谓世界中无有此等人也,虽日日以此等人环集于其旁,而彼之视为无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与此之蠢仆,何其蔽欤?
人谁不见苹果之坠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谁不见沸水之腾气,而因以悟汽机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谁不见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觅得新大陆者,惟有一哥仑布;人谁不见男女之恋爱,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动机者,惟有一瑟士丕亚。无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窝儿哲窝士于此中见造化之微妙焉;海滩之僵石,渔者所淘余,潮雨所狼藉,而达尔文于此中悟进化之大理焉。故学莫要于善观。
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
(1900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