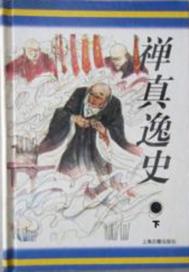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插奇标卖身作父
词云:千年劫,偏自我生逢。国破家亡身又辱,不教一事不成空。
极狠是天公!差一念,悔杀也无功。青冢魂多难觅取,黄泉路窄易相逢。难禁面皮红!
右调《望江南》此词乃闯贼南来之际,有人在大路之旁拾得漳烟少许,此词录于片纸,即闯贼包烟之物也。拾得之人不解文义,仅谓残篇断幅而已。再传而至文人之手,始知为才妇被掳,自悔失身,欲求一死,又虑有腆面目,难见地下之人,进退两难,存亡交阻,故有此悲愤流连之作。玩第二句,有"国破家亡"一语,不仅是庶民之妻,公卿士大夫之妾,所谓"黄泉路窄易相逢"者,定是个有家有国的人主。彼时京师未破,料不是先帝所幸之人,非藩王之妃即宗室之妇也。贵胄若此,其他可知。能诗善赋,通文达理者若此,其他又可知。所以论人于丧乱之世,要与寻常的论法不同,略其迹而原其心,苟有寸长可取,留心世教者,就不忍一概置之。古语云:"立法不可不严,行法不可不恕。"古人既有诛心之法,今人就该有原心之条。迹似忠良而心同奸佞,既蒙贬斥于《春秋》;身居异地而心系所天,宜见褒扬于末世。
诚以古人所重,在此不在彼也。此妇既遭污辱,宜乎背义忘恩,置既死之人于不问矣;犹能慷慨悲歌,形于笔墨,亦当在可原可赦之条,不得与寻常失节之妇同日而语也。
此段议论,与后面所说之事不甚相关,为什么叙作引子?
只因前后二楼都是说被掳之事,要使观者稍抑其心,勿施责备之论耳。从来鼎革之世,有一番乱离,就有一番会合。乱离是桩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造物之巧于作缘,往往如此。
却说宋朝末年,湖广郧阳府竹山县有个乡间财主,姓尹名厚。他家屡代务农,力崇俭朴,家资满万,都是气力上挣出来,口舌上省下来的。娶妻庞氏,亦系庄家之女,缟衣布裙,躬亲杵臼。这一对勤俭夫妻,虽然不务奢华,不喜炫耀,究竟他过的日子比别家不同,到底是丰衣足食。莫说别样,就是所住的房产,也另是一种气概。《四书》上有两句云:"富润屋,德润身。"这个"润"字,从来读书之人都不得其解。不必定是起楼造屋,使他焕然一新,方才叫做润泽;就是荒园一所,茅屋几间,但使富人住了,就有一种旺气。此乃时运使然,有莫之为而为者。
若说润屋的"润"字是兴工动作粉饰出来的,则是润身的"润"字也要改头换面,另造一副形骇,方才叫做润身;把正心诚意的工夫反认做穿眼凿眉的学问了,如何使得!尹厚做了一世财主,不曾兴工动作。只因婚娶以后再不宜男,知道是阳宅不利,就于祖屋之外另起一座小楼。同乡之人都当面笑他,道:"盈千满万的财主,不起大门大面,蓄了几年的精力,只造得小楼三间,该替你上个徽号,叫做'尹小楼'才是。"尹厚闻之甚喜,就拿来做了表德。
自从起楼之后,夫妻两口搬进去做了卧房,就忽然怀起孕来。等到十月满足,恰好生出个孩子,取名叫做楼生。相貌魁然,易长易大,只可惜肾囊里面止得一个肾子。小楼闻得人说,独卵的男人不会生育,将来未必有孙,且保了一代再处。不想到三四岁上,随着几个孩童出去嬉耍,晚上回来,不见了一个,恰好是这位财主公郎。彼时正在虎灾,人口猪羊时常有失脱,寻了几日不见,知道落于虎口,夫妻两个几不欲生。起先只愁第二代,谁想命轻福薄,一代也不能保全。劝他的道:"少年妇人只愁不破腹,生过一胎就是熟胎了,哪怕不会再生?"小楼夫妇道;"也说得是。"从此以后,就愈敦夫妇之好,终日养锐蓄精,只以造人为事。谁想从三十岁造起,造到五十之外,行了三百余次的月经,倒下了三千多次的人种,粒粒都下在空处,不曾有半点收成。
小楼又是惜福的人,但有人劝他娶妾,就高声念起佛来,说:"这句话头,只消口讲一讲就要折了冥福,何况认真去做,有个不伤阴德之理!"所以到了半百之年,依旧是夫妻两口,并无后代。亲戚朋友个个劝他立嗣。尹小楼道:"立后承先,不是一桩小事,全要付得其人。我看眼睛面前没有这个有福的孩子,况且平空白地把万金的产业送他,也要在平日之间有些情意到我,我心上爱他不过,只当酬恩报德一般,明日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懊悔。若还不论有情没情,可托不可托,见了孩子就想立嗣,在生的时节,他要得我家产,自然假意奉承,亲爷亲娘叫不住口;一到死后,我自我,他自他,哪有什么关涉?
还有继父未亡,嗣子已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倒要胁制爷娘,欺他没儿没女,又摇动我不得,要逼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家主公的,这也是立嗣之家常有的事。我这份家私,是血汗上挣来的,不肯白白送与人。要等个有情有义的儿子,未曾立嗣之先,倒要受他些恩惠,使我心安意肯,然后把恩惠加他。别个将本求利,我要人将利来换本,做桩不折便宜的事与列位看一看,何如?"众人不解其故,都说他是迂谈。
一日,与庞氏商议道:"同乡之人知道我家私富厚,哪一个不想立嗣?见我发了这段议论,少不得有垂钩下饵的人把假情假意来骗我。不如离了故乡,走去周游列国,要在萍水相逢之际,试人的情意出来。万一遇着个有福之人,肯把真心向我,我就领他回来,立为后嗣,何等不好!"庞氏道:"极讲得是。"就收拾了行李,打发丈夫起身。
小楼出门之后,另是一种打扮:换了破衣旧帽,穿着苎袜芒鞋,使人看了,竟像个卑田院的老子、养济院的后生,只少得一根拐捧,也是将来必有的家私。这也罢了,又在帽檐之上插着一根草标,装做个卖身的模样。人问他道:"你有了这一把年纪,也是大半截下土的人了,还有什么用处,思想要卖身?
看你这个光景,又不像以下之人,他买你回去,还是为奴作仆的好,还是为师作傅的好?"小楼道:"我的年纪果然老了,原没有一毫用处,又是做大惯了的人,为奴做仆又不合,为师作傅又无能。要寻一位没爷没娘的财主,卖与他做个继父,拚得费些心力,替他管管家私,图一个养老送终,这才是我的心事。"问的人听了,都说是油嘴话,没有一个理他。他见口里说来没人肯信,就买一张绵纸,褙做三四层,写上几行大字,做个卖身为父的招牌。其字云:年老无儿,自卖与人作父,只取身价十两。愿者即日成交,并无后悔。
每到一处,就捏在手中,在街上走来走去。有时走得脚酸,就盘膝坐下,把招牌挂在胸前,与和尚募缘的相似。众人见了,笑个不住,骂个不了,都说是丧心病狂的人。
小楼随人笑骂,再不改常,终日穿州撞府,涉水登山,定要寻着个买者才住。要问他寻到几时方才遇着受主,只在下回开卷就见。
第二回 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
尹小楼捏了那张招帖,走过无数地方,不知笑歪了几干几万张嘴。忽然遇着个奇人,竟在众人笑骂之时成了这宗交易。
俗语四句道得好:弯刀撞着瓢切菜,夜壶合着油瓶盖。
世间弃物不嫌多,酸酒也堪充醋卖。
一日,走到松江府华亭县,正在街头打坐,就有许多无知恶少走来愚弄他,不是说"孤老院中少了个叫化头目,要买你去顶补",就是说"乌龟行里缺了个乐户头儿,要聘你去当官"。
也有在头上敲一下的,也有在腿上踢一脚的,弄得小楼当真不是,当假不是。
正在难处的时节,只见人丛里面挤出一个后生来,面白身长,是好一个相貌,止住众人,叫他不要啰唣,说:"鳏寡孤独之辈,乃穷民之无靠者,皇帝也要怜悯他,官府也要周恤他。
我辈后生,只该崇以礼貌,岂有擅加侮谩之理?"众人道:"这等说起来,你是个怜孤恤寡的人了,何不兑出十两银子买他回去做爷?"那后生道:"也不是什么奇事,看他这个相貌,不是没有结果的人,只怕他卖身之后,又有亲人来认了去,不肯随找终身。若肯随我终身,我原是没爷没娘的人,就拚了十两银子买他做个养父,也使百年以后传一个怜孤恤寡之名,有什么不好!"小楼道:"我止得一身,并无亲属,招牌上写得分明,后来并无翻悔。你如果有此心,快兑银子出来,我就跟你回去。"众人道:"既然卖了身,就是他供养你了,还要银子何用?"小楼道:"不瞒列位讲,我这张痨嘴原是馋不过的,茶饭酒肉之外,还要吃些野食,只为一生好嚼,所以做不起人家。难道一进了门,就好问他取长取短?也要吃上一两个月,等到情意洽浃了,然后去需索他,才是为父的道理。"众人听了,都替这买主害怕,料他闻得此言,必定中止。谁想这个买主不但不怕,倒连声赞美,说他:"未曾做爷,先是这般体谅,将来爱子之心一定是无所不至的了。"就请到酒店之中,摆了一桌厦饭,暖上一壶好酒,与他一面说话,一面成交。
起先那些恶少都随进店中,也以吃酒为名,看他是真是假。
只见卖主上坐,买主旁坐,斟酒之时毕恭毕敬,俨然是个为子之容;吃完之后,就向兜肚里面摸出几包银子,并拢来一称,共有十六两,就双手递过去道:"除身价之外,还多六两,就烦爹爹代收。从今以后,银包都是你管,孩儿并不稽查。要吃只管吃,要用只管用,只要孩儿趁得来,就吃到一百岁也无怨。"小楼居然受之,并无惭色,就除下那面招牌递与他,道:"这件东西就当了我的卖契,你藏在那边,做个凭据就是了。"后生接过招牌,深深作了一揖,方才藏人袖中。小楼竟以家长自居,就打开银包,称些银子,替他会了酒钞,一齐出门去了。
旁边那些恶少看得目定口呆,都说:"这一对奇人,不是神仙,就是鬼魅,决没有好好两个人做出这般怪事之理!"却说小楼的身子虽然卖了,还不知这个受主姓张姓李,家事如何,有媳妇没有媳妇,只等跟到家中察其动静。只见他领到一处,走进大门,就扯一把交椅摆在堂前,请小楼坐下,自己志志诚诚拜了四拜。拜完之后,先问小楼的姓名,原籍何处。
小楼恐怕露出形藏,不好试人的情意,就捏个假名假姓糊涂答应他,连所居之地也不肯直说,只在邻州外县随口说一个地方。
说出之后,随即问他姓什名谁,可曾婚娶。那后生道:"孩儿姓姚名继,乃湖广汉阳府汉口镇人,幼年丧亲,并无依倚。十六岁上跟了个同乡之人叫做曹玉宇,到松江来贩布,每年得他几两工钱,又当糊口,又当学本事。做到后来人头熟了,又积得几两本钱,就离了主人,自己做些生意,依旧不离本行。
这姓人家就是布行经纪,每年来收布,都寓在他家。今年二十二岁,还不曾娶有媳妇。照爹爹说起来,虽不同府同县,却同是湖广一省。古语道得好:'亲不亲,故乡人。'今日相逢,也是前生的缘法。孩儿看见同辈之人个个都有父母,偏我没福,只觉得孤苦伶仃,要投在人家做儿子,又怕人不相谅,说我贪谋他的家产,是个好吃懒做的人。殊不知有我这个身子,哪一处趁不得钱来?七八岁上失了父母,也还活到如今不曾饿死,岂肯借出继为名贪图别个的财利?如今遇着爹爹,恰好是没家没产的人,这句话头料想没人说得,所以一见倾心,成了这桩好事。孩儿自幼丧亲,不曾有人教诲,全望爹爹耳提面命,教导孩儿做个好人,也不在半路相逢,结了这场大义。如今既做父子,就要改姓更名,没有父子二人各为一姓之理,求把爹爹的尊姓赐与孩儿,再取一个名字,以后才好称呼。"小楼听到此处,知道是个成家之子,心上十分得意。还怕他有始无终,过到后来渐有厌倦之意,还要留心试验他。因以前所说的不是真话,没有自己捏造姓名又替他捏造之理,只得权词以应,说:"我出银子买你,就该姓我之姓;如今是你出银子买我,如何不从主便,倒叫你改名易姓起来?你既姓姚,我就姓你之姓,叫做'姚小楼'就是了。"姚继虽然得了父亲,也不忍自负其本,就引一句古语做个话头,叫做"恭敬不如从命"。
自此以后,父子二人亲爱不过,随小楼喜吃之物,没有一件不买来供奉他。小楼又故意作娇,好的只说不好,要他买上几次,换上几遭,方才肯吃。姚继随他拿捏,并不厌烦。过上半月有余,小楼还要装起病来,看他怎生服侍,直到万无一失的时候,方才吐露真情。
谁想变出非常,忽然得了乱信,说元兵攻进燕关,势如破竹,不日就抵金陵。又闻得三楚两粤盗贼蜂起,没有一处的人民不遭劫掠。小楼听得此信,魂不附体,这场假病哪里还装得出来?只得把姚继唤到面前,问他:"收布的资本共有几何?
放在人头上的可还取计得起?"姚继道:"本钱共有三百余金,收起之货不及一半,其余都放在庄头。如今有了乱信,哪里还收得起?只好把现在的货物装载还乡,过了这番大乱,到太平之世再来取讨。只是还乡的路费也吃得许多,如今措置不出,却怎么好?"小楼道:"盘费尽有,不消你虑得。只是这样乱世,空身行走还怕遇了乱兵,如何带得货物?不如把收起的布也交与行家,叫他写个收票,等太平之后一总来取。我和你轻身逃难,奔回故乡,才是个万全之策。"姚继道:"爹爹是卖身的人,哪里还有银子?就有,也料想不多。孩儿起先还是孤身,不论有钱没钱,都可以度日。如今有了爹爹,父子两人过活,就是一分人家了,捏了空拳回去,叫把什么营生?难道孩儿熬饿,也叫爹爹熬饿不成?"小楼听到此处,不觉泪下起来,伸出一个手掌,在他肩上拍几拍,道:"我的孝顺儿呵!
不知你前世与我有什么缘法,就发出这片真情?老实对你讲罢,我不是真正穷汉,也不是真个卖身。只因年老无儿,要立个有情有义的后代,所以装成这个圈套,要试人情义出来的。不想天缘凑巧,果然遇着你这个好人。我如今死心塌地把终身之事付托与你了。不是爹爹夸口说,我这份家私也还够你受用。你买我的身价只去得十两,如今还你一本千利,从今以后,你是个万金的财主了。这三百两客本,就丢了不取,也只算得毡上之毫。快些收拾起身,好跟我回去做财主。"姚继听到此处,也不觉泪下起来。当晚就查点货物,交付行家。次日起身,包了一舱大船,溯流而上。
看官们看了,只说父子两个同到家中就完了这桩故事,哪里知道,一天诧异才做动头,半路之中又有悲欢离合,不是一口气说得来的。暂结此回,下文另讲。
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白发 因留慈母得娇妻
尹小楼下船之后,问姚继道:"你既然会趁银子,为什么许大年纪并不娶房妻小,还是孤身一个?此番回去,第一桩急务,就要替你定亲,要迟也迟不去了。"姚继道:"孩儿的亲事原有一头,只是不曾下聘。此女也是汉口人,如今回去,少不得从汉口经过,屈爹爹住在舟中权等一两日,待孩儿走上岸去探个消息了下来。若还嫁了就罢,万一不曾嫁,待孩儿与他父母定下一个婚期,到家之后,就来迎娶。不知爹爹意下如何?"小楼道:"是个什么人家,既有成议在先,无论下聘不下聘,就是你的人了,为什么要探起消息来?"姚继道:"不瞒爹爹说,就是孩儿的旧主人,叫做曹玉宇。他有一个爱女,小孩儿五六岁,生得美貌异常。孩儿向有求婚之意,此女亦有愿嫁之心,只是他父母口中还有些不伶不俐,想是见孩儿本钱短少,将来做不起人家,所以如此。此番上去,说出这段遭际来,他是个势利之人,必然肯许。"小楼道:"既然如此,你就上去看一看。"及至到了汉口,姚继吩咐船家,说自己上岸,叫他略等一等。不想满船客人都一齐哗噪起来,说:"此等时势,各人都有家小,都不知生死存亡,恨不得飞到家中讨个下落,还有工夫等你!"小楼无可奈何,只得在个破布袱中摸出两封银子,约有百金,交与姚继,道:"既然如此,我只得预先回去,你随后赶来。这些银子带在身边,随你做聘金也得,做盘费也得。只是探过消息之后,即便抽身,不可耽迟了日子,使我悬望。"姚继拜别父亲,也要叮咛几句,叫他路上小心,保重身子。不想被满船客人催促上岸,一刻不许停留,姚继只得慌慌张张跳上岸去。
船家见他去后,就拽起风帆,不上半个时辰,行了二三十里。只见船舱之中有人高声喊叫,说:"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吩咐得,却怎么处!"说了这一句,就捶胸顿足起来。你说是哪一个?原来就是尹小楼。起先在姚继面前,把一应真情都已说破,只有自己的真名真姓与实在所住的地方倒不曾谈及;只说与他一齐到家,自然晓得,说也可,不说也可。哪里知道,仓卒之间把他驱逐上岸,第一个要紧关节倒不曾提起,直到分别之后才记上心来。如今欲待转去寻他,料想满船的人不肯耽搁;欲待不去,叫他赶到之日,向何处抓寻?所以千难万难,唯有个抢地呼天、捶胸顿足而已。急了一会,只得想个主意出来:要在一路之上写几个招子,凡他经过之处都贴一贴,等他看见,自然会寻了来。
话分两头。且说姚继上岸之后,竟奔曹玉宇家,只以相探为名,好看他女儿的动静。不想进门一看,时事大非,只有男子之形,不见女人之面。原来乱信一到楚中,就有许多土贼假冒元兵,分头劫掠,凡是女子,不论老幼,都掳入舟中,此女亦在其内,不知生死若何;即使尚存,也不知载往何方去了。
姚继得了此信,甚觉伤心,暗暗地哭了一场,就别过主人,依旧搭了便船,竟奔郧阳而去。
路不一日,到了个码头去处,地名叫做仙桃镇,又叫做鲜鱼口。有无数的乱兵把船泊在此处,开了个极大的人行,在那边出脱妇女。姚继是个有心人,见他所爱的女子掳在乱兵之中,正要访她的下落,得了这个机会,岂肯惧乱而不前?又闻得乱兵要招买主,独独除了这一处不行抢掠。姚继又去得放心,就带了几两银子,竟赴人行来做交易。指望借此为名,立在卖人的去处,把各路抢来的女子都识认一番,遇着心上之人,方才下手。不想那些乱兵又奸巧不过,恐怕露出面孔,人要拣精择肥,把像样的妇人都买了去,留下那些"拣落货"卖与谁人?
所以创立新规,另做一种卖法:把这些妇女当做腌鱼臭鲞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随人提取,不知哪一包是腌鱼,哪一包是臭鲞,各人自撞造化。那些妇人都盛在布袋里面,只论斤两,不论好歉,同是一般价钱。造化高的得了西子王嫱,造化低的轮着东施嫫姆,倒是从古及今第一桩公平交易!姚继见事不谐,欲待抽身转去,不想有一张晓谕贴在路旁,道:"卖人场上,不许闲杂人等往来窥视。如有不买空回者,即以打探虚实论,立行枭斩,决不姑贷!特谕。"姚继见了,不得不害怕起来。知道只有错来,并无错去,身边这几两银子定是要出脱的了:"就去撞一撞造化,或者姻缘凑巧,恰好买着心上的人也未见得;就使不能相遇,另买着一位女子,只要生得齐整,像一个财主婆,就把她充了曹氏带回家中,谁人知道来历。"算计定了,那走到叉口堆中,随手指定一只,说:"这个女子是我要买的。"那些乱兵拿来称准数目,喝定价钱,就架起天平来兑银子。还喜得斤两不多,价钱也容易出手。姚继兑足之后,等不得抬到舟中,就在卖主面前要见个明白。及至解开袋结,还不曾张口,就有一阵雪白的光彩透出在叉口之外。
姚继思量道:"面白如此,则其少艾可知,这几两银子被我用着了。"连忙揭开叉口,把那妇人仔细一看,就不觉高兴大扫,连声叫起屈来。原来那雪白的光彩不是面容,倒是头发!
此女霜鬓皤然,面上鄃纹森起,是个五十向外六十向内的老妇。
乱兵见他叫屈,就高声呵叱起来,说:"你自家时运不济,拣着老的,就叫屈也无用,还不领了快走!"说过这一句,又拔出刀来,赶他上路。
姚继无可奈何,只得抱出妇人离了布袋,领她同走到舟中,又把浑身上下仔细一看,只见她年纪虽老,相貌尽有可观,不是个低微下贱之辈,不觉把一团**变作满肚的慈心,不但不懊侮,倒有些得意起来,说:"我前日去十两银子买着一个父亲,得了许多好处;今日又去几两银子买着这件宝货,焉知不在此人身上又有些好处出来?况且既已恤孤,自当怜寡,我们这两男一女都是无告的穷民,索性把鳏寡孤独之人合来聚在一处,有什么不好?况且我此番去见父亲,正没有一件出手货,何不就将此妇当了人事送他,充做一房老妾,也未尝不可。虽有母亲在堂,料想高年之人无醋可吃,再添几个也无妨。"立定主意,就对那老妇道:"我此番买人,原要买个妻子,不想得了你来。看你这样年纪,尽可以生得我出,我原是个无母之人,如今的意思,要把你认做母亲,不知你肯不肯?"老妇听了这句话,就吃惊打怪起来,连忙回复道:"我见官人这样少年,买着我这个怪物,又老又丑,还只愁你懊悔不过,要推我下江,正在这边害怕。怎么没缘没故说起这样话来?岂不把人折死!"姚继见她心肯,倒头就拜。拜了起来,随即安排饭食与她充饥。
又怕身上寒冷,把自己的衣服脱与她穿着。
那妇人感激不过,竟号啕痛哭起来。哭了一会,又对他道:"我受你如此大恩,虽然必有后报,只是眼前等不得。如今现有一桩好事,劝你去做来。我们同伴之中有许多少年女子,都要变卖。内中更有一个,可称绝世佳人,德性既好,又是旧家,正好与你作对。那些乱兵要把丑的老的都卖尽了,方才卖到这些人。今日脚货已完,明日就轮到此辈了,你快快办些银子,去买了来。"姚继道:"如此极好。只是一件,那最好的一个混在众人之中,又有布袋盛了,我如何认得出?"老妇道:"不妨,我有个法子教你。她袖子里面藏着一件东西,约有一尺长、半寸阔,不知是件什么器皿,时刻藏在身边,不肯丢弃。你走到的时节,隔着叉口把各人的袖子都捏一捏,但有这件东西的即是此人,你只管买就是了。"姚继听了这句话,甚是动心,当夜醒到天明,不曾合眼。第二日起来,带了银包,又往人行去贸易。依着老妇的话,果然去摸袖子,又果然摸着一个有件硬物横在袖中,就指定叉口,说定价钱,交易了这宗奇货。买成之后,恐怕当面开出来有人要抢夺,竟把她连人连袋抱到舟中,又叫驾撑开了船,直放到没人之处,方才解看。
你道此女是谁?原来不姓张、不姓李,恰好姓曹,就是他旧日东君之女,向来心上之人。两下原有私情,要约为夫妇,袖中的硬物乃玉尺一根,是姚继一向量布之物,送与她做表记的;虽然遇了大难,尚且一刻不离,那段生死不忘的情份,就不问可知了。这一对情人忽然会于此地,你说他喜也不喜!乐也不乐!此女与老妇原是同难之人,如今又做了婆媳,分外觉得有情,就是嫡亲的儿妇,也不过如此。
姚继恤孤的利钱虽有了指望,还不曾到手,反是怜寡的利息随放随收,不曾迟了一日。可见做好事的再不折本。奉劝世人,虽不可以姚继为法,个个买人做爷娘,亦不可以姚继为戒,置鳏寡孤独之人于不问也。
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
却说尹小楼自从离了姚继,终日担忧,凡是经过之处,都贴一张招子,说:"我旧日所言并非实话,你若寻来,只到某处地方来问某人就是。"贴便贴了,当不得姚继心上并没有半点狐疑,见了招子,哪有眼睛去看?竟往所说之处认真去寻访。
那地方上面都说:"此处并无此人,你想是被人骗了。"姚继说真不是,说假不是,弄得进退无门。
老妇见他没有投奔,就说:"我的住处离此不远,家中现有老夫,并无子息。你若不弃,把我送到家中,一同居住就是了。"姚继寻人不着,无可奈何,只得依她送去。只见到了一处地方,早有个至亲之人在路边等候,望见来船,就高声问道:"那是姚继儿子的船么?"姚继听见,吃了一惊,说:"叫唤之人分明是父亲的口气,为什么彼处寻不着,倒来在这边?"老妇听了,也吃一惊,说:"那叫唤之人分明是我丈夫的口气,为什么丢我不唤,倒唤起他来?"及至把船拢了岸,此老跳入舟中,与老妇一见,就抱头痛哭起来。
原来老妇不是别人,就是尹小楼的妻子,因丈夫去后也为乱兵所掠。那两队乱兵原是一个头目所管,一队从上面掳下去,一队从下面掳上来,原约在彼处取齐,把妇女都卖做银子,等元兵一到就去投降,好拿来做使费的。恰好这一老一幼并在一舱,预先打了照面。若还先卖**、后卖老妇,尹小楼这一对夫妻就不能够完聚了;就是先卖老妇、后卖**,姚继买了别个老妇,这个老妇又卖与别个后生,姚继这一对夫妻也不能够完聚了。谁想造物之巧,百倍于人,竟像有心串合起来等人好做戏文小说的一般,把两对夫妻合了又分,分了又合,不知费他多少心思!这桩事情也可谓奇到极处、巧到至处了,谁想还有极奇之情、极巧之事,做便做出来了,还不曾觉察得尽。
小楼夫妇把这一儿一媳领到中堂,行了家庭之礼,就吩咐他道:"那几间小楼是极有利市的所在,当初造完之日,我们搬进去做房,就生出一个儿子,可惜落于虎口,若在这边,也与你们一般大了。如今把这间卧楼让与你们居住,少不得也似前人,进去之后就会生儿育女。"说了这几句,就把他夫妻二口领到小楼之上,叫他自去打扫。
姚继一上小楼,把门窗户扇与床幔椅桌之类仔细一看,就大惊小怪起来,对着小楼夫妇道:"这几间卧楼分明是我做孩子的住处,我在睡梦之中时常看见的,为什么我家倒没有,却来在这边?"小楼夫妇道:"怎见得如此?"姚继道:"孩儿自幼至今,但凡睡了去,就梦见一个所在:门窗也是这样门窗,户扇也是这样户扇,床幔椅桌也是这样床幔椅桌,件件不差。
又有一夜,竟在梦中说起梦来,道:'我一生做梦,再不到别处去,只在这边,是什么缘故'就有一人对我道:'这是你生身的去处,那只箱子里面是你做孩子时节玩耍的东西,你若不信,去取出来看。'孩儿把箱子一开,看见许多戏具,无非是泥人土马棒槌旗帜之属。孩儿看了,竟像是故人旧物一般。及至醒转来,把所居的楼屋与梦中一对,又绝不相同,所以甚是疑惑。方才走进楼来,看见这些光景,俨然是梦中的境界,难道青天白日又在这边做梦不成?"小楼夫妇听了,惊诧不已,又对他道:"我这床帐之后果然有一只箱子,都是亡儿的戏物。
我因儿子没了,不忍见他,并做一箱,丢在床后,与你所说的话又一毫不差,怎么有这等奇事?终不然我的儿子不曾被虎驮去,或者遇了拐子拐去卖与人家,今日是皇天后土怜我夫妻积德,特地并在一处,使我骨肉团圆不成?"姚继道:"我生长二十余年,并不曾听见人说道我另有爷娘,不是姚家所出。"他妻子曹氏听见这句说话,就大笑起来道:"这等说,你还在睡里梦里!我们那一方,谁人不知你的来历?只不好当面说你。你求亲的时节,我的父母见你为人学好,原要招做女婿,只因外面的人道你不是姚家骨血,乃别处贩来的野种,所以不肯许亲。你这等聪明,难道自己的出处还不知道?"姚继听到此处,就不觉口呆目定,半晌不言。小楼想了一会,就大悟转来,道:"你们不要猜疑,我有个试验之法。"就把姚继扯过一边,叫他解开裤子,把肾囊一捏,就叫起来,道:"我的亲儿,如今试出来了!别样的事或者是偶尔相同,这肾囊里面只有一个卵子,岂是同得来的?不消说得,是天赐奇缘,使我骨肉团圆的了!可见陌路相逢,肯把异姓之人呼为父母,又有许多真情实意,都是天性使然,非无因而至也。"说了这几句,父子婆媳四人一齐跪倒,拜谢天地,磕了无数的头。
一面宰猪杀羊,酬神了愿,兼请同乡之人,使他知道这番情节。又怕众人不信,叫儿子当场脱裤,请验那枚独卵。他儿子就以此得名,人都称为"尹独肾"。
后来父子相继积德,这个独卵之人一般也会生儿子,倒传出许多后代,又都是独肾之人。世世有田有地,直富到明朝弘治年间才止。又替他起个族号,都唤做"独肾尹家"有诗为证:综纹入口作公卿,独肾生儿理愈明。
相好不如心地好,麻衣术法总难凭。
〔评〕觉世稗官所作,事事在情理之中,独有买人为父一节,颇觉怪诞。观者至此,都谓"捉出破绽来",将施责备之论矣。
及至看到"原属父子,天性使然"一语,又觉得甚是平常,并不曾跳出情理之外。可见人作好文字与做好人、行好事一般,常有初使人惊,次招人怪,及至到群疑毕集怨?
将兴之际,忽然见出他好处来,始知做好人行好事者原有一片苦心,令人称颂不已。悟此即知作文之法,悟此即知读书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