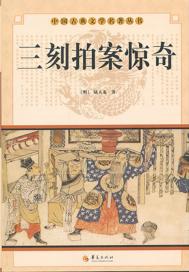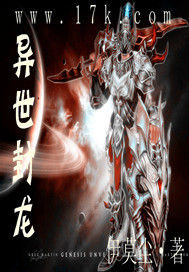残日照山坞,长松覆如宇。
啾啾宿鸟喧,欣然得所主。
嗟我独非人,入室痛无父。
跋涉宁辞远,栉沐甘劳苦。
朝寻鲁国山,暮宿齐郊雨。
肯令白发亲,飘泊远乡土。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之恩,昊天罔极。若使父母飘泊他乡,我却安佚故土,心上安否?故此宋时有个朱寿昌,弃官寻亲。我朝金华王待制祎,出使云南,被元镇守梁王杀害,其子间关万里,觅骸骨而还。又还有个安吉严孝子,其父问军辽阳,他是父去后生的。到十六岁,孤身往辽阳寻问。但他父子从不曾见面,如何寻得?适有一个乞丐问他求乞,衣衫都无,把席遮体。有那轻薄的道:“这莫不是你父亲?”孝子一看,形容与他有些相似,问他籍贯姓名,正是他父亲。他便跪拜号哭,为他沐浴更衣,替父充役。把身畔银子故意将来借与同伴,像个不思量回乡意思,使人不疑。忽然他驼了爷回家,夫妇、子母重聚。这虽不认得父亲,还也晓得父亲在何处,如今说一个更奇特的,从不曾认得父亲面庞,又不知他在何处,坚心寻访,终久感格神明,爷子团圆的。
这事出在山东青州府,本府有个安丘县,县里有个弃金坡,乃汉末名士管宁与华歆在此锄地得金,华歆将来掷去,故此得名。坡下有个住民,姓王名喜,是个村农,做人极守本分。有荒地十余亩,破屋两三椽,恰是:几行梨枣独成村,禾黍阴阴绿映门。
墙垒黄沙随雨落,椽疏白荻逐风翻。
歌余荷耒时将晚,声断停梭日已昏。
征缮不烦人不扰,瓦盆沽酒乐儿孙。他有一妻霍氏,有一个儿子叫做王原,夫耕妇馌,尽可安居乐业。但百姓有田可耕,有屋可住,胡乱过得日子,为何又有逃亡流徙的?却不知有几件弊病:第一是遇不好时年,该雨不雨,该晴不晴;或者风雹又坏了禾稼,蝗虫吃了苗麦。今年田地不好,明年又没收成,百姓不得不避荒就熟。第二是遇不好的官府,坐在堂上,只晓得罚谷罚纸,火耗兑头,县中水旱也不晓得踏勘申报。就勘报时,也只凭书吏胡乱应个故事。到上司议赈济,也只当赈济官吏,何曾得到平人?百姓不得不避贪就廉。第三是不好的里递,当十年造册时,花分诡寄,本是富户,怕产多役重,一户分作两三户,把产业派向乡官举监名下。那小户反没处挪移,他的徭役反重。小民怕见官府,毕竟要托他完纳,银加三、米加四,还要津贴使费,官迟他不迟,官饶他不饶。似此咀啮小民,百姓也不能存立。
这王喜却遇着一个里蠹,姓崔名科,他是个破落户,做了个里胥,他把一家子都要靠着众人养活。王喜此时是个甲首,该有丁银;有田亩,该有税粮。他却官府不曾征比,便去催他完纳。就纳完了,他又说今年加派河工钱粮哩,上司加派兵饷哩,还要添多少。穷民无钱在家,不免延捱他两个日子,一发好不时时去骚扰。一到,要他酒饭吃,肉也得买一斤,烧刀子也要打两瓶请他;若在别家吃了来时,鸡也拿他只去准折,略一违拗,便频差拨将来。其时正是国初典作之时,筑城凿池,累累兴师北伐,开河运米,正是差役极多、极难时节。王喜只因少留了他一遭酒,被他拨得一个不停脚。并不曾有工夫轮到耕种上,麦子竟不曾收得,到夏恰值洪武十八年,是亢旱时节,连茹茹都焦枯了,不结得米。便有几株梨枣,也生得极少。家中甚难过活。
村中有一个张老三,对王喜道:“王老大,如今官府差官赈济,少也好骗他三五钱银子,你可请一请崔科,叫他开去。”王喜为差拨上,心上原也不曾喜欢他,只是思量要得赈济,没奈何去伺候他。他道:“今日某人请我吃饭,某人请我吃酒,明日也是有人下定的,没工夫。”王喜回来对妻子道:“请他他又道没工夫,怎处?”霍氏道:“这明白是要你拿钱去。”王喜道:“要酒吃还好去赊两壶,家里宰只鸡,弄块豆腐,要钱那里去讨?”霍氏道:“咱身上还有件青绵布衫,胡乱拿去当百来文钱与他罢。”王喜拿了去半日,荒时荒年,自不典罢了,还有钱当人家的?走了几处,当得五十钱。那王原只得两岁儿,看了又哭,要买馍馍吃。王喜也顾他不得,连忙拿了去见崔科。他家里道:“南村抄排门册去了。”到晚又去,道:“五里铺赵家请去吃酒去了。”一连走了七八个空。往回,才得见崔科,递出钱去,道:“要请你老人家家去吃杯酒,你老人家没工夫。如今折五十个钱,你老人家买斤肉吃罢。”那崔科笑了笑道:“王大,我若与你造入赈济册,就是次贫,也该领三钱银子,加三也该九分。这几个钱,叫老子买了肉没酒,买了酒没肉,当得甚来?好歹再拿五十钱来,我与你开做次贫罢。”王喜回去闷闷不快,霍氏问时,他道:“攮刀的嫌少哩!道次贫的有三钱,加三算还要我五十文。”霍氏道:“适才拿钱来,原儿要个买波波不与他,还嫌少?哥,罢!再拿我这条裙去,押五十个与他,若得三钱银子,赎了当,也还有一二钱多,也有几日过。”王喜只得又去典钱,典了送崔科,却好崔科不在。嫂子道:“他在曹大户家造册,你有甚话,回时我替你讲。”王喜便拿出五十个钱道:“要他开次贫。”嫂子道:“知道了,我叫他开。”王喜道:“奶奶不要忘了。”他嫂子道:“我不忘记,分付他料不敢不开。”王喜欢天喜地自回。那嫂子果然钱虽不曾与崔科,这话是对他说的。怎奈崔科噇了一包子酒,应了却不曾记得。
到赈济时,一个典史抬到乡间,出了个晓谕,道:“极贫银五钱、谷一石;次贫银二钱、谷五斗。照册序次给散。”只见乡村中扶老携幼,也有驼条布袋的,也有拿着栲栳的,王喜也把腰苎裙联做丫口赶来,等了半日。典史坐在一个古庙里唱名给散,银子每钱可有九分书帕,谷一斗也有一升凹谷、一升沙泥,先给极贫。王喜道:“这咱不在里边的。”后边点到次贫,便探头伸脑去伺候,那里叫着?看看点完,王喜还道:“钱送得迟,想填在后边。”不知究竟没有,王喜急了,便跪过去。崔科怕他讲甚么,道:“你有田有地的,也来告贫?”那典史便叫赶出去。
王喜气得个不要,赶到崔科家里。他家里倒堆有几石谷,都是鬼名领来的,还有人上谢他的。他见了不由得不心头火发,道:“崔科,王八羔子!怎诓了人钱财,不与人造册?”崔科道:“咄!好大钱财哩!我学骗了你一个狗抓的来。”王喜道:“我有田有地,不该告贫,你该诓这许多谷在家里么?我到县里首你这狗攮的。”崔科道:“你首!不首的是咱儿子。”便一掌打去。王喜气不过,便一头撞过来,两个结扭做一处。只见众人都走过来,道王喜不是道:“他歹不中也是一个里尊,你还要他遮盖,怎生撞他?”那崔科越跳得八丈高,道:“我叫你不死在咱手里不是人,明日就把好差使奉承你。”那王喜是本分的人,一时间尚气,便伤了崔科。一想想起后边事:“他若寻些疑难差使来害我,怎么区处?”把一天愤气都冰冷了,便折身回家。
霍氏正领了王原立在门前,见王喜没有谷拿回,便道:“你关得多钱,好买馍馍与儿子吃?”王喜道:“有甚钱!崔科囚攮的得了咱钱,又不己咱造册。咱与他角子口,他要寻甚差使摆布咱哩!”霍氏道:“前日你不请得他吃酒,被他差拨了半年,如今与他角了口,料也被他腾倒个小死哩!”两个愁了一夜。清早起来,王喜道:“嫂子,如今时世不好,边上达子常来侵犯,朝廷不时起兵征剿,就要山东各府运粮接济。常见大户人家点了这差使,也要破家丧身的。如今恶了崔科,他若把这件报了我,性命就断送在他手里,连你母子也还要受累。嫂子,咱想咱一时间触突了崔科,毕竟要淘他气,不若咱暂往他乡逃避,过一二年回来,省得目前受害。”指着王原道:“只要你好看这孩子。”霍氏道:“哥,你去了,叫咱娘儿两个靠着谁来?你还在家再处。”王喜道:“不是这般说,我若被他算计了,你两个也靠我不得,这才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且喜家徒四壁,没甚行囊,收拾得了,与妻子大哭了一场,便出门去了。正是:恶吏威如虎,生民那得留?
独余清夜梦,长见故园秋。
王喜起了身,霍氏正抱着王原坐在家里愁闷。那张老三因为王喜冲突了崔科,特来打合他去陪礼,走来道:“有人在么?”霍氏道:“是谁?”张老三还道王喜在,故意逗他耍道:“县里差夫的。”那霍氏正没好气,听了差夫,只道是崔科,忙把王原放下,赶出来一把扭住张老三道:“贼忘八!你打死了咱人,还来寻甚么?”老三道:“嫂子,是咱哩!”霍氏看一看,不是崔科,便放了。老三道:“哥在那厢?”霍氏道:“说与崔科相打,没有回来。”老三道:“岂有此理!难道是真的?”霍氏道:“怎不真?点点屋儿,藏在那里?不是打死,一定受气不过,投河了。”张老三道:“有这等事?嫂子,你便拴了门,把哥儿寄邻舍家去,问崔科要尸首,少也诈他三五担谷。”果然霍氏依了赶去,恰好路上撞着崔科,一把抓住道:“好杀人贼哩!你诓了咱丈夫钱,不与他请粮,又打死他!”当胸一把,连崔科的长胡子也扭了。崔科动也动不得。
那霍氏带哭带嚷,死与不放。张老三却洋洋走来,大声道:“谁扭咱崔老爹?你吃了狮子心来哩!”霍氏道:“这贼忘八打死咱丈夫,咱问他要尸首!”老三道:“你丈夫是谁?”霍氏道:“王喜。”老三道:“是王喜?昨日冲撞咱崔老爷,我今日正要寻他陪礼。”霍氏道:“这你也是一起的,你阎罗王家去寻王喜,咱只和你两个县里去。”扯了便走。张老三道:“嫂子,他昨两个相打,须不干咱事。”霍氏道:“你也须是证见。”霍氏把老三放了,死扭住崔科,大头撞去。老三假劝。
随着一路,又撞出一个好揽事的少年、一个惯劈直的老者,便丛做一堆。霍氏道:“他骗咱丈夫一百钱,不与丈夫请粮。”崔科道:“谁见来?”霍氏便一掌打去,道:“贼忘八!先是咱一件衫,当了五十钱,你嫌少。咱又脱了条裙,当五十钱,你瞎里不瞧见咱穿着单裤么?”这老者道:“崔大哥,你得了他钱,也该与他开。”霍氏道:“是晚间咱丈夫气不愤的,去骂他。他一家子拿去,一荡子打死,如今不知把尸首撩在那里。”指着老三道:“他便是证见,咱和他县里去讲。”崔科道:“昨日是他撞咱一头,谁打他来?”老者道:“这等打是实了。嫂子,我想你丈夫也未必被他打死,想是粮不请得,又吃他打了两下,气不愤,或者寻个短见,或者走到那厢去了。如今依咱处,他不该得你钱不与你粮,待他处几担谷与你罢。”少年连叫:“是!是!”霍氏道:“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一向卖富差贫,如今上司散荒,他又诈人酒食才方报册,没酒食的写他票子,领出对分,还又报些鬼名,冒领官钱。咱定要官司结煞。”少年道:“这嫂子也了得哩!嫂子,官司不是好打的,凭他老人家处罢。”那老者道:“你当了裙衫,也只为请粮;今日丈夫不见,也只为请粮。我们公道处,少也说不出,好歹处五名极贫的粮与你,只好二两五钱银子、五担谷罢。”霍氏道:“谁把丈夫性命换钱哩?”崔科还在那里假强,张老三暗地对他道:“哥,人命还是假的,冒粮诈钱是真,到官须不输他妇人?”崔科也便口软,处到五两银子、八担谷。霍氏道:“列位老人家,我丈夫不知怎么,他日后把些差拨来,便这几两银子也不够使用。咱只和他经官立案,后边还有成说。”张老三道:“你如今须是女户,谁差得着?”霍氏还不肯倒牙,张老三道:“嫂子,这老人家处定了。崔老爹也一厘加不得了,你怕他后边有事,再要他写个预收条粮票,作银子加你。”众人团局,崔科也只得依处。霍氏也便假手脱散了伙,自与儿子过活。这边崔科劳了众人处分,少不得置酒相谢,又没了几两银子,不题。
却说王喜也是一味头生性,只算着后边崔科害他,走了出去,不曾想着如何过活,随身只带一个指头的刷牙、两个指头的筯儿、三个指头的抿子、四个指头的木梳,却不肯做五个指头伸手的事。苦是不带半厘本钱,又做不得甚生理,就是闯州县,走街坊,无非星相风水课卜,若说算命,他晓得甚么是四柱?甚么是大限、小限、官印、刃杀?要去相面,也不知谁是天庭?谁是地角?何处管何限?风水又不晓得甚来龙过脉、沙水龙虎?就起课也不曾念得个六十四卦熟,怎生骗得动人?前思后想,想起一个表兄,是个吏员,姓庄名江,现做定辽卫经历,不若且去投他。只是没盘缠,如何去得?不如捱到临清,扯粮舡纤进京再处。果然走到临清,顶了一个江西粮舡的外水缺,一路扯纤到通湾。吃了他饭,又得几钱工银,作了路费,过了京师,也无心观看。趱过了蓟州昌平,出了山海关,说不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定辽卫。
走到那边,衙门人道:“目下朝廷差宋国公征纳哈出,差去催趱军粮不在。”等了两日,等得回来,去要见,门上道:“你若是告状的,除了帽、拴了裙进去;若是来拜,须着了公服,待我替你投帖,若肯见请见。”王喜道:“我只有身上这件衣服,你只替我说表弟王喜拜就是了。”门上道:“这里不准口诉,口里拜帖儿是行不通的。”王喜见他做腔,道:“不打紧,我自会见。”自在那边伺候,恰值他出来,便向前一个喏,道:“表兄,小弟王喜在这里。”那庄经历把头一别,打伞的便把伞一遮去了。王喜大没意思,又等他回,便赶过去把轿杠攀住道:“表兄,怎做这副脸出来?”手下几掀掀不开,庄经历只得叫请进私衙来。两个相见,做了许多腔,道:“下官误蒙国恩,参军边卫,止吃得这厢一口水,喜得军民畏伏。”王喜备细告诉遭崔科蔽抑。庄江道:“敝治幸得下官体察民隐,却无此辈。”留了一箸饭,道:“请回寓,下官还有薄程。”走到下处,只见一个人忙忙的送一封书帕,说老爷拜上,道老爷在此极其清苦,特分俸余相送,公事多,不得面别去了。王喜上手便拆,称来先先二钱六分,作三钱。王喜呆了半日,再去求见。门上不容他,又着人分付店主人,催起身。只得叹了几口气出门,思量无路可投,只得望着来时这条路走。
行了两日,过了广宁,将到宁远地方,却见征尘大起,是宋国公兵来。他站在大道之旁,看他一起起过去,只见中间一个管哨将官,有些面善。王喜急促记不起,那人却叫人来请他去营中相见。见时,却是小时同窗读书的朋友全忠,他是元时义兵统领,归降做了燕山指挥佥事,领兵跟临江侯做前哨。一见便问他缘何衣衫褴缕,在这异乡?他备细说出来的情由,并庄表兄薄情。全忠道:“贤兄,如今都是这等薄情的,不必记他。但你目今没个安身之所,我营中新死了一个督兵旗牌,不若你暂吃他的粮。若大军得胜,我与你做些功,衣锦还乡罢。”王喜此时真是天落下来的富贵,如何不应允?免不得换了一副缠粽大帽、红曳撒,捧了令旗、令牌,一同领兵先进。过了三坌河,却好上司拨庄经历,解粮饷到前军来,见了王喜,吃一大惊,就来相见,说他荣行,送了三两赆礼,求他方便,收了粮。王喜道宁可他薄情,也便为他周旋,自随全先锋进兵。进兵时,可奈这些鸦雀日日在头上盘绕,王喜也便心上不安。那主将临江侯陈镛,又是个膏粱子弟,不晓得兵事,只顾上前,不料与大兵相失了,传令道:“且到金山屯兵,抓探大兵消息。”离金山还有百余里,一派林木甚盛,忽听得林子里一声铜角,闪出五六百鞑子来。临江侯倚部下有兵万余,叫奋勇杀上去。全指挥便挥刀砍杀,准知这是他出哨的兵,初时也胜他一阵,不料还有四五万大兵在后,追不过一二里,他大兵已到。跑得个灰尘四起,天地都黑,两边乱砍。全指挥马已中箭跌倒了,王喜便把自己的马与他骑。争奈寡不胜众,南兵越杀越少,鞑兵越杀越多,全军皆死。
王喜因没了马,也走不远,与一起一二百人只逃到林子边,被追着砍杀。王喜身中一枪,晕倒在地。两个时辰醒来,天色已晚,淡月微明。看一看地下时,也有折手的、折脚的、断头的、马踹的,都是腥血满身。那死的便也不动了,那未死的还在那里挣跳,好不惨伤。自己伤了枪,也不能走动,坐在林子里,只见远远有人来,王喜道:“可可还剩得一个人,好歹与他走道儿罢。”到面前时,却是个妇人,穿着白,道:“王喜,你大难过了,还有大惊,我来救你。”便拾一枝树枝,在地下画一个丈来宽大圈子,道:“你今夜只在此圈里坐,随甚人鬼不能害你,异日还在文登与你相会。”说罢这妇人去了。王喜道:“这所在有这妇人?非仙即佛。又道文登相会,这话也不解。但坐在这圈中,若有鞑子来,岂不被他拿去?且坐了试一试看。”坐到初更,只听得林子背后,刮刮风起,跳出一个夜叉来,但见:两角孤峰独耸,双晴明镜高悬。朱砂鬓发火光般。四体犹如蓝靛。臂比刚钩更利,牙如快刃犹铦。吼声雷动小春天。行动一如飞电。竟望着王喜扑来。王喜不是不要走,却已惊得木呆,又兼带伤,跑不动了。只见那夜叉连扑几扑,到圈子边就是城墙一般,只得把王喜看上几眼,吼了几声。回头见地上无数的死人,他便大踏步赶去,把头似吃西瓜般,呝搜呝搜一连抓来,啃上几十个。手足似吃蕨般,啯散啯散,吃了几十条。那王喜看了,魂都没了。那夜叉吃饱了,把胸前揉上两揉,放倒头睡了一觉,跳将起来,双爪把死人胸膛挖开,把心肝又吃上几十副才去。渐渐天明,王喜道:“若没这圈,咱一个也当不得点心哩!若得到家,咱也只拜佛看经,谢神圣罢了。”又到战场上看时,看见个人,身边一个钞袋,似有物的。去捏一捏,倒也有五七两兵粮,他就去各人身边都搜一搜,倒搜得有七八十两。笑了笑道:“惭愧,虽受了惊险,得这横财,尽好还乡度日了。”一个人孤孤影影、担饥受饿了几日,走到辽阳,恰好撞见庄经历,只道他差回,忙请他到衙。问起却是军败回来,他就道:“足下如今临阵逃回,是有罪的了。下官也不敢出首,也下好留足下。还须再逃到别处,若再迟延,恐我衙门人知得不便。”王喜只得辞了,道他原是薄情的,只是我身边虽有几两银子,回家去怕崔科来查我来历,我且到京师去做些生意,若好时,把妻子移来便是。一路向着京师来,已不差得一日路,在路上叫驴,集儿上已没了,只得走着。看见远远一个掌鞭的骑着驴来,他便叫了,不料上驴时掌鞭的把他腰边一插,背后一搀,晓得他有物了,又欺他孤身客人,又不曾赶着队,捱到无人处所,猛地把驴鞭上两鞭,那驴痛得紧,把后脚一掀,把个王喜“扑”地一声,跌在道儿上。那掌鞭的将来按住,搜去暖肚内银两,跳上驴去了。比及王喜爬得起来,只见身边银子已被拿去,两头没处寻人,依然剩得一个空身。正是:薄命邓通应饿死,空言巴蜀有铜山。
王喜站在道儿上,气了一回,想了一回,道:“枉了死里逃生,终弄得一钱没有,有这等薄命!”走了半晌,见一个小火神庙,道:“罢,罢!这便是我死的所在了,只是咱家妻子怎生得知?早知如此,便在家中,崔科也未便奈何得我死。”坐在神前,呜咽哭了半日。正待自缢,只听得“呀”地一声里边门响,道:“客官不可如此!人身难得。”却是五十来岁一个僧人。王喜把从前事告诉这僧人,僧人劝慰了一番,道:“小僧大慈是文登县成山慧日寺和尚,因访知识回来,不期抱病在此两月,今幸稍痊,不若檀越与小僧同行,到敝寺,小僧可以资助檀越还乡。”王喜道:“小可这性命都是师父留的,情愿服侍师父到宝刹。”过了两日,大慈别了管庙道人,与王喜一路回寺,路上都是大慈盘缠。到得寺中,原来这大慈是本寺主僧,那一个不来问候?大慈说起途中抱病,路上又亏这檀越扶持得回,就留王喜在寺中安寓。一日大慈与王喜行到殿后白衣观音宝阁,王喜见了,便下老实叩上十来个头,道:“佛爷爷,果然在这里相会。”大慈道:“檀越说救夜叉之患的,便是此位菩萨么?敝寺原是文登县地界。”王喜因道:“前日原有愿侍奉菩萨终身,如今依了菩萨言语,咱在此出了家罢。”大慈道:“檀越有妻有子,也要深虑。”王喜道:“沙场上、火神庙时,妻子有甚干?弟子情愿出家。”大慈道:“若果真心,便在此与老僧作个伴儿,也不必落发。前许资助盘费,今你不回,老僧就与你办些道衣,打些斋,供佛斋僧罢。”随即择了个好日,不两日点起些香烛,摆列些蔬果,念了些经文,与他起个法名叫做“大觉”,合寺因叫他“大觉道者”。自此王喜日夕在大慈房中搬茶运水,大慈也与他讲些经典,竟不思家了。
家中霍氏虽知他是逃在外边,却不知是甚所在,要问个信,也没处问,只是在家与儿子熬清受淡,过了日子。光阴迅速。王喜去时,王原才得两周三岁,后边渐渐的梳了角儿读书,渐渐蓄了发。到十五六岁时,适值连年大熟,家中到也好过子。常问起父亲,霍氏含着泪道:“出外未回。”到知人事时,也便陪着母亲涕泣思想。只是日复一日,不见人来,又没有音信。他问母亲道:“爷在外做甚?怎再不见他?”霍氏细把当日说起,王原道:“这等爹又不是经商,他在外边怎么过?我怎安坐在家,不去抓寻?”使要起身。霍氏道:“儿,爹娘一般的,你爹去了,你要去寻,同在一家的,反不伴我?你若又去了,叫我看谁?”王原听了,果是有理,就不敢去,却日日不忘寻爹的念头。到十八岁时,霍氏因他年纪已大,为他寻了个邻家姓曾的女儿做媳妇。虽是小户人家,男家也免不得下些聘物,女家也免不得陪些妆奁,两个做亲。才得一月,那王原看妻子却也本分孝顺,便向母亲道:“前日要去寻爹,丢母亲独自在家里,果是不安。如今幸得有了媳妇,家中又可以过得,孩儿明日便起身去寻父亲。”霍氏道:“你要去,我也难留你。只是没个定向,叫你那厢去寻?寻得见寻不见,好歹回来,不要使我记念。”又拿一件破道袍、一条裙道:“这布道袍因你爹去时是秋天,不曾拿得去,这裙是我穿的,你父亲拿去当钱与崔科,这两件他可认得,你两边都不大认得,可把这个做一执照。”姑媳两个与他打点了行李,曾氏又私与他些簪珥之类,道:“你务必寻了回来,解婆婆愁烦。”王原便拜别起身,正是:矢志寻乔木,含悲别老萱。
白云飞绕处,瞻望欲消魂。
想道他父亲身畔无钱,不能远去,故此先在本府益都、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诸城、蒙阴、莒州、沂水、日照各县,先到城市,后到乡村,人烟凑集的处在,无不寻到。又想道父亲若是有个机缘,或富或贵,一定回来。如今久无音信,毕竟是沦落了,故此僧道、星卜,下及佣工、乞丐里边,都去寻访。访了几月,不见踪迹,又向本省济南、兖州、东昌、莱州各府找寻。也不知被人哄了几次,听他说来有些相似,及至千辛万苦寻去,却又不是。他并没个怨悔的心,见这几府寻不见,便转到登州,搭着海船行走。
只见这日忽然龙风大作,海浪滔天,曾有一首《黄莺儿》咏他:砂石走长空。响喧阗,战鼓轰。铜墙一片波涛涌。
看摧樯落篷。苦舟欹楫横。似落红一点随流送。
叫天公。任叫舴猛,顷刻饱鱼龙。那船似蝴蝶般东飘西侧,可可里触了礁,把船撞得粉碎。王原止抱得一块板,凭他来去。上边雨又倾盆似倒下来,那头发根里都是水,胸前都被板磨破了,亏得一软浪,打到田横岛沙上搁住了。他便望岸不远,带水拖泥,爬上岸来。只见磨破的胸前经了海里咸水,疼一个小死,只得强打精神走起,随着路儿走去,见一个小小庙儿:荒径蓬蒿满,颓门薜荔缠。
神堂唯有板,砌地半无砖。
鬼使趾欲断,判官身不全。
苔遮妃子脸,尘结大王髯。
几折余支石,炉空断篆烟。
想应空谷里,冷落不知年。王原只得走进里边暂息,向神前拜了两拜,道:“愿父子早得相逢。”水中淹了半日一夜,人也困倦,便扯过拜板少睡,恍惚梦见门前红日衔山,止离山一尺有余,自己似吃晚饭一般,拿着一碗莎米饭在那里吃,又拿一碗肉汁去淘。醒来却是一梦,正是:故乡何处暮云遮,漂泊如同逐水花。
一枕松风清客梦,门前红日又西斜。
正身子睡着想这梦,只听得祠门数数,似有人行走,定睛看处,走进一个老者来,头带东坡巾,身穿褐色袍,足着云履,手携筇杖,背曲如弓,须白如雪,一步步挪来,向神前唱了一个喏。王原见了也走来作上一个揖,老者问少年何来,王原把寻亲被溺之事说了,老者点头道:“孝子,孝子!”王原又将适才做的梦请教,那老者一想道:“恭喜,相逢在目下了。莎米根为附子,义取父子相见;淘以肉汁,骨肉相逢;日为君父之象,衔山必在近山,离山尺余,我想一尺为十寸,尺余十一寸,是一‘寺’字,足下可即山寺寻之。”王原谢了老者,又喜得身上衣衫已燥,行李虽无,腰边还有几两盘缠,还可行走,便辞了老者,出了庙门,望大路前进。因店中不肯留没行李的单身客人,只往祠庙中歇宿。一路问人,知是文登县界,他就在文登县寻访。过了文登山、召石山、望海台、不夜城,转到成山。成山之下,临着秦皇饮马池,却有一座古寺,便是王喜在此出家的慧日寺。王原寻到此处,抬头一看,虽不见壮丽闳玮,却也清幽庄雅。争奈天色将晚,不敢惊动方丈,就在山门内金刚脚下将欲安身。只见一个和尚搂着一个小沙弥,两个一路笑嘻嘻走将出来,把小沙弥亲了一个嘴,小沙弥道:“且关了门着。”正去关门,忽回头见一个人坐在金刚脚下,也吃了一惊。小沙弥道:“你甚么人?可出去,等我们关门。”王原道:“我也是个安丘书生,因寻亲渡海,在海中遭风失了行李,店中不容,暂借山门下安宿一宵,明日便行。”这两个怪他阻了高兴,狠狠赶他。又得里面跑出一个小和尚来,道:“你两个来关门,这多时,干得好事,我要捉个头儿!”看他两个正在金刚脚边催王原出门,后来的,便把沙弥肩上搭一搭道:“你是极肯做方便的,便容他一宵,那里不是积德处?”沙弥道:“这须要禀老师太得知。”沙弥向方丈里跑来,说:“山门下有个人,年纪不上二十岁,说是寻亲的,路上失了水,没了行李,要在山门借宿。催逼不去,特来禀知师太。”大慈道:“善哉!是个孝子了。那里不是积善处?怕还不曾吃夜饭,叫知客留他茶寮待饭,与他在客房宿。”只见知客陪吃了饭,见他年纪小,要留他在房中。那关门的和尚道:“是我引来的,还是我陪。”王原道:“小生随处可宿,不敢劳陪。”独自进一客房。这小和尚对着知客道:“羞!我领得来,你便来夺。”知客道:“你要思量他,只怕他翻转来要做倒骑驴哩。”次早王原梳洗了,也就在众僧前访问,众僧没有个晓得。将欲起身,来方丈谒谢大慈,大慈看他举止温雅,道:“先生尊姓、贵处?”王原道:“弟子姓王名原,青州府安丘县人,有父名为王喜,十五年前避难出外,今至未回。弟子特出寻访。”大慈道:“先生可记得他面庞么?”王原道:“老丈离家时,弟子只得三岁,不能记忆。家母曾说是柑子脸,三绺须,面目老少不同,与弟子有些相似。”大慈道:“既不相识,以何为证?”王原道:“有老父平日所穿布袍与家母布裙为验。”大慈听了半晌,已知他是王喜儿子了,便道:“先生且留在这边,与老僧一观。”正看时,外边走进一个老道人,手里拿着些水,为大慈汲水养花供佛。大慈道:“大觉道者,适才有一个寻亲的孝子,因路上缺欠盘缠,将两件衣来当,你可当了他的?”那道人看了一看,不觉泪下。大慈道:“道者缘何泪下?”那道人道:“这道袍恰似贫道家中穿的,这裙恰是山妻的,故此泪下。”大慈道:“你怎么这等认得定?”那道者道:“记得在家时,这件道袍胸前破坏了。贫道去买尺青布来补,今日胸前新旧宛然。又因没青线,把白线缝了,贫道觉得不好,上面把墨涂了,如今黑白相间。又还有一二寸,老妻把来接了裙腰,现在裙上。不由人不睹物凄然。”大慈道:“这少年可相认么?”道者说:“不曾认得。”大慈道:“他安丘人,姓王名原。”因指那道者对王原道:“他安丘人,姓王名喜。”王原听了道:“这是我父亲了。”便一把抱住,放声大哭,诉说家中已自好过,母亲尚在,自己已娶妻,要他回去。
莫向天涯怨别离,人生谁道会难期?
落红无复归根想,萍散终须有聚时。王道人起初悲惨,到此反板了脸道:“少年莫误认了人,我并没有这个儿子。”王原道:“还是孩儿不误认,天下岂有姓名、家乡相对,事迹相同如此的?一定要同孩儿回去。”王道人道:“我自离家一十五年,寄居僧寺,更有何颜复见乡里?况你已成立,我心更安,正可修行,岂可又生俗念?”王原道:“天下没有无父之人,若不回家,孩儿也断不回去。”又向大慈并各僧前拜谢道:“老父多承列位师父看顾,还求劝谕,使我一家团圆,万代瞻仰。”只见大慈道:“王道者,我想修行固应出家,也有个在家出家的。你若果有心向善,何妨复返故土?如其执迷,使令嗣系念,每年奔走道途,枉费钱财,于心何安?依我去的是。”众僧又苦苦相劝,王喜只得应允了。王原欢喜不胜,就要即日起身。大慈作偈相送道:草舍有净土,何须恋兰若?
但存作佛心,顿起西方钥。又送王原道:方寸有阿弥,尔惟忠与孝。
常能存此心,龙天自相保。
父子两个别了众僧,一路来到安丘,亲邻大半凋残,不大有认得的了。到家夫妻相见,犹如梦里。媳妇拜见了公公,一家甚是欢喜。此时崔科已故,别里递说他以三岁失父,面庞不识,竟能精忱感格,使父复回,是个孝子,呈报县中。王原去辞,都道已开报上司了。其年正值永乐初年,诏求独行之士,本省备开王原寻亲始末,将他起送至京。圣上嘉其孝行,擢拜河南彰德府通判。王原谢恩出京,就迎了两老口赴任禄养。后因父母不服水土,又告养亲回籍。不料数年间,父母年纪高大,相继而殁,王原依礼殡葬,自不必说。终日悲泣,几至丧生。服阅荐补常德通判,再转重庆同知,所至皆能爱民报国。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有由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