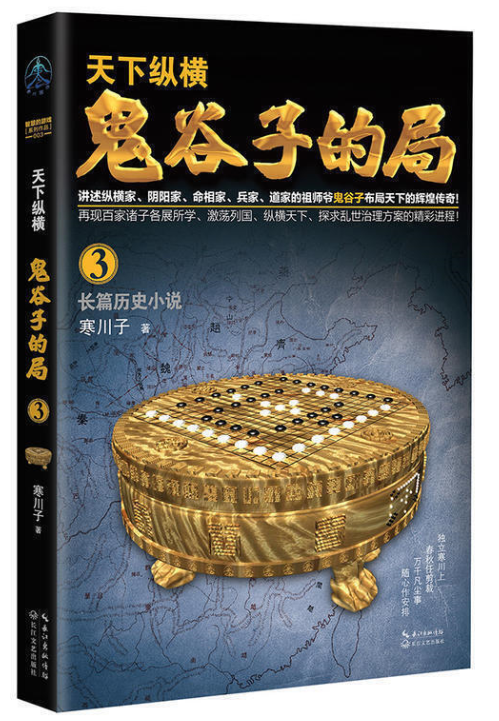色如老女色何观,情到盲儿情亦阑。
强解风流时世辈,盲儿老女可同看。
却说香儿房内,除绿云、红雨、采萧、芊芊、贝锦外,还有上宿的两人:一个是车载之母,一个是李名之妻。李名死后,康夫人就令在里面居住。只有个侄儿,李寡妇常去看望。这寡妇年近五十,容颜虽老,而态度犹存。常见耿朗、香儿恩爱缠绵,就打动他儿女心情。至耐不过时,便用角先生顶缸。这日正值八月十六日,耿朗从东角门走出。宿酒未消,倦容满面,寡妇撞见,因想到昨夜在二娘房里酒后之色,不知如何畅满,便立在角门边胡想。谁知梦卿直坐了一夜,早间耿朗醒来,记得昨夜呕吐,而衾褥鲜好,并无一些污染。梦卿往东里屋梳妆去时,耿朗下床,偶立在北边床前,闻得有些酒气。揭起褥子一看,下面迭着件葱绿新绣夹衫,一条项帕,俱是吐污了的。北套间内,又卷着一副衾褥,亦是一派酒气,心内大觉不安。走到外间屋里,坐在床上。梦卿走来,耿朗只恐又有谏劝言语。不想梦卿连昨夜一字不提,只顾问茶问水。原来耿朗妻室既是五房,而情形亦不一般。若遇耿朗有过,云屏是在劝不劝之间。爱娘虽亦常劝,但加上些耍笑,又象不甚劝的光景。香儿彩云全不知劝。惟有梦卿,事事皆劝,以此耿朗又爱听又怕听。然梦卿亦渐次觉得,故自此不再劝了。当时耿朗梳沐已毕,呷了些醋笋汤,看过康夫人,复到梦卿屋里倚枕而卧。云屏、爱娘、香儿、彩云一齐走来,坐了半晌,饭后方散。香儿回到屋里,李寡妇迎着道:“大爷今日病酒,听说昨日吐了半夜,二娘房内的都不曾合眼。”香儿咧一咧嘴,道:“我不信!二娘脸上为何全无倦意?且是红白得好看。”李寡妇听了,便低低道:“连春大姐亦有些发福。”香儿道:“人走时运马走膘,时运既来,安得不好?”李寡妇道:“不但他一个,连上宿的众妈妈、梁嫂子,亦都有起色。”香儿笑道:“一人有福,托带满屋。你既爱慕,何不换了过去?”李寡妇道:“哎呀!奶奶是何样侍我,我敢坏了良心?除非象采艾、采萧那一种无志气的,才有那朝秦暮楚的想头。”香儿道:“这山望着那山高,有要去的,便随他去。”李寡妇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男子们性情那个是拿得定的?”香儿笑而不语。李寡妇又大声道:“奴婢要告几日假,去看看侄儿,又恐奶奶屋内少人。”香儿道:“但去不妨,只不可贪恋着野孤老多迟日子。”于是李寡妇于十七日便去看侄儿。住了两日,侄儿出外,侄妇归宁,李寡妇遂替看家。
午间小解登东,听得墙外亦有溲溺声音,脚登墙砖望外看时,却是个失目男子,立着小解。其物壮大,伟然可喜。目触心动,勃然兴作。回至屋里,正无聊赖,忽听街上三弦声,急隔门张望,那算命先生正是小解男子。一时情迷,便托算命,将瞎子唤入屋内坐下。那瞎子问明八字,推算一番,无过说些月令平常,小人不足的套话。算毕,李寡妇送一杯茶来。瞎子接茶,正摸着寡妇的手,滑輭不干。再察口音,就知年齿亦不甚老。茶毕,寡妇给与命礼钱文,却落了两个在地下。瞎子弯腰乱摸,东一把,西一把,正摸着寡妇的脚,纤细堪足一捻。寡妇反笑道:“好先生,看我家无人,竟敢调戏。”瞎子见如此光景,乃挑道:“小子双瞎,不知回避,该死该死!还求娘子施恩,有登东处,借重片时。”寡妇又恼道:“好先生,望妇人家说这些事,益发没了道理!”因走至瞎子背后,揪住衣领要打。瞎子顺势一仰,将寡妇撞了一交。寡妇力微,手足乱动,两条大腿,正夹着瞎子脖项,落了头巾。瞎子用力一挺,恰好撞着李寡妇小肚,又好笑,又好痛,因道:“先生起来,这是甚么样子!”瞎子听得,益发在寡妇身上乱滚,只道夹坏了脖项,弄得寡妇鬓发、纽扣、裙带、弓鞋,大半散落,周身俱被摸索。及至乘便立起,瞎子还在地上摸头巾。寡妇向后一闪,不防被矮凳一绊,两足朝天,一背向地。瞎子摸至凳旁,撞着輭屁,即腾身而上,正好合了格式。寡妇因央道:“先生起来,有话商议。”瞎子又象耳聋,寡妇用力推开,还沾了满裤裆秽物。因道:“彼此有情,何必心急!且大晴白日,开门张户,万一有人撞见,如何措处?”瞎子道:“是,是。但小子自幼从无尝此滋味,求娘子可怜则个!”寡妇道:“你走百家门,大街小巷,岂有不知?物理人情,岂有不晓?约你今晚起更后来,人不知,鬼不觉,可享终宵之乐。且定个后会之策,岂不更好?”瞎子大喜,连连应允,急急整理衣巾、三弦、明杖,临行约下咳嗽为号,又抱住李寡妇,没好没歹亲了几个嘴,方一步步走去,李寡妇目送一程。
到得晚间,收拾衾褥,洗沐下体,长在门缝中张望。起更多时,尚不见来。因恨道:“瞎业障!终不济事。早知如此,倒不如白日任他弄了”。又转道:“或是路远也未可知。”等了一会,已交二鼓,便蹲在地下。忽然抬头,瞎子已在面前。才待怪他来迟,突地往后倒仰,一跌惊醒,却是一梦。是一个大黑猫从身下钻去。立起身来,听了听街上,业经三更,又急又气,又怜又骂。欲要去睡,且又难舍。原来那瞎子回到寓所,晚饭之后,托付同伴换上衣服,拄着明杖,走至大街,已是掌灯时候。人马喧杂,被西瓜皮滑了一个筋斗,将头巾跌落。急切寻不着,只得露着头,寻那走熟的便路小巷而行。又错走在泥里,将一支鞋陷了进去,捞摸不着,又只得光了一只脚,一步步漫走。谁知以南作北,以东作西,白走了许久,将近二更,路旁恶狗拦道,瞎子用明杖去打,反被狗将明杖咬夺了去。瞎子急得乱嚷,比及街坊上人出来指明路径,已是二鼓。又无明杖,不敢快走,七曲八折,刚然穿到大街,又被一家醉汉撞了一个仰面朝天。
瞎子受了一肚闷气,又被这一撞,就要借故讹诈,便两手捧了小肚,大骂道:“谁家贼根畜生,夺去鞋帽,还踢命根,金吾卫都不拿人!”那汉被讹,酒怒大发,迎面一掌,瞎子便倒。那汉乱打,将衣服扯得粉碎。前番踢命根是假话,今番踢命根是真情矣。瞎子昏卧于地,醉汉一溜烟从小巷中走脱。及至苏醒转来,漏声已交三鼓。是时金风作冷,玉露生寒。带剑诘奸者连类而至,击柝警夜者结伴而来,便要拿瞎子犯夜。瞎子哭诉前情,一齐笑道:“你既作生意,岂不知这条路是走不得的?这条路自元末以来,乃奸人恶鬼出没之场,我们还成群打伙的来往,你一个瞽目之人,如何走得?不伤性命,就是万幸矣。跟我们来,且在铺房中息宿,明日回家,免得犯禁。”瞎子无奈,只得依允,咬牙忍痛而行,时已四更了。再说李寡妇在门前守至五更,不见他来,只得进了屋子。瞽先生既不可得,少不的又要借重那角先生矣。虽非鼓角齐鸣,军威大振,而角声鸣咽,亦只有进无退而已。闷闷的住了数日,侄妇回家,方才转来,仍旧服侍香儿。起初李寡妇之用角先生不过于情不能遏时偶用一两次,至遇瞎子勾情以后,便情不自禁,夜夜都离他不得。一日失于检点,被红雨摸着,问起原由,李寡妇恐怕唱扬,说了多少妙处。红雨不信,李寡妇便借与红雨试用。于是两人带角先生在身边,从此互相雌雄,遂成莫逆。
这一来有分教:启愤怨于同群,淫声毕露。擅权威之独断,丑态弥张。
散人曰:此所以丑香儿也。其丑香儿奈何?红雨者,香儿之媵也。媵之不正,嫡之咎也。等而上之,李寡之淫,可以摇其媵,亦可以摇其嫡也。故曰所以丑香儿也。后此补红雨之缺者,即名红雨,而不另易,亦所以警香儿也。惟香儿暴弃自甘,故又深之以童氏一节。
车载母李名妻,与骆氏之义同。李寡之侄及妇及算命瞎子,俱无名姓者,皆借用人也。
“大觉不安”及“只恐又有谏劝言语”瞒照之与梦卿,已大有芥蒂矣。“只顾问茶问水”及“自此不再劝了”,梦卿之与瞒照,亦大有界限矣。“朋友数,斯疏矣。”夫妻亦闺中朋友也。前第六回结语中目梦卿为贾谊,岂虚言哉!贾谊上言不曰“长太息”,则曰“痛哭”,即使朋友听之,亦难乎其为情矣。然则贾公亦不庸中之庸者也。
此书一部中**者惟此回与第十回耳,然皆不成实事,盖成实事则便索然矣。试思男女未媾精之前,是何样情致,既媾精之后,是何等意味,不言可知矣。神仙游戏三昧,作此两回者,亦复尔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