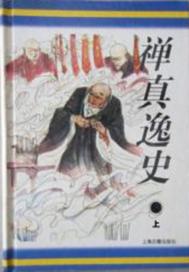话说马氏把被抄的情形,及将**银两安放停妥的事,把个电报通知周庸祐,总不见复电,心里自然委放不下。这时冯、骆两管家都被扣留,也没人可以商议各事的。还幸当时亲家黄游击,因与大吏意见不投,逃往**,有事或向他商酌。奈这时风声不好,天天传粤中大吏要照会****拿人,马氏不知真假,心内好不慌张。又见潘子庆自逃到**之后,镇日不敢出门,只躲在西么台上大屋子里,天天打算要出外洋,可见事情是紧要的无疑了。但自己不知往哪里才好,又不得周庸祐消息,究竟不敢妄自行动。怎奈当时风声鹤唳,纷传周庸祐已经被拿,收在上海道衙里,马氏又没有见复电,自然半信半疑。
原来周庸祐平日最是胆小,且又知租界地方原是靠不住的,故虽然接了马氏之电,惟是自己住址究不欲使人知道,因此并不欲电覆马氏,只挥了一函,由邮政局付港而已。
那一日,马氏正在屋子里纳闷,忽报由上海付到一函,马氏就知是丈夫周庸祐付回的,急令呈上,忙拆开一看,只见那函道:马氏夫人妆鉴:昨接来电,敬悉一切。此次家门不幸,遭此大变,使廿年事业,尽付东流。回首当年,如一场春梦,曷胜浩叹!差幸港中产业生理,皆署别名,或可保全一二耳。夫人当此变故之际,能及早知机,先逃至港,安顿各事,深谋远虑,儿子亦得相安无事,感佩良多。自以十余年在外经营,每不暇涉及家事,故使骄奢淫逸,相习成风,悔将何及!即各房姬妾,所私积盈余,未尝不各拥五七万,使能一念前情,各相扶持,则门户尚可支撑。但恐时败运衰,各人不免自为之所,不复顾及我耳。此次与十二宅既被查抄,眷属又被拘留,回望家门,诚不知泪之何自来也!
古云“罪不及妻孥”,今则婢仆家人,亦同囚犯;或者皇天庇佑,罪亦无名,未必置之死地耳。愚在此间,亦与针毡无异,前接夫人之电,不敢遽覆者,诚恐行踪为人所侦悉故也。盖当金帅盛怒之时,凡通商各埠,皆可以提解回国,此后栖身,或无约之国如暹罗者,庶可苟延残喘而已。港中一切事务,统望夫人一力主持,再不必以函电相通。愚之行踪,更直秘密,待风声稍息,愚当离沪,潜回**一遭,冀与夫人一面,再商行止。时运通塞,总有天数,夫人切勿以此介意,致伤身体。匆匆草覆,诸情未达,容待面叩。敬问贤助金安。
愚夫周庸祐顿首
马氏看罢,自然伤感。惟幸丈夫尚在沪上,并非被拿,又不免把愁眉放下。一面派人回省,打听家属被官吏拘留,如何情景。因为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儿,统通被留去了,自不免挂心。迨后知得官府留下家属,全为查问**自己的产业起见,也没有什么受苦,这时反不免悲喜交集。喜的是女儿幸得平安,悲的就怕那些人家,把自己在港的某号产业、某号生理,一概供出,如何是好?还亏当时官吏,办理这件案实在严得一点,周氏两边家人,都自见无辜被拘,一切周家在**的产业都不肯供出。在周乃慈的家人,自然想起周乃慈在生时待人有些宽厚,固不肯供出,一来这些人本属无罪,与犯事的不同,也不能用刑逼供,故讯问时都答话不知,官吏也没可如何。至于周庸祐的家人,一起一起的讯问,各姨太太都说家里各事向由马氏主持,庶妾向不能过问的,所以港中有何产业,只推不知。至于管家人,又供说**周宅另有管家人等,我们这些在省城的,在**的委实不知。问官录了供词,只得把各人所供,回覆大吏。
大吏看了,暗忖这一干人都如此说,料然他不肯供出,不如下一张照会到****去,不怕查封他不得。又看了那管家的供词,道是管理周家在省城的产业,便令他将省城的产业一一录了出来,恐有漏抄的,便凭他管家所供来查究。因此再又出了一张告示,凡有欠周栋臣款项,或有与周栋臣合股生理,抑是租赁周栋臣屋子的,都从速报明。一切房舍,都分开号数,次第发出封条。其生理股本及欠周氏银两的,即限时照数缴交善后局。因此上省中商场又震动起来。
大约生意场中,银子都是互相往来的,或那一间字号今天借了周栋臣一万,或明天周栋臣一时手紧,尽会向那一间字号借回八千,无论大商富户,转动银两,实所不免。因当时官府出下这张告示,那些欠周栋臣款项的,自然不敢隐匿。便是周家合股做生理的,周家尽会向那字号挪移些银子,若把欠周家的款项,及周家所占的股本,缴交官府,至于周家欠人的,究从那里讨取?其中自然有五七家把这个情由禀知官吏。你道官吏见了这等禀词,究怎么样批发呢?那官吏竟然批道:“你们自然知周庸祐这些家当从哪里来,他只当一个库房,能受薪水若干?若不靠侵吞库款,哪里得几百万的家财来?这样,你们就不该与他交易,把银来借与他了,这都是你们自取,还怨谁人?且这会查抄周家产业,是上台奏准办理的,所抄的数目,都报数人官,那姓周的纵有欠你们款项,也不能扣出。况周庸祐尚有产业在**的,你们只往**告他也罢了。”各人看了这等批词,见自己欠周家的,已不能少欠分文,周家欠自己的,竟无从追问,心上实在不甘,惜当时督帅一团烈性,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所以商家哪有不震动起来。偏是当时衙门人役,又故意推敲,凡是与周家有些戚谊,与有来往的,不是指他私藏周家银物,便是指他替周庸祐出名,遮瞒家产,就借端鱼肉,也不能尽说。所以那些人等,又吃了一惊,纷纷逃窜,把一座省城里的商家富户,弄成风声鹤唳。过了数十天,人心方才静些。
一府两县,次第把查抄周、傅、潘国家的产业号数,呈报大吏。那时又对过姓周家属的供词,见周庸祐是落籍南海大坑村,那周庸祐自富贵之后,替村中居民尽数起过屋子。初时周庸祐因见村中兄弟的屋子湫陋,故此村中各人,他都赠些银子,使他们各自建过宅舍,好壮村里观瞻,故阖村皆拆去旧屋,另行新建。这会官府见他村中屋子都是周庸祐建的,自然算是周庸祐的产业,便一发下令,都一并查抄回来。这时大坑村中居民眼见屋子要入官去了,岂不是全无立足之地,连屋子也没得居住?这样看来,反不若当初不得周庸祐恩惠较好。这个情景,真是阖村同哭,没可如何,便有些到官里求情的。官吏想封了阖村屋宇,这一村居民都流离失所,实在不忍,便详请大吏,把此事从宽办理,故此查封大坑村屋宇的事,眼前暂且不提。
只是周庸祐在**置下的产业,做下的生理,端的不少,断不能令他作海外的富家儿,便逍遥没事,尽筹过善法,一并籍没他才是,便传洋务局委员尹家瑶到衙商议。囗大吏道:“现看那四家抄查的号数,系姓傅的居多,那周庸祐的只不过数十万金。试想那四家之中,自然是算周庸祐最富,不过因傅家产业全在省城,故被抄较多。若周庸祐的产业在省城的这般少,可知在**的就多得很了。若他在港的家当,便不能奈得他何,试想官衙员吏何止万千,若人人吞了公款,便逃到洋人地面做生理,置屋业,互相效尤,这还了得!你道怎么样办法呢?”
那尹家瑶听了,低头一想,觉无计可施。原来尹家瑶曾在**读过英文,且当过英文教习,亦曾到上海,在程少保那里充过翻译员,当金督帅过沪时,程少保见自己幕里人多,就荐他到金督帅那里。还亏他有一种做官手段,故回粤之后,不一二年间,就做到天字一号的人员,充当洋务局总办。他本读英文多年,只法律上并未曾学过,当下听得金督帅的言语,便答道:“**中周庸祐生理屋业端的很多,最大的便是囗囗银行,占了几十万的股份,但股票上却不是用他的名字。其次,便算那一间囗记字号,比周乃慈的那囗囗昌字号生意还大呢!只是他用哪一个名字注册,都无从查悉。其余屋业,就是周、潘三家也不少,究竟他们能够侵吞款项,预先在**置产业,好比狡兔三窟,预为之谋,想契纸上也未必用自己名字了,这样如何是好?”金督帅道:“不如先往**一查,回来再行打算。”尹家瑶答道:“是。”金督便令草了一张告示,知照港督,说明委员到港,要查姓周的产业来历。
尹家瑶一程来到**,到册房,从头至尾,自生理册与及屋业册,都看过一遍,其中有周、潘名字的很少,纵有一二,又是与人暗借了银款的,这情节料然是假。
惟是真是假,究没有凭据。胡混过了两天,即回到省里,据情口覆金督。自经这一番查过之后,周、潘两家人等,少不免又吃一点虚惊。因为中、英两国究有些邻封睦谊,若果能封到自己产业,因是财爻尽空;且若能封业,便能拘人。想到这里,倍加纳闷,只事到其间,实在难说,唯有再行打听如何罢了。
过了数日,金督帅见尹家瑶往**查察周、潘产业,竟没分毫头绪,毕竟无从下手,便又传尹家瑶到街商议,问他有什么法子。尹家瑶暗忖金督之意,若不能封得周、潘两家在港的产业,断不干休。但他的性情又不好与他抗辩,便说道:“此事办来只怕不易,除是大帅把一张照会到港督处,说称某项屋业,某家生理,是姓周、姓潘的,料****体念与大帅有了交情,尽可办得好,把他来封了。且职道又是亲往**查过的,算有些证据,实与撒谎的不同。此计或可使得,未知大帅尊意如何?”金督听了,觉此言也有些道理,便问尹家瑶道:“究竟哪号生理、哪号屋业,是姓周、姓潘的,你可说来。”尹家瑶便不慌不忙的说道:“坚道某大宅子,西么台某大宅子,及周围与合股囗囗银行,囗荣号,囗记号,此人人皆知。至于某地段某屋铺,统统是姓周的。又西么台某大宅子,对海油麻地某数号屋铺,以及港中某地段屋,某号生理,统统是姓潘的。”原原本本说来,金督一一录下。
次日,即再具一张照会,并列明某是周、潘的产业,请港督尽予抄封。港督看了,即对尹家瑶道:“昨天来的照会,本部堂已知道了。论起两国交情,本该遵办,叵耐敝国是有宪法的国,与贵国政体不同,不能乱封民产,致扰乱商场的。且另有司法衙门,宜先到桌司衙门控告,看有何证据,指出某某是周、潘两家产业,假托别名,讯实时,本部就照办去便是。”尹家瑶满想照会一到,即可成功,今听到此话,如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没得可答,只勉强再说两句请念邦交的话。港督又道:“本部堂实无此特权,恕难从命。且未经控告,便封产业,倘使贵部堂说全**都是周、潘两家产业生理,不过假托别人名字的,难道本部堂都要立刻封了,把整个**来送与贵国不成?这却使不得。请往桌衙先控他罢。”尹家瑶见此话确是有理,再无可言,只得告辞而去。正是:政体不同难照办,案情无据怎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