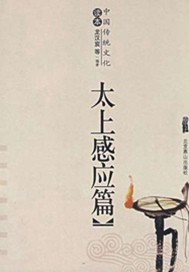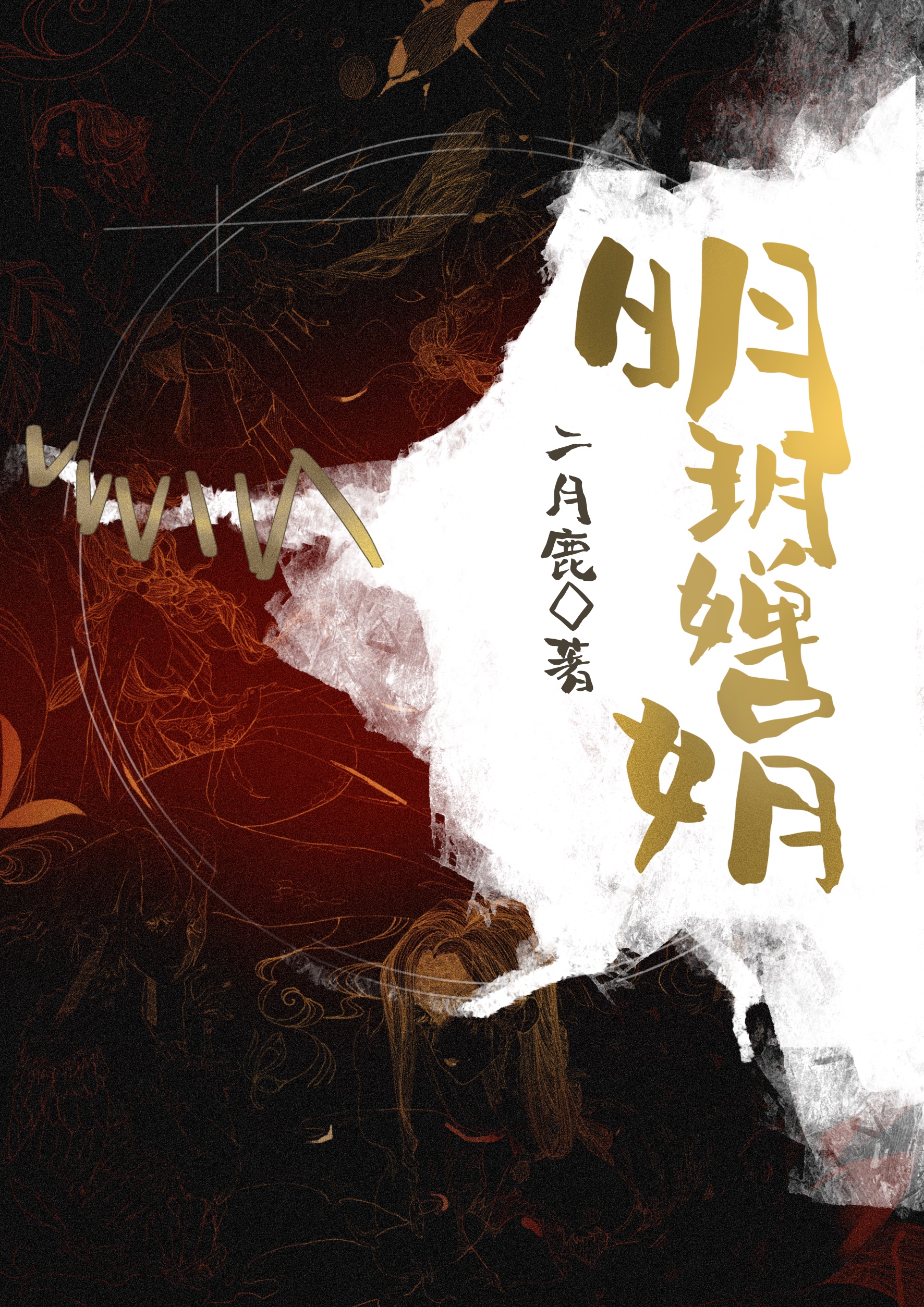话说伍姨太嘱咐了儿子之后,各人正欲与他更衣,只见他登时牙关紧闭,面儿白了,眼儿闭了。男男女女,都唤起“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声来。忽停了一会子,那伍姨太又渐渐醒转来了,神色又定了些,这分明是回光近照的时候,略开眼把众人遍视了一回,不觉眼中垂泪。香屏姨太就着梳佣与他梳了头,随又与他换过衣裳,再令丫环打盆水来,和他沐浴过了。
香屏姨太困坐得疲倦,已出大厅上坐了片时,只见八姨太银仔出来说道:“看他情景,料然是不济的了。大人又不在府里,我两个妇人没爪蟹,若有山高水低,怎样才好?”香屏道:“这是没得说了。他若是抖不过来,倒要着人到**去叫骆管家回来,好把丧事理理儿便罢。”八姨太道:“既是如此,就不如赶着打个电报过他,叫骆管家乘夜回来也好。”香屏答个“是”,就一面着人往打电报去,然后两人一同进伍氏的房子里。见他梳洗过了,衣裳换了,随把伍氏移出大堂上,儿子周应祥在榻前伺候着,动也不动。少时,见他复气喘上来,忽然喉际响了一声,眼儿反白,呜呼哀哉,敢是殁了。立即响了几声云板,府里上上下下人等,都到大堂,一齐哭起来。第一丫环小柳,正哭得泪人一般。还是仆妇李妈妈有些主见,早拉起香屏姨太来,商了丧事,先着人备办吉祥板,一面分派人往各亲朋那里报丧,购买香烛布帛各件,整整忙了一夜。次早,那管家骆子棠已由**回到了,但见门前挂白,已知伍氏死了,忙进里面问过,各件都陆续打点停妥。到出殡之期,先送枢到庄上停寄,好待周庸祐回来,然后安葬。这时因七旬未满,香屏姨太都在增沙别宅,和儿子应样一块儿居住,不在话下。
且说马氏和周庸祐在星加坡,自从国携带洋膏误了事,那心上把游埠的事,都冷淡去了,因此一同附搭轮船回港。这时听得二房伍氏殁了,在周庸祐心上,想起他剩下了个儿子,今一旦殁了,自然凄楚,只在马氏跟前,也不敢说出。在马氏心上,也像去了眼前钉刺的一般,不免有些快意,只在周庸祐跟前,转说些怜惜的话。
故此周庸祐也不当马氏是怀着歹心的,便回省城去,打点营葬了伍氏。就留长子在城里念书,并在香屏的宅子居住忙了三两天,便来**。
只自从九姨太闹出这宗事,那周庸祐也不比前时的托大,每天必到各姨太的屋子里走一遭。那日由九姨太那里,回转马氏的大宅子,面上倒有不妥的样子。马氏看了,心里倒有些诧异,就问道:“今天在外,究是有什么事,像无精打采一般?
不论什么事,该对妻子说一声儿,不该怀在肚子里去闷杀人。”周庸祐道:“也没什么事,因前儿囗记字号的梁老板,借了我十万银子,本要来办广西省江州的煤矿,他说这煤矿是很好的,现在倒有了头绪。怎奈工程太大,煤还未有出来,资本已是完了。看姓梁的本意,是要我再信信他,但工程是没有了期的,因此不大放心。”
马氏道:“大人也虑得是,只他既然是资本完了,若不是再办下去,怕眼前十万银子,总没有归还,却又怎好?不如打听他的煤矿怎地,若是靠得住的,再行打算也罢了。”周庸祐答个“是”,就转出来。
次日,马氏即唤冯少伍上来,问他:“那江州的煤矿,究竟怎么样的?你可有知得没有?”冯少伍道:“这煤矿吗,我听得好是很好的,不如我再打听打听,然后回复夫人便是。”马氏道:“这样也好,你去便来。”冯少伍答声“理会得”,就辞出。暗忖马氏这话,料然有些来历,便往找梁早田,问起江州煤矿的事,并说明马氏动问起来,好教梁早田说句实话。梁早田听了,暗忖自己办江州的煤矿,正自欲罢不能,倒不如托冯少伍在马氏跟前说好些,乘机让他们办去,即把那十万银子的欠项作为清债,岂不甚妙?便对冯少伍说得天花乱坠,又说道:“从来矿务却是天财地宝,我没福气,自愿让过别人。若是马夫人办去,料然有九分稳当的了。”
冯少伍一听,暗忖梁早田既愿退手,若马夫人肯办,自己准有个好处,不觉点头称是。急急的回去,又忖马氏为人最好是人奉承他好福气的,便对马氏说称:“梁早田因资本完了,那煤矿自愿退手。”又道:“那煤矿本来是好的很,奈姓梁的没了资本,就可惜了。”马氏道:“既然如此,他又欠我们十万银子,不如与他订明,那煤矿顶手,要回多少银子,待我们办去也好。”冯少伍道:“这自然是好的,先对大人说过,料姓梁的是没有不允了。”马氏听罢,就待周庸祐回来,对他说道:“横竖那姓梁的没有银子还过我们,不如索他把煤矿让我们办去罢。”那周庸祐向来听马氏的话,本没有不从,这会说来,又觉有理,便满口应承。随即往寻梁早田,说个明白,求他将煤矿准折。梁早田心内好不欢喜,就依原耗资本十万,照七折算计,当为七万银子,让过周家。其余尚欠周家三万银子,连利息统共五万有余,另行立单,那煤矿就当是凭他福气,必有个好处。周庸祐倒应允了,马氏就将这矿交冯少伍管理,将股份十分之一拨过冯少伍,另再增资本七万,前去采办。
矿内各工人,即依旧开采。
谁想这矿并不是好的,矿质又是不佳,整整办了数月来,总不见些矿苗出现。
一来冯少伍办矿不甚在行,二来马氏只是个妇人,懂得甚事?因此上那公司中人,就上下其手,周庸祐又向来不大理事,况都是冯少伍经手,好歹不知,只凭着公司里的人说,所以把马氏的七万银子,弄得干干净净。冯少伍只怨自己晦气,还亏承顶接办,是由周大人和梁早田说妥,本不干自己的事,只自己究不好意思,且这会折耗了资本。幸是周庸祐不懂得矿务是怎么样的,亏去资本,是自然没话好说,其中侵耗,固所不免。只究从哪里查得出,马氏心上甚是懊悔。幸周庸祐是向来有些度量的,不特不责骂,反来安慰马氏道:“俗语说‘破财是挡灾’,耗耗就罢了。
且这几万银子,纵然不拿来办矿,究从哪里向姓梁的讨回?休再说罢。”马氏道:“是了,妾每说今年气运不大好,破财是意中事,还得儿女平安,就是好的。”
次日,马氏即谓冯少伍道:“幸周大人没话说,若是别人,怕不责我们没仔细呢!”冯少伍道:“这都是周大人和夫人的好处,我们哪不知得?只今还有一件事,八月二十日,就是周大人的岳降生辰。大人做过官回来,比不同往日,怎么办法才好?”马氏道:“我险些忘却了,还亏你们懂得事。但可惜今年周大人的流年,不像往年好,祝寿一事,我不愿张煌,倒是随便也罢。”冯少汪道个“是”,便主意定了,于八月二十,只在家里寻常祝寿,也不唱戏。
只当时自周庸祐回港,那时朋友,今宵秦楼,明夜楚馆,每夜哪里有个空儿?
这时就结识得水坑口近香妓院一个妓女,唤做阿琦,年纪十七八上下,生得婀娜身材,眉如偃月,眼似流星,桃花似的面儿,樱桃似的口儿,周庸祐早把他看上了。
偏是阿琦的性子,比别人不同,看周庸祐手上有了两块钱,就是百般奉承。叵奈见周庸祐已有十来房姬妾,料回去没有怎么好处,因此周庸祐要与他脱籍,仍是左推右搪。那姓周的又不知那阿琦怎地用意,仍把一副肝胆,落在阿琦的身上去了。这会阿琦听得周庸祐是八月二十日生辰,暗忖这个机会,把些好意来过他,不怕他不来供张我。便对周庸祐说道:“明儿二十日是大人的生日,这里薄备一盏儿,好与大人祝寿,一来请同院的姊妹一醉。究竟大人愿意不愿意,妾这里才敢备办来。”
周庸祐听了,暗忖自己正满心满意要搭上阿琦,今他反来承奉我,如何不喜欢?便答道:“卿这话我感激的了,但今卿如此破费,实在过意不去,怎教周某生受?”
阿琦道:“休说这话,待大人在府里视过寿,即请来这里,妾自备办去了。”周庸祐自是欢喜。
到了二十那一日,周家自然有一番忙碌,自家人妇子祝寿后,其次就是亲戚朋友来往的不绝。到了晚上,先在府里摆寿宴请过宾客,周庸祐草草用过几杯,就对马氏说:“另有朋友在外与他祝寿,已准备酒筵相待,不好不去。”先嘱咐门上准备了轿子伺候着,随又出大堂,与众亲朋把一回盏,已是散席的时候,先送过宾客出府门去了,余外就留住三五知己,好一同往阿琦那里去。各人听得在周家饮过寿筵。又往近香娼院一醉,哪个不愿同去?将近八打钟时分,一同乘着轿子,望水坑口而来。
到了近香楼,自然由阿琦接进里面,先到厅子上坐定。周庸祐对众人说道:“马夫人说我今年命运不大好,所以这次生日,都是平常做去,府上并没有唱戏。
这会又烦阿琦这般相待,热闹得慌。还幸马夫人不知,不然,他定然是不喜欢的。”
座中如潘云卿、冯虞屏都说道:“妇人家多忌讳,也不消说,只在花天酒地,却说不去。况又乘着美人这般美意,怎好相却?”正说着,那些妓女都一队拥上来,先是阿琦向周庸祐祝寿,说些吉祥的话儿,余外各妓,都向用庸祐颂祷。周庸祐一一回发,赏封五块银子,各人称谢。少时,锣鼓喧天,笙箫彻耳。一班妓女,都一同唱曲子,或唱《汾阳祝寿》,或唱《打金枝》,不一而足。
唱罢曲子,自由阿琦肃客入席,周庸祐和各宾客自在厅子里一席,余外各姊妹和一切仆妇,都相继入席,男男女女,统共二十席。这时鬓影衣香,说不尽风流景况。阿琦先敬了周庸祐两盅,其余各妓,又上来敬周庸祐一盅。敬酒已罢,阿琦再与各宾客各姊妹把盏,各宾客又各敬周庸祐一二盅。那时节,周庸祐一来因茶前酒后,自然开怀畅饮;二来见阿琦如此美意,心已先醉了。饮了一会,觉得酩酊大醉,急令冯少伍打赏六百银子,给予阿琦。席犹未撤,只得令阿琦周旋各宾友,自己先与冯少伍乘着轿子,回府而去。正是:挥手千金来祝寿,缠头一夜博承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