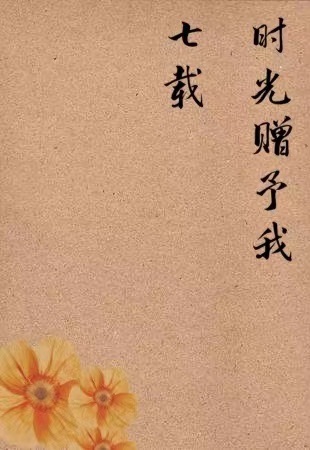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露脸,壮文他们四人已经习惯性地都睁开了眼。看看南炕,早已人去炕空。锦文一边穿衣一边说:“这几个目中无人的家伙,这么早就走了,昨天一边玩儿一边‘眉’呀‘眼’呀,其实他们凉眉淡眼的,哪像个出门人?这么大几个大活人进来,愣是假装没看见,几次想和他们打个问讯,连个机会都不给。今天这么早鬼眉六眼的溜走,也不知是干什么的。”
壮文说:“说也奇怪,我隐约觉得他们就好像是熟人,甚至连他们的说话声也好像是听过的,也不知他们是哪里人,要到哪里去。”
锦文说:“大哥,出门人可不能随便认亲,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们对人三冬寒,咱们何必三春暖,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咱干咱的!”
“那也不一定,风吹浮萍归大海,熟人何处不相逢。几百年前三生石上早就推心置腹的人,被几百年后碰上,也是有的。”壮文又说。
四人雷厉风行穿衣洗漱,草草吃喝毕,和以前没有两样,接着再上路。而我这个几百年后的人,不能再跟他们了,我得赶快回家接着写。
在鸿雁飞飞的带领下,出花如浪村向北行约八九里路,那飞飞突然减速低飞,在离地面仅二三尺高处反复盘旋,并发出咕咕的叫声。正在这时,从四面八方又飞来七八个鸿雁依次落在地上,围着飞飞拍打着翅膀跳跃着欢叫着,好像欢迎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又像告诉它什么重大的好消息似的,气氛热烈绕圈盘桓。
鸿雁们在这里停留约有一顿饭的功夫,它们就又振翅高飞向西而去。他们四人驱车紧跟,行约二里多路,那些鸿雁又低低地在一个地方盘旋,而后落地停歇,并发出咕咕的叫声,叫声此起彼伏,像在热烈讨论着什么,这是鸿雁们第二次的异常反应。
停歇了一会儿,它们又飞向高空,是那些后来的鸿雁飞在前面,飞飞跟在后面。飞飞特别关照他们四人,它和那些鸿雁在前边飞,只要和他们四人拉开一段距离,飞飞就会掉头飞回来绕一圈,然后再向前飞。它们搧动着翅膀叽叽地叫着,慢慢向北飞去。四人不解其意,又紧跟其后。虽然它们飞得很慢,四人还是跟得很紧张,因为这里并没有路,沟沟坡坡顛簸得很,大车很不好走。行约四五里路,来到一个开阔处。仍向前两次一样,那些鸿雁或低飞或盘旋,或停地鸣叫,像在和他们说着什么。四个人只顾关注鸿雁的动态,却没怎么留心这块地方究竟如何。
也没多长时间,它们又起飞了,这次是向东南飞,四人赶车再次紧跟其后。估计也有四五里,经过一座较高但坡度较缓的山又来到一处。那鸿雁又低飞慢转,而后落在地上跳跃鸣叫,留恋一个时辰后,那些鸿雁突然就聚在一块儿热烈地鸣叫,而后每只鸿雁展开双翅轮流拥抱飞飞。而飞飞也跳着叫着到每只鸿雁面前,接受它们的拥抱。拥抱完了,那些鸿雁一个一个陆续飞向高空,像有意表演似的,在他们头顶上转个圆圈,而后飞走了。飞飞抬起头一直呆呆地望着它们,只到看不见了它们,它才长长鸣叫了一声。接着它拍拍翅膀又跳了几跳,就再次飞起,绕着他们四人转了两圈,突然落在锦文肩上停下,咕咕叫了几声并又拍了拍翅膀,而后展翅向南飞去,越飞越远,渐渐看不见了。
“噫,它干什么去了?”铁锁子问。
“它走了?”壮文也问。
“它走了!”锦文看着它远去的方向,叹了一口气说,“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回去了,它和咱们同甘共苦,顶风受寒走了近半个月,现在独自一个走了。”
在这近半个月中,大家都把它看作他们中的一员,每天跟它奔波,却没有想过它是要走的。四人望着鸿雁飞走的方向,站在荒芜人烟的塞外,都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其实,禽也好,兽也好,好多动物都是有感情,甚至是有灵性的。像这只鸿雁,它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外出,要找新的安居之处?或者它是在执行谁的使命?人却不知道。人类凭着自己智商高,自古以来对动物总是伤害多爱护少。这种以强凌弱的情形,造成动物对人总怀着戒心,由于没有和动物友好相处,故对动物了解甚少。人若真正能因自己是强者,对它们多加呵护,肯定就能深切地体会到,动物的真诚善良和智慧。
天色渐暗,大家饥肠辘辘,再加鸿雁这一走,使大家的情绪突然消沉下来,只能返回那花如浪的客店。回去后壮文说:“一整天只跟着鸿雁转,那鸿雁带领所到之处,一点也未曾细看。今天累了,大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再去详细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