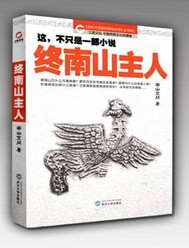过了一晌,心中略有了些头绪,韩可孤唤来正在廊下打着瞌睡的萧狗子,令他即时动身去请蔡大人速来,共商要事。
及至第二日的晌午,蔡高岭才堪堪赶到。因为不知道韩大人这边发生了什么急事,见询萧狗子时,竟是一问三不知,徒增气恼。一路匆匆赶来,驿马都换了几匹。
韩可孤把他迎进大厅落座,便亟不可待的将李福此番到来的真实意图详细告之。蔡高岭放下端在手中的茶盏,拿指头轻轻敲击面前的几案,沉思了片刻忽道:“梁王殿下本就是刘升欲攀亲的那位准女婿吧?”
“正是。”事出紧急,竟疏忽了。一经提醒,韩可孤才想到还有这桩事由。
“哼!刘升此贼野心不小,他还妄想当一当国丈哩!”蔡高岭气急败坏的说:“本来就是看中梁王的疏散性子,如果真的成了事实,他就有了名份,朝纲会名正言顺地把持到他的手中,与国又是一场大乱,金军免不了又坐享了渔人之利。”
“如今之计,高岭以为要如何做?”
“攸关国家复兴大计,唯今也只能依娘娘所托,非大人不能压制此僚。当去!而且必须要去的,宜早不宜迟!”蔡高岭的急躁性子又犯了,手拍打着案几,激动得满脸通红。
“为国为民,可孤赴汤蹈火又有何惜?只是如今这般惨淡光景,纵是去了,又何能威慑得住刘升?”韩可孤苦笑,手中少兵,腰杆不硬呀!
蔡高岭缓和下情绪,坐回到原位,长长吁出一口胸中闷气,复又低下头,一声一声地敲打起案几来。几年的同僚相知,韩可孤知道他进入了苦思冥想的状态。稍顿了有半盏茶的功夫,见还没有醒转的意思,便顾自言道:
“这几日,我也是昼夜思索。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虽然我们占了大义,但且不论兵将多寡,唯今的形势实不宜同室操戈,让金军寻了间隙乘虚而入!”
“高岭也作的如是想。”蔡高岭回过神道:“真要是带了许多兵丁前往干预,难保那厮会浑气发作,恼羞成怒起来,免不了激起一场大乱。”
“对!”韩可孤搓了搓手掌:“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如今之计,我想也只有以气势胜之了。”
“请大人明示。”蔡高岭闻弦歌而知雅意,听出韩可孤已有定计,急切地询问。
韩可孤便把这一日夜的思谋和盘托出。蔡高岭细细揣摩,又添了些主意,补足韩可孤不曾想到的漏洞。所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两个人如此这般的筹谋方定,决定宜早不宜迟,韩可孤明日即行启程前往隆圣州城,轻车简从只带萧狗子和几名亲随兵士。
“此去时日不定,这里的一应军政事务,就拜托足下了。”韩可孤郑而重之的起身向蔡高岭一揖。
急忙还礼:“请大人放心,高岭定当全力维持。”蔡高岭连声答应。
移步到大堂坐了,韩可孤将需要在这几日处理的公务一一向蔡高岭做了交代,又把自己的想法也一并传达了过去。这一顿的折腾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到了用膳的时辰。心中有了算计,人也就踏实了下来,韩可孤特意吩咐萧狗子热热的烫了一壶老酒,两个人对酌起来。眼见量浅的韩大人杯子见了底儿,平日里嗜酒如命的蔡高岭的杯中酒却只浅浅的抿出一点儿。韩可孤知道他的气性大,平日肠胃不好,便问道:
“我是为陪你才使狗儿烫的热酒,你却只在这里充样子,是又胃痛的毛病犯了吗?”
“这老病根子算是没治了。”蔡高岭笑道:“时常的就要发作一回,有时还痢下些血丝来,倒是不多。大夫不允我喝酒了哦!”指了指面前的酒盏:“闻着这味道,真是馋得慌呢!”
“让个大酒篓子戒酒,可真是难为你了。”韩可孤嘴上笑谈,眼光中却满是怜惜和关切:“难怪脸色这么难看。”赶紧招呼狗儿将酒具撤下去,免得把蔡大人的酒虫熏出来不好控制,复道:“高岭,你有王佐之才,中兴大业全倚赖着你等这般能力超群之人。为国为民,一定要珍重此身!”
蔡高岭谦逊,连连答应。
就着饭桌,二人边用餐,边又推敲商定了一些细节。
一夜无话。次日清晨,这些年的颠沛生活养成的习惯,二人早早的便起身,带着昨夜指定的几名随护,也不惊动,便一路急行,来到城外的十里亭子。虽然考虑得周详,但仍觉得前途未明,心中七上八下的,蔡高岭执着韩可孤的手,不放心地道:“刘升小人行径,无所不用其极,大人万万小心,提防这厮狗急跳墙。”
“高岭且放宽心,刘升再如何歹毒阴狠,谅也不敢将我一口吞下去。”韩可孤含笑安慰。
又相互叮咛了几句,韩可孤带着亲兵卫士启程,扬长而去。马奔出老远,遥遥的回望见蔡高岭还伫立在晨风中向着这边挥手,刚刚冒出头儿的太阳把他的头脸衣衫染得殷红。
——————
听闻韩大人单骑往了隆圣州,饶是平日以沉着冷静著称的李长风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虎狼之地岂可轻入。在此国事危难之时,韩大人倘若有个一差二错便真是塌了天了。本来就对蔡高岭在韩可孤面前偶尔表露出来的倨傲不恭有很大意见,前次相逢是见他劫里逃生,被那一路的苦难煎熬得狼狈,才压下火气没好意思即时计较。此番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自已没有阻止下来也就罢了,还没有及时通知其他的人过来规劝。李长风心中恼怒,星夜兼程赶回州政办公所在,要找寻蔡高岭问个究竟,讨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