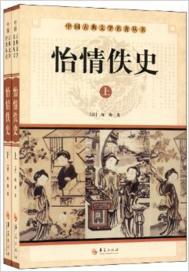童翟在门外四处张望,丝毫没注意到屋内的情况。而焰丫头站在一边,满脸疑惑,不知她在做什么,累得自己跟刚打过一场仗似的。
玞雅此刻只觉体内气血翻涌,似乎五脏六腑也要绞在了一起,不用说也知道定是受到了那股奇异气息的影响。脸色难看至极的她突然轻呼一声,挪开了手,泛白的嘴角渗出一丝血。焰丫头惊疑地扶住她:“呀!怎么吐血了?”
玞雅一怔,伸手拂去嘴角的血丝,笑道:“没事!”眯眸暗道,看来只有靠你了。反手掏出碧龙牙,合上掌心,目中射出的金光落在掌间,光芒竟暴涨了一倍不止。焰丫头忙伸臂遮住眼睛,连童翟也被这光吸引,目不转睛的看着屋里。
试过很多次却没有正式实践过,没想到这碧龙牙的能量居然大到自己无法想象。玞雅将碧龙牙推向猫狐头顶,竟像是耗费了全身的力。
淡青绿色的光洒在猫狐身上,开始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原本焦黄的毛色变回了原来的模样,只顷刻间,就已使它睁开了眼睛。玞雅笑着晕过去,喃喃道:“这次……终于救了别人。”
猫狐只是睁眼瞄了一下,又闭上了,这次却是累过头睡过去的。碧龙牙失去力量控制,瞬间黯淡,“啪”的一声落在木桌上,安安静静再无动弹。
“童翟大哥,她怎么了?这又是什么?”焰丫头一蹦一蹦的跳出去,疑惑地翻转着手里的碧龙牙。
“唉,快放回去!这是那位姑娘的东西,我不认得。”童翟挥挥手道。
焰丫头笑笑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又扶着板凳跳回去,将碧龙牙重新放回桌上。“我去弄点吃的,等她们醒了别饿着。”
“好!你小心点啊!别摔着了。”?此时的童翟是个正正常常的年轻人,明天呢?明天,这种和谐就会一扫而空吧!他原地躺下,枕着比别人粗壮几倍的手臂,默默望着天穹。朔月当空的时候,繁星都隐没了,没有谁能够胜得过圆月的光华,谁说它是淡雅的呢?这一瞬间的梦幻就像肥皂泡一样,一戳就破,脆弱得不堪一击。
小村宁静下来,这里的人们生活安定,夜里也没什么事儿,多半在家闲坐、做做一天剩下的家务,或与家人安享天伦。童翟倚在榕树干上,抱臂眺望村里那最矮的房子。
那里住着他的母亲和妻儿,她们被村长强行安排在最中间,以阻挡他们相见。
他甚至能感觉到她们在挣扎、在哭泣、在哀求能见他一面。今夜他不再想着到临村去,他怕自己会一去不回。在临村犯下的罪孽已经深深地折磨着他,也许明天,一切都会结束。
那个高明的法师会将他的灵魂永远镇封,他也无法再见到还未来得及尽孝的母亲、可爱聪颖的孩子和温柔善良的妻子了。
他站累了,半靠着小憩了一会儿,梦中全是儿时的快乐。不想自己的脸突然变成了儿子的,他刚要伸手去抓,手腕一紧,似乎被什么东西套住。
十指尖又传来每日都会有的异样感觉,他惊恐地挣扎,双眼竟变成了血红色。脸上骨骼被挤得变了形,一张血盆大口发出骇人的嘶吼,獠牙长达三寸,在血红的晨光里闪烁着耀眼的凶光,馋涎欲滴。
一方空地,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临村的请来的法师正全力束缚着他的双手。童翟的意识慢慢消失,只留下想要杀光所有人的念头。他狂吼着,披头散发的疯狂模样使离得近的人惊惧地退后。
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三个熟悉的身影,他猛一清醒,忘记了挣扎。法师找准机会蓦地发力,一根闪耀着蓝光的冰刺“嗖”的钉进他右手腕处。他吃痛全力挣扎,奈何那绳索就像长在他身上一般。
接着一针刺如肩井,又是一声凄厉的哀嚎。沸腾的人们被震慑住,悲愤声渐消,有的看不下去纷纷转过头。忽闻一个苍老的哭声从人群中爆发出去:
“儿啊!我的儿啊……你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儿啊……”
这一声使得人人侧目,有人道:“大娘怎么来了?这种场面万一吓坏了怎么办?丫头,快带大娘回去!”旁边童翟的妻子死活不肯,只死死盯着台上被绑的丈夫不住地垂泪。
童翟被巨痛刺得稍稍清醒,抬起模糊的视线,口齿不清地道:“母……亲!”身上不知被刺了多少针,只觉力气在飞速流逝着。那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在体内疯狂地奔走,朦胧中似乎有人建议烧死他。
也好!死了就解脱了,就不用再遭罪了,老天待他不薄,临死前还能看到家人,这就够了。妻子会替他照顾好母亲的,儿子年纪还小,不懂事,若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曾是杀人狂,一定会恨他吧!
“住手!何刀莫,你在做什么?”风风火火的白色身影情急之下竟腾空跃上高台,怒气冲冲地挥开即将飞射向童翟的冰刺,大声质问。
何刀莫一个踉跄,惊讶道:“玞雅姑娘!你……你怎么……”
经过一夜的休整,元气稍复的玞雅脸上尤自苍白如纸。当她看到童翟的模样后着实吓了一跳,也终于明白为何村民们都要赶他走。转念一想,这人好心来搭救自己,又收留了瘸腿的焰丫头,断然不会泯灭良知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他变成这样,虽不知其因,但终究该先救下这条命。是以不顾一切跳出来阻止,没曾想这被村民请来的法师居然是老相识何刀莫,这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怎么在这儿?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他是个好人!你用什么刺的他!给我放了他,快!”玞雅拽着何刀莫的衣襟嘶声道。
“这……可是,村民们说……”
“说,说什么?说他是杀人狂魔?你亲眼看见的吗?一个杀人狂可能收养瘸腿的孤女,可能从蟒蛇手里将我救出来吗?你怎么能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辞啊?”玞雅急怒之下有些不讲道理。
下面村民也怒了:“哎你这人还讲不讲理!我们每个人都亲眼看见他发狂杀人的,难道我们都瞎了不成?”
“对啊!这妖女一定跟他是一伙的,你们看她一直都在为那魔头说话啊!”
“他们都是妖孽,要烧死他们……”
“对!烧死他们!烧死他们……”
焰丫头吓得流泪,一蹦一蹦地拨开人群,挤到高台边上,使劲往上爬。一团火红在她肩头有些躁动不安,左瞳竟隐隐透出血红的光,闪烁不定。
站稳了身子,她过去拉住玞雅:“先别激动!村民们的话没错……我们赶紧救大哥下来,其他的回去再说!”
玞雅望了一眼直欲冲上来的人们,瞪了一眼何刀莫,闷闷道:“哼!改天再找你算帐!”转身刚要帮忙解绳子,却见那猫狐瞪着那血红的左眼,悬在空中躬起身子,像一支上足了劲的弓。前爪已尽数伸了出来,目标居然直指焰丫头。
暗呼一声,玞雅感觉到异样,只够伸臂挡住猫狐的利爪,一阵钻心的痛犹如侵入骨髓一般。她猛甩开咬住她的猫狐,忍痛撕下群摆,紧紧系住伤口以上的经脉。再看时那猫狐却像丝毫不觉,在人群中上蹿下蹿,吓跑了一半也抓伤了不少。
经过这一变故,村民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现场已无一活口。玞雅瞧得心惊,直欲作呕,扶起虚弱的童翟忙说要离开。何刀莫傻愣了半晌,也伸手帮忙。猫狐似乎也安静下来,只蹲在地上看着玞雅,一动不动。
刚下台阶,玞雅费力道:“呀!这是童翟……的母亲!”
话音刚落,腿一软便往一边歪去。
“玞雅!”只听一声惊呼,一个人影急掠过去堪堪抱住倒下的玞雅。此刻怀中的人已经脸现乌青,惊讶地瞪大眼睛。
“你……还没走?”
那人急切地抓起她受伤的臂,就要往唇边放。玞雅意识还在,知道他要做什么,用尽力气夺回来:“不!你会死的!”
这毒太厉害,从她脸上便能看出来,若不及时施救恐怕就难以活命。他咬咬牙,正色道:“听我这一次!我是带毒之身,本就不怕毒的,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玞雅再没力气挣扎,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急得泪流满面却无力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口又一口地替她吸出毒血,直到重新流出红色的血。
猫狐在一旁冷冷看着这一切,突然仰天嘶叫一声,一红一紫两只眼透出杀人般的冷芒。它伸出尖刀般的爪子在地上刨了刨,嘴里一直呜呜作响。
何刀莫放开童翟,急奔过来,不知所措,却意外地问出了众人都来不及关注的问题:“怎么会这样?这只猫狐哪里来的?”
无奈没人有心情回答他,每个清醒的人都焦急地望着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男人。
不一会儿,男人欣慰地抬起头,擦擦嘴角的血,闭眼运气从喉中吐出一个淡金色光芒的圆球。那球卜一出现,便没入玞雅体内,再无动静。
男人脱力般顿地,面含微笑凝视玞雅,对他人的问候聪耳不闻。
“你!给了我什么?”玞雅面上乌青褪去,惊恐地抓住男人,嗫嚅道:“不会是……内丹吧!”
男人已无力气动弹,只是点点头。
玞雅一怔,泫然泣道:“不!你拿回去!我不要!你拿回去!我不要你的施舍!你不要命了啊!你……”
“我说过要跟着你,既然你不愿,那我只好换一种方式,你不接受也好,就当是欠我的。只要你一辈子记得我,就够了!来世……再找你讨回来!”
“不!你这个傻子!傻子……”玞雅使劲摇晃男人的身体,手心突然一空,再一看,腕上多了一条细小的蛇形手镯。她惊讶地试着脱下来,却偏偏像是天生长在上面一样,无法取下。也罢!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吧。只是没想到这条毒蛇会连内丹都献出来,一个人人惧怕的毒物竟会痴情至此,恐是众人都没想到的吧。
几人都默默无话,埋头回了茅草屋,何刀莫见玞雅连遭打击,心情郁闷悲痛。又听焰丫头讲明了原由,于是动手施救,只求能早些治好何刀莫,缓和一下悲伤的情绪。
原来几年前,村里来了几个人,说是要招募青壮年为圣廷培养新一代的守护者。只需两年,若是考核通过,可以留在圣廷任职,而未通过的也可以遣送回家,并发下大量的抚恤金。
于是,村里的男人在得到第一笔款子之后,高兴地上路了。两年后,回来了一大半,却只有一两个被留下了。所幸的是人人都带回了丰厚的物资,全村为他们的归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可是第二天一早,就发生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惨祸。
村里刚回来的男人们突然之间全部变成了一种模样,身上骨骼像发狂似的暴涨,凭空比以前高大了不少,看上去倒像怪物。眼睛血红,见人就咬,那一天,村里死了一半的人。
“后来呢?后来那些男人都去哪里了?”
“后来……村里来了一个戴面具的男人,他说,他没有法子治好这些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杀止杀。”说到这里,焰丫头微微颤抖了一下,似乎还在为当时的情形害怕。
“以杀止杀?”叨莫皱眉道。
“戴面具?那是杜覃铎了,除了他,还有谁能杀光所有发狂的巨人。呀!你说的那些人是不是就和童翟刚才……”玞雅突然捂住嘴,惊讶道。
“不错!他们就是和童翟现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