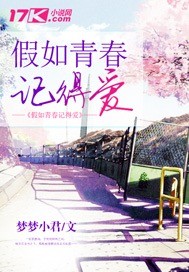“哎”,凌菲叹口气,“你和黄大哥还挺恩爱的,可惜黄大哥走的早,珍姐,黄大哥是为什么牺牲的啊?”
珍姐的伤心事被勾起,她放下首饰,回忆起往事,“你黄大哥是好人呐,他是替别人死的。”
“替别人死的?”
“嗯”,珍姐扬着眉点点头,“陆站长应该对你说过,他在北方待过一段时间,我家老黄从南京跟过去,也就在那里,我经人介绍认识了老黄,而后我俩成了亲。”
陆地并未对凌菲讲过他的过往,凌菲见珍姐像要说出什么似的,附和道:“是啊,这事陆地倒说过,所以我们才能够吃到一起嘛。”
珍姐道:“你说的对,咱们北方的姑娘往往喜欢北方的汉子,再怎么着,也要接受我们的饮食习惯。我娘家算是个富足的小户人家,我结婚前从未吃过苦,所以不知天高地厚,没有意识到他的工作性质特殊又危险,我和他的情份转瞬即逝了,结婚没多久就阴阳相隔。”
“黄大哥到底怎么牺牲的?是共产党的人陷害他?”
“和共产党没有关系。”
珍姐简单的回应道,忽然停住了话语,凌菲看出了她的迟疑。
珍姐沉默着想了又想,当年陆地可怜她年纪轻轻就守寡,所以才将她丈夫真正的死因告诉她,珍姐清楚,陆地这么做可是违反了纪律的,她做大嘴巴再扩音出去,对陆地好吗。
凌菲也不作声,从水果盆里拿出一只苹果,咬上一口道:“珍姐,这苹果不错,又脆又甜。”
珍姐见凌菲顾左右而言他,料想她不开心了,陪笑道:“妹妹,姐姐有难言之隐,你不会怪姐姐吧。”
凌菲装作无所谓的摆摆手里的苹果,“怎么会怪姐姐呢,姐姐有些话藏在心里不想告诉我,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不就是生气了吗。
珍姐害怕与凌菲闹翻,一咬牙说道:“多大点事啊,你看我搞得跟国家机密似的,妹妹又不是外人,理应知道你大哥去世的原因的,但妹妹得答应姐姐,千万别告诉陆站长,我可是在他面前发过毒誓,保证不向外透露一个字的。如果他知道我告诉了旁人,说不定会把我从这房子里轰出去,那我就要露宿街头了。”
凌菲笑道:“姐姐言重了吧,这么神秘,那你还是别说了,免得你心里留着疙瘩。再说我怎么会告诉陆地呢,女人家之间的闺房话,我对他说干什么。”
珍姐拍拍凌菲的手,“姐姐错了,错了,那还是去年夏天的事了……”
她突然中断了说话,警惕的察觉到有人从门缝里闪进来。
“是谁呀?”珍姐扯开嗓子问。
“夫人,是我,玲儿。”
珍姐吁了口气,“菜买好了啊?”
“买了,猪肉、芹菜、面粉都买了”,玲儿把菜放进厨房,走过来说道。她望见凌菲,朝凌菲笑,“周小姐,你来了。”
珍姐道:“别的事你先别忙活了,现在去街上买一盆茶梅回来,摆在这会客厅的窗台上,我昨天还惦记买一盆呢,转念就忘记了。”
“好的,夫人。”
支走了玲儿,珍姐锁上会客厅的门,问道:“哟,我刚说到哪了?”
“你说那还是去年夏天的事。”
“对,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家老黄和陆站长一同去枣城买汽油。”
凌菲几乎喊出了声,“枣城?”
珍姐吓一跳,弱弱的应着,“对,是枣城,妹妹你……”
凌菲清咳了几声,尴尬的笑,“不好意思,我在枣城长大的,兀然听到你说枣城,激动了些。”
“噢,妹妹在枣城长大的,那你可知道枣城有个姓林的富商,叫林,林什么的,对,叫林祥雨。”
凌菲能感觉到身体在筛糠似的发抖,她默念着强迫自己,凌菲你要冷静,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她抬起发红的眼睛望向珍姐,珍姐正在自言自语的解释她之所以记住林祥雨这个名字的原因,“老黄的表哥也叫祥雨,你说巧不巧。”
“妹妹,我记得你之前的丈夫也姓林,不会和林祥雨是亲戚吧。”
凌菲的舌头不听使唤的打结,她努力把话说清楚,“枣城那么大,姓林的哪能都是亲戚,我前夫家是卖山货的,卖卖红枣、核桃什么的,没有做汽油生意的亲戚,珍姐,你,你接着说啊。”
“哎,当时陆站长还是少校,他打听到枣城有个做汽油生意的林家,于是便约林祥雨出来谈汽油买卖的事。当时林祥雨是带着他的儿子去的,两人到了约好的地点后,陆站长不在,他的手下正捧着一份电报站在房间里等他,后来又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陆站长进去的时候,电报到了林祥雨的儿子手上,林祥雨和他的手下在抽雪茄。那不是一份寻常的电报,涉及到重要的机密,陆站长立即问他的手下在干什么,那孩子说林老板请他抽根雪茄,他就麻烦林少爷帮他拿一下电报。”
珍姐的声音变得沙哑,“你知道那孩子是谁吗,他是老黄的亲侄子,叫成才,但陆站长不确定成才说的是否是真的,不确定林祥雨和他的儿子没有看过电报,做他们这工作的,疑心很重,宁可错杀十个,不愿放过一个,他向上级请示之后,决定秘密把他们三人处决了。”
“处决?”凌菲瘫软在沙发里无法动弹。
“是处决,我们老黄知道后,他就求陆站长放过成才,我和老黄没有孩子,成才的父亲早已经走了,只留下他这个唯一的儿子,成才是黄家的命啊。但陆站长行事向来果断,他决定了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老黄自知求他无望,花重金买通狱警,偷偷的放跑了成才,自己却当了替死鬼。”
珍姐垂下头低声呜咽, 凌菲抹了把眼泪,问道:“林祥雨和他的儿子就这样死了?他们是商人啊,陆地连商人也不放过。”
“我想那林祥雨的儿子也许不懂政治,商人的儿子,大多也是从商的,他根本没有料到帮忙拿份文件会招来带来杀身之祸吧。但话又说回来,也许他俩果真是共产党呢,这年头的人,谁搞的清楚谁啊。”
凌菲失去理智,发了疯似的吼道:“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无辜的!陆地,他,他是个魔鬼!”
珍姐抽了抽鼻子,笑道:“瞧瞧,我干了什么好事,说着说着竟哭起来了,还让你对陆站长产生了误会,我从来都没怪过陆站长,老黄私自放走了成才,本就是杀头之罪,可陆站长好人啊,把这件事担了下来,对外称老黄是功臣,我才得以有颜面苟活在这世上。我只怪我们家老黄狠心抛下我一个人,自个跑到那边享福去了。”
凌菲的泪水哗哗的往下流。
“妹妹,妹妹,你怎么也哭上了。”
犹如万箭穿心,疼的凌菲咬牙切齿,她忍着那快压垮神经的痛楚,失落的回过神,“我,我在替珍姐感到伤心呢。”
“不伤心,不伤心,这日子还得好好的往下过呢,你坐着,我去给你煮杯咖啡。”
“嗯。”
珍姐离开后,留下凌菲一个人在沙发上静静的哭着笑着,她拼命锤打胸口,无声的嚎啕大哭,哭的撕心裂肺,他死了!他死了!梓慕死了!
天花板在眼前眩晕似的晃动,眼泪淌进胃里,恶心的她翻江倒海,发出“喔喔”的干呕声,梓慕你已经死了啊!
梓慕你已经死了啊!
门口传来脚步声,凌菲忙掏出手帕,把整张脸蒙进去擦了又擦。进来的是玲儿,她招呼身后的男子道:“卖花的,把茶梅放到这窗台上。”
又调过脸关切的问凌菲:“周小姐,你的眼睛怎么肿了?你哭了?”
凌菲打了个喷嚏,道:“不是,我感觉身子有点冷,像是感冒了。”
玲儿会意的笑道:“周小姐在暖和的地方待惯了,不习惯我们这屋子的阴冷,我去给你灌个汤婆子。”
凌菲迫不及待的打发她走开,“好呀,好呀。”
搬花的男子听闻凌菲的声音,惊喜的叫道:“沂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凌菲勉强瞟了一眼他,是阿乔,好巧。
她冷冷的打了个招呼,“噢,阿乔,你好。”
阿乔见到她格外兴奋,喋喋不休的说道:“沂小姐,我听说了,你要做站长夫人了,恭喜你啊,上次我误以为你和周少爷结婚了呢,对不起啊。”
“没有关系的。”
“原来之前陪你去买花的是陆站长,国民党的中校啊,真是了不起,我差点把他当成了你的佣人。要不是他回头去找我,我还不知道你和他的事呢。”
“他又去找你了?他问你什么了?”
“他就问了一些你在枣城的事情,说是为了多了解你,问我你的前夫姓什么?”
“你怎么说的?”
“我实话实说啊,说姓林。”
“他还问了什么?”
“问林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
凌菲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她急促的问:“你如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