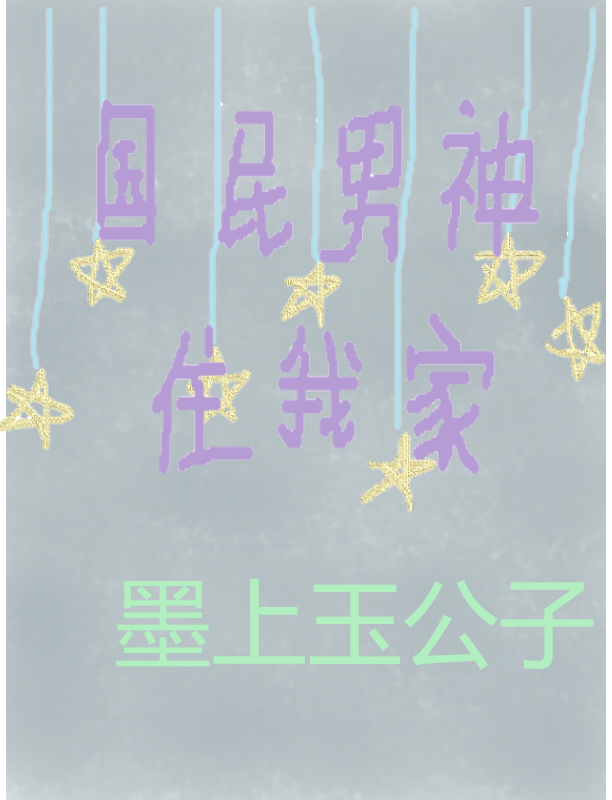秋竹跟着孙太医回太医局拿药,一路上孙太医与她闲聊几句:“我瞧刚刚那个丫头不像是一般的宫女,品级很高的样子,莫不是懿妃娘娘身边新晋的女官?”。
“大人是说季姑娘啊,她哪里是什么宫婢女官,人家可是季家的二小姐呢”孙太医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随口说了句:“怪不得”。
再说话时,二人已经到了太医局,经过一夜的折腾,此时已是卯时,曙光已经照亮了天空的一角,睡意早已消散。
孙太医一边安方子抓药,一边对秋竹说:“你拿回去熬吧,太医局这里的瓦罐不多了”顿了顿,又补充道:“前些日子瓦罐都被薛美人用了,还未刷净,那安胎药和止血药是万万不能同用的,否则是要引起血崩的”。
秋竹躬身施礼,孙太医这话秋竹是打左耳朵听右耳朵便冒了出去,他想不过是太医随意挂在口上的无心之谈,不足以令她记在心里当一码事,眼巴儿前就想着赶紧提药回去熬制成汤,也好让皇三子服下,病伤早日痊愈。
脚下是一刻也不敢耽搁,于是焦急的和太医道了一声:“多谢大人,奴婢先告退”未等孙太医再与她交代几句时,便急匆匆的没了身影。
秋竹刚走,又见一小宫女入太医局内,微微含笑,柔声道:“不知董太医可在?”。
太医局内唯有孙太医一人在低头整理案板上的医书,见有人入内,便开口回她:“董太医恰逢南江人,今日告休回去探亲了,不知姑娘是哪宫的?”。
小宫女毕恭毕敬地应声回答:“奴婢乃长春宫宫女,奉荣昭仪之命来取进补的汤药”原是春娆打发她来取荣昭仪的汤药,自荣昭仪小产失子后,便寻了万般的汤药,只为了让自己一举得子,而这董太医因为是妇科圣手,便也成了荣昭仪的心腹,时常去宫外找些偏方呈给荣昭仪,虽说用处不大,但是深得荣昭仪的信任。
一时间长春宫的事宜,旁人也无法再插手,按说董太医与孙太医官职同级,可是各人有命,人家董太医掌管一宫主位的膳食健康,而他孙太医只能沦落侍疾顾暇一些不得宠的小主,谁人不想攀附高枝,可是也得由机会让他攀附。
长春宫的宫女听闻董太医不在,只好折返而去,而这时孙太医思索了一番,机会不就摆在眼前了么,只要他能乘机抓住机会,那来日,在这太医局里他再也不是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太医,也不用辗转在各个小主面前。
他们孙氏一族祖上世代为医,只有他这一支得了进宫的机会,他阿爹临死时也不忘与他喋喋不休:“一定要出人头地发扬我孙氏一族啊”他时刻不敢忘记父亲的临终委托,再加上心里也不服气,凭什么董太医可以出入长春宫,他丢弃手中翻开的医书,抬头叫住小宫女:“且慢,姑娘”。
顺手写了一张字条,放入信封中,又用火漆封缄,递给小宫女:“姑娘请帮我将这个交到昭仪娘娘手中”,从腰间拿出了一些碎银子一并塞到了小宫女手中。
小宫女见这情形,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好吧”小宫女哑口无言,岂是她不想帮忙,实在是自己没有这个权利,她不过是个杂役宫女,连她自己都没有机会面见荣昭仪,更何谈帮孙太医递封信件。
孙太医见她犹犹豫豫的,便叫她到身前近一些,又掏了些碎银子塞到她手心里:“姑娘也不用太为难,只要递到娘娘跟前就好,事成了我不会亏待你”。
小宫女也是左右难为,毕竟孙太医给了她好处,于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他,小宫女倒也算是机灵,不忘和孙太医说道:“大人也得有个心里准备,奴婢未必能办利索了”。
孙太医言语之间露着感激之情:“多谢姑娘”。
小宫女回到长春宫思来想去,只得将事情原原本本的与春娆说了一通,信是交到了她手中,但是关于孙太医给自己的好处,却只字未提。
这日夜里,季子棠挥散了江孝珩身边伺候的人:“都回去休息吧,今夜我陪着主子”。
秋竹与她推辞:“还是我来吧,你瞧你的脸色这么差,总是熬着,身体会吃不消的”。
“秋竹姐姐不是也说了么,难得他回来一趟,怎么还要和我抢这个机会呢”秋竹自然不能再说什么,只是叮嘱她:“若是夜里主子这里有情况,你就来喊我”。
季子棠朝她摆摆手:“去睡个安稳觉吧”秋竹向来睡觉浅,偶有一丁点的动静便再也不得入睡,很多在宫里生活过得宫婢奴才都是这样,总要提着一个精气神儿,生怕主子突然有事喊不到人,于是深了不敢睡,浅了睡不着,到头来各个都落一个睡觉困难的症状。
她呆呆的依靠在床榻旁,静悄悄的盯着江孝珩时不时的替他掖着被角,生怕夜里再受了寒气,可不知过了多久自己竟然打起了瞌睡,脑袋如拨浪鼓般点头频频。
季子棠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说不上来是美梦还是糟糕的梦,只是记得梦里见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熟悉的,自然也有未曾相见过得陌生人,大家围坐一团欢歌笑语,唯有她不知怎么了竟然滴滴落泪,说不出的心酸,可也绞的她心口犯疼。
大概是被疼醒的,次日一早睁眼,发现自己虚汗不断,却也不忘先瞧瞧江孝珩高热是否退尽,秋竹端着熬好的汤药走进来,声音低沉的询问她:“主子,如何了?”。
“高热是退了,就是不见醒来”江孝珩迷迷糊糊的听见有说话的声音,缓缓睁开眼。
“醒了,怕是我俩说话的声音扰着主子了”季子棠扶他起身:“先把药喝下,然后再进点食”吹了吹汤药,中草药味道十足,她舀了一汤匙喂到江孝珩嘴边:“趁热喝,药效才最好”。
江孝珩伸手接过她手中的碗,闷着气一口饮下,他自小就服用各种汤药,早就习惯了,无需她这样口口相喂,模样矫情的像个小娘子。
用过早膳,季子棠继续摆弄昨日的绣工,而江孝珩却在案前低头看书,期间懿妃差人来瞧过,见他已无大事便只带话让其好好休息,珍嫔与许才人虽然人没来,可是也吩咐了下人送来了人参、灵芝这样进补的上等药材。
因为并非在京中皇宫,此次随行也只是带了一支半根,但是赏赐的并不多。
倒是皇帝,自始至终未曾来瞧过皇三子,长生殿的人早已习以为常,皇帝向来不过问他的事情,只不过,儿子受了伤却也不提不问,难免让人感到心寒。
季子棠本以为事情已经了结,谁知四喜前来,说皇帝要召见江孝珩,季子棠放下手头的东西,修整仪容,可四喜却告诉她:“陛下只单见皇三子一人,姑娘不必跟着”季子棠与江孝珩面面相觑。
“四喜公公可否门外稍等片刻?”四喜应声,只是说了一句:“姑娘切快些,陛下等的急”。
季子棠拉着江孝珩到里间,嘱咐了他几句:“见到皇上时,且要知礼数,不可惹他不快”江孝珩点头应下,一路跟着四喜,由他引着进了内殿。
江孝珩一入内殿,侍奉在皇上身边的宫人自觉屏退,他礼数周到的给皇帝行了个君臣礼:“儿臣给父皇请安”。
“听宫人说你受了伤,又发了高热,可还好?”。
“儿臣无碍”说罢,将京中情况逐一和皇帝禀告,皇帝所听之处,并没有显现出气愤之态,反倒异常的平静,不容江孝珩与他说,其中事由早已有所耳闻,若不是闲话传的久了,想必他耳朵根儿还是清净的,江孝珩这番言语不过是证实了,朝中的确有人暗箱操作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各个提着一副好皮囊,殊不知私底下肮脏的事不尽其数,不过皇帝倒是先听听看江孝珩对此事有何态度:“你觉得该如何处理?”
“找出最大的源头杀一儆百给前朝百官看,随后将其他参与者连根拔起”皇帝不曾发现江孝珩性子竟然如此凶狠,其手段倒是遗传他几分,不过凭他想,左不过就是让衙门下去些人给他们找些绊子,时日久了,各生意做不下去自然就关门歇业,或许是他年事已高,手腕和决断远不比从前,没成想他的这个儿子远在他之上。
“如果差你去办,你可担的起?”江孝珩明白,皇上这是要重用他了,他沉浮了这么久,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再仔细一想,他却犹豫三分。
皇上不难看出他的心思:“朕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为解他所有顾虑,其实皇上早已有所打算:“朕会以你此次玩闹受伤之由降罪与你”说是降罪,倒不如换个说法,是给众人一个交代,会提前逐他出宫自立府门,为他招兵买马,让他私下操办这些事情。
实则表面上他还可以做一个游手好闲不得宠的皇子,而埋头修炼自然是不为人知的事情,一来前朝百官还当他若有若无,大家也不会顾忌他三分。
二来皇帝心知,太子并非君王命,皇四子担不起国家重担,唯有江孝珩还是可用之人,只等他一朝一夕慢慢达成所望。
皇帝既然已经有了周全打算,江孝珩自然只能照他意思去做。
“儿臣明白了”。
皇帝突然想起一个人,虽说不能为他所用,但是至少能在身边照顾周全他:“朕看季家那个小女儿在你身边待的不错,就指给你,他日和你一同出宫,至于名分,暂且不论”。
江孝珩谢过皇帝后,全身而退。
很快江孝珩出宫建府的消息就在大行宫传遍了,季子棠听闻后,倒是欢喜了良久,幻想着出宫的种种美好之态,一想到自己马上就可以不用日日在宫里被束缚,就欢欣雀跃。
倒是秋竹有些暗伤:“真羡慕你,要是我也能跟着出宫该多好”她自小就被卖进宫里侍奉主子,如今双八年纪,早已称得是“宫中老人”,距离她年满出宫还有近十载的光阴岁月。
十年并不容易熬,只盼着日子能快一些,她想出宫的念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她就想看看如今京中的繁华光景,而不是每每只能听季子棠的描绘,然后在字里行间的话语中自己勾画幻想。
“你想出宫?难不成是想嫁人了?”秋竹脸上泛起羞涩:“哪有女子不想成亲嫁人的?”。
季子棠便不想,她早就为自己设想好了往后的日子,若是能和这个九重天撇清关系,她就干脆带着檀栀,找一处风景优美,却了无人烟的地方,种一片桃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源涌银浪笑春风,堪比世外桃源般。
整日弹琴书画,闲来拨花弄草,直至终老,云游四海的日子,何其逍遥快活,怪不得少时锦堂总说她没有半点女儿身姿,活脱脱一个野小子,若是生的男儿身,自然没什么不妥,偏偏是个女儿身,丢不掉的规矩礼仪和男尊女卑。
“倒不如,我向三皇子请了愿,到时带你一同出宫,反正来日府里需要人手,你又伺候他这么多年”其实季子棠也是想有个知心的人伴着她。
说起秋竹的为人,季子棠倒是赞叹不停,长生殿里伺候江孝珩的人不多也不少,却只有秋竹和她脾性相近,十分投缘。
又碍着秋竹稍长季子棠几岁,自然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多少还需要秋竹指点一二。
要是换作旁人,整日里各自安生,绝不会深交亲近,也不顾得听她说尖酸辛苦和早水晚粥的过往经历。
“我自小就入宫为奴,只盼着年芳二五时出宫安家得子,怕是连这点期盼也是遥遥无期的,哪里还妄想着跟着主子一道出宫”。
她这样说也是情理之中,宫中年满出宫的,若不是伺候不当惹主子不悦,便是平级低下,向她这样做事麻利,又得主子顺用的,自然不能轻易放她出宫,北四所掌事姑姑便是头例。
季子棠记得从前得了闲和她聊天时才知晓,家里当日已为她定下亲事,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是男方为人老实,就是身上有一点残疾,倒不碍着二人过日子。
日子虽然清贫一点,但至少没有勾心斗角,姑姑自己自然是满心期盼,想着自己黄花半老,还能婚嫁,也算是上天待她不薄,可到头来,内侍省却没有在名单上提笔她的名字,只因为她办事能力强,为此不仅晋了她的等级,又将北四所交给她掌管。
最终所有的盘算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念想没了,好好的姻缘也与她错过了,换来的是一个须有的官衔职位和深宫的围困。
季子棠只记得掌事姑姑和她说过一句,最让她难忘的话:“后半辈子,就是死也只能死在宫里了”。
秋竹的后怕,也是于此,她见过太多品级高的姑姑,年纪轻轻的日日劳作,搞的自己身体慢慢垮掉,到老时只能得了主子恩赏,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宫里“熬”日子,说来也是万般无奈。
日子过成了,将死之状,可就算这样也比不过冷宫里的女人们,至少她们曾经也拥过男人,可是很多姑姑,怕是到死了也是黄花老姑娘处子之身,何其悲凉。
这感觉就如同白走世上一遭,还不如投胎转世成一畜生,吃吃睡睡,就算被人宰割了,也不至于留有遗憾。
秋竹深知若想出宫再领略一番京中景象只能成为庸闲之辈,可那样连保全自己也成了枉笑,如果既想保全自己又想出宫,却成了左右为难的事情,所以说世间万事岂能安于人心。
季子棠宽慰她:“莫不是如今连我也不信了?”。
秋竹多想告诫她,宫里向来没有信任二字,看重的只有权位,得权者才是得天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