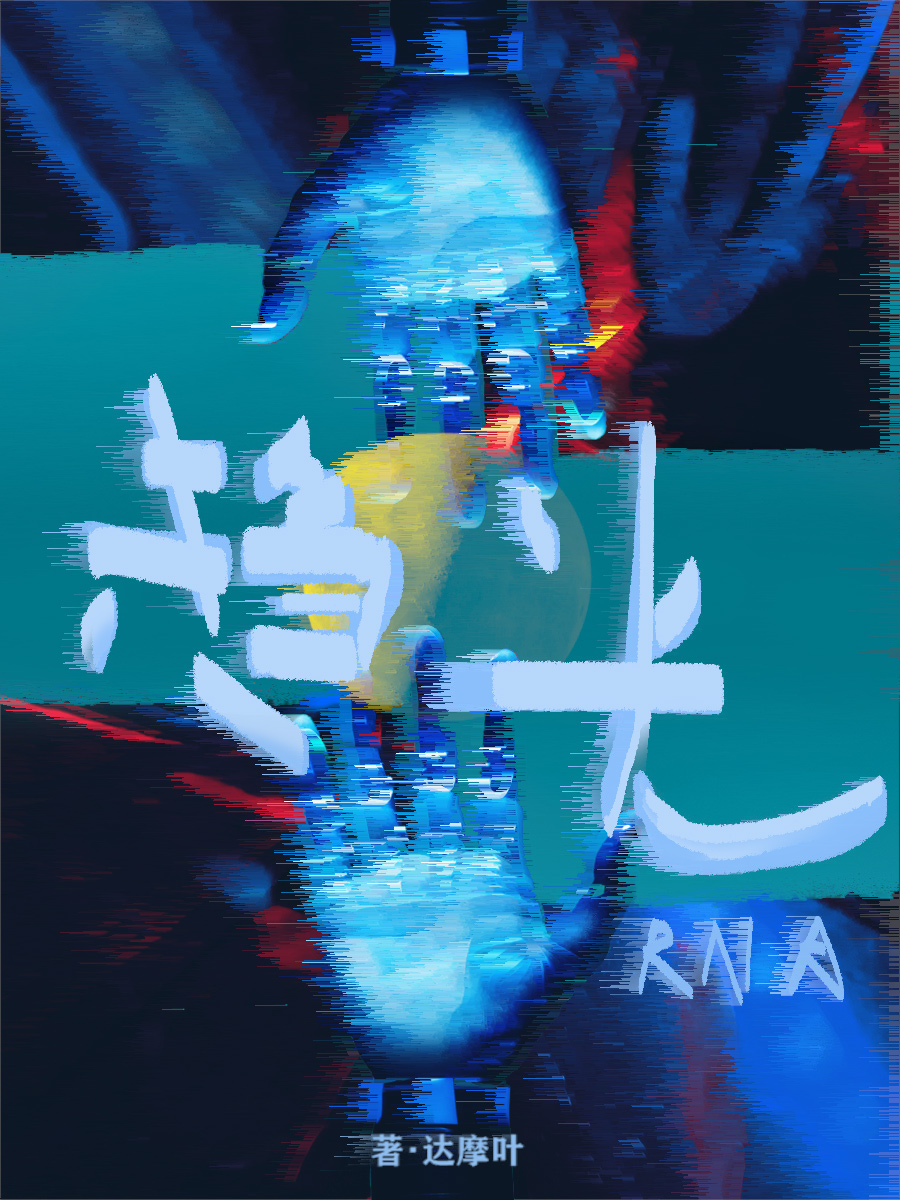我心里沉了一下,虽然我是一个暴力而没有同情心的女人,但我还没有恶毒到真的希望别人被活活打死的地步。一时间,我忘记了隐藏自己,直接站到了巷子口,随后我看到了他,看到那个自找苦吃的傻逼。
他软绵绵地靠坐在墙边,软得像一张鸡蛋饼,他的身上全是血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还没死。因为他看着我,那双眼睛像黑曜石一样,仿佛带有特殊的光泽,在对上他的眼神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自己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因此我很快挪开了目光。
但是我已经逃不掉了,因为那些混混看见了我,他们说:“哟,这小妞是谁啊!”
这一刻,我真希望自己长得跟如花一样,那才足以把他们吓跑。
“既然被你看到了,就不能让你轻易回去了!”其中一个混混说。
“小妞,虽然胸不大,但至少还算苗条,怎么,给我们爽爽不?”
我觉得自己才是一个傻逼,为了看另一个傻逼而将自己卷入了危险中去。
我也算是练过一点武术的人,但是对上这么多混混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一点胜算,只听哐地一声响,一个板砖砸在我头上,接着是火辣辣的疼,然后我感觉到有一个大脚丫子踹在了我的背上,另外有噼里啪啦雨点一样的攻击落在我身上……
在失去意识之前,我所想的是: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睁开眼睛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头上缠着纱布,一扭头,脑袋钝钝地疼。我费力地坐起身,看到躺在旁边的人,不由感慨——真是冤家路窄啊!为什么又是这个傻逼?不过,看到他浑身缠满绷带的样子,还是挺爽的!
医院里很静,一股消毒水的味道,一个护士经过,见我醒了,进来叽里咕噜说了一堆话,可我一句都没听懂。
“Can you speak Chinese?”
“No!”然后又是一大堆话,这回我听出来了,她说的是英语,可惜实在不太标准。
“你说韩语或者日语得了!”我用英文吼道,她愣了一下,竟然真的说起日本语,还好我学过一些日语,大致听懂了——反正就是让我好好休息,别乱跑的意思。
护士离开后,我左右张望,出门时随身带的包早已不见了,手机稍微裂了点,放在病床边上。我坐直了身子,拿起手机,一按亮屏幕,就看到许多未读信息。
是柳泉的,我在把他的号码存作了“紧急联系人”,所以把我送到医院来的人就拨打了他的电话。柳泉说他已经和医院联系过,我没有什么大碍,他今晚会过来看我,要我好好休息。
头还在疼,我估摸着这会儿再躺下估计也睡不着。也许是第一次被人打进医院的关系,我竟有些隐隐的兴奋。我侧头,看着躺在不远处的……呃,我不清楚现在是不是还要叫他傻逼,因为我做的事并不比他聪明到哪里去。如果走到病房门口的话,应该能看见名牌,不过我现在并没有那个力气。
他躺着的样子可比他站着的样子可爱多了,现在看起来,那张脸不像之前那样可气,甚至显得俊俏起来,说不定还挺招女孩子喜欢。当然,再俊的人也俊不过柳泉,所以我当然不会对他的外貌大惊小怪。
“好无聊啊……”
手机电量不多了,对了,得让柳泉帮我把充电器带来……
发完短信,我在病床上百无聊赖地发了一会儿呆,过不一会儿,边上的病床传来了动静,我扭过头,看见那傻逼动了动身子,睁开了眼睛。
我们对视了,然后同时挪开了目光。
“哟,又见面了。”我说。
他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我是谁,说道:“又见面了。”大概是身体虚弱的关系,他的嗓音有些黯哑。
“唉,我竟然和一个自讨苦吃的笨蛋分在了一个病房。”我说。
“因为看别人被打而被送进医院的人没有资格说我……咳!咳!”他说。
我不再理会他,自顾自玩手游,玩了好一会儿,眼看已经快没电了,不能再玩手游,我就上了聊天软件。好友很多,但是想聊的人一个都没有,我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别人发的状态,随手点进了“附近的人”。平时我几乎从来不用这个功能,今日阴差阳错点进来,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网名叫“夹心饼干”的人物。
夹心饼干,有趣。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吃奥利奥吃得满嘴黑牙,走出去吓哭了小朋友的事迹。
这位饼干君的头像是一张毫无意义的风景照,我试着打开了临时对话框,给对方打了个招呼。
“哟,饼干君!”
对面马上回复:“哟,麦片粥!(这是我的网名)”
聊天如下:
麦片粥:“饼干君,你为啥叫夹心饼干?”
夹心饼干:“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麦片粥:“我只是单纯地无聊,没别的事可干。”
我原以为他会回答我爱吃饼干什么的,没想到过了很久,那边也没有回复,我抬起头,看见旁边的傻逼也在耍手机。
手机震动,饼干回我了,回了一串长篇大论:
“饼干,是一种世俗的无奈;夹心,是无奈的人!你看过一部叫《双面胶》的小说吗?夹心饼干的含义和双面胶近似——两个对你都很重要的人发生了争执,你选谁?谁都不能选,只能夹在中间,如果他们要打起架来,你可能被挤出去,也可能被挤扁,总之无论如何都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这样。当然,饼干可不仅仅指代两个人,它还可以是两种文化,两种观念,两种……反正很多很多东西。”
“挺复杂的,你的人生一定充满纠结。”我回。
“嗯。”这次答得又太简短了。
“你是什么夹心?奶油的?巧克力的?我喜欢谷香的。”
“我?看心情吧,反正都是要被挤扁的,爱什么就什么吧。”
手机屏幕暗了一下,电量只剩百分之五了,我回了一句:“快没电了,先不聊了。”把手机放到一边,重新躺下。
迷迷糊糊地睡了有两三个小时,醒来时,我看见旁边的床上驾着一块画板。
他在画画。
我动了动身子,试着走下床去,凑到他的病床边上。
他画的是一只麻雀,只完成了小半。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画技,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麻雀的羽毛栩栩如生,眼睛也水润润的,尽管并不完整,也仿佛马上就能动起来一般,我差点大呼一声“卡哇伊”,把手指戳上去,不过还是忍住了。
“想不到你还是个才子。”我说。
“素描兴趣班的作业。”他说。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看这样子我们还得在这住几天,总不能老是你啊你的叫吧?”
“中文名林书南,日文名七夜彻,英文名埃德蒙。”
他用背书一般的语气说。
“这么多名字?”我说,“你到底是哪国人?”
他笑了笑,说:“我是加拿大人。”
看他长相,显然是亚洲人,而且他的普通话比我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