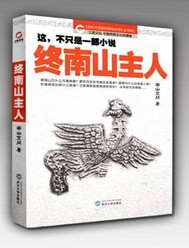话说杨愫和郭平娥在定阳太守府住了几日之后,平时不是一同聊天就是一起下棋,杨愫抱怨身子重,忌不住口,动不动肚子里那个还要翻一翻天,折腾的府衙上下鸡犬不宁,郭平娥像个小妹妹一样聆听,种种辛苦和不适都被两位夫人用来互诉衷肠;石柯、石贝则继续埋头于公务中。这天天气出奇的陡然热了起来,石柯和石贝就在花园里一棵柳树下纳凉,聊到了时政问题。
石柯靠在树干上,说:“二哥,我就知道,你那几天总是在大街上市井里出没,一定有什么原因。我当时就猜到你打算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说说你都想到什么了?”
石贝摇着扇子,说:“人心。”
树上的蝉鸣叫着,石柯说:“可是光有人心有什么用,之前你和丘狩他们制定的法律解决了钱粮和兵马,现在已经不像去年那样为了粮饷的事发愁了,这人心固然重要,可是我觉得还不是最为关键的。比方说……比方说……”
石贝说:“轻徭薄赋。是这句吗?”
石柯坐直了身子,“这固然是好,但是好不容易将府库充实起来,又要减少收入,不是自讨苦吃吗。再说眼下乱世,没有钱粮养不起兵,屯田既能增加岁入,又能充当粮饷,着实是个再好不过的法子。不知道这次二哥又能想出什么主意来。”石贝说:“我发觉我们的各项政策虽然好,但是从长远考虑,对百姓未必不是个负担,我们不仅要增加岁入,还要笼络人心。这虽然不容易,但是我已经有打算了。”
石柯略加思索,“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如果将这两项政策联合起来的话,不仅能继续招揽流民,也能增加军粮的产量,这样不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吗?农户、商户的赋税就可以酌情减轻了啊!二哥你可真是有办法!”
石贝摇着扇子,“但是这只是一个不成形的主意,具体到细枝末节还要和大哥以及各位大臣商量,你应当知道,这些关系国计民生,大意不得。”
石柯倏的站起来,拉着石贝的手就往书房跑去,石贝踉跄的跟着,“三弟,你这是去做什么?”石柯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写奏本,把你的打算和主意告诉大哥啊!”石贝苦笑着被石柯拖进了书房,写了奏本送往营城。
奏本被送到营城的同时,丘狩和李增也在和石珍商量扩大屯田的事,这份奏本送到之后,石珍立刻将其递给他们二人过目,丘狩和李增看过之后,石珍问:“二位以为如何?”李增说:“应当立刻实施。聪侯在奏本中说的十分清楚,百姓的赋税依然厚重了些,如果我们大力屯田,则军粮就可以自行解决,而不用增加百姓的负担。”
丘狩接着说:“不错,实施屯田法到如今,我们的府库已经基本充实了,但是还没有足够的余粮,财政上也是一样。所以,我认为应当扩大屯田,将定郡彻底纳入我们的掌控之中。至于民生,在下以为前朝的庸调署,工调署,和药材署都是竭泽而渔的办法,既不能实质上增加财政之收入,反而将百姓盘剥殆尽,十几年里将天下的财富全部抽走了,百姓赖以为生的钱财与民力都也被耗尽,根本是天下混乱、民生艰难的根源。应当立刻废除,另行仁德之政策,于百姓休养生息。”
石珍沉吟,缓缓道来:“即日起,废除庸调署,工调署,和药材署;发布榜文,招揽四方流民在定郡屯垦,只要连续屯垦三年,间续屯垦五年,既将其土地无偿赠与;另外由国库拨发专款,栽种一颗桑树赏钱五十,五年之内桑树未死就赏钱一百,每纺织一丈布,赏钱十,一丈丝绢,赏钱八。只要男耕有其田,女织有其桑,就能得到百姓人心,人心在我,何愁天子位。”
丘狩满意的捻着胡须,李增却说:“主公,这样也只是得到了千千万万的俗人心,还有士子之心呢?我提议在我境内举行科举,而且四科同考,收拢人才!”丘狩大惊失色,“从来都是天子开科取士,此举如是惹来非议,李从……”
李增不屑一顾的说:“年兄抬举他了,他?已经被侯爷打的没了嚣张气焰,即使他敢来又如何?至于其他诸侯,无不是山高路远,唯一能讨伐我们的就是张专,可是张专……”李增哂笑着,丘狩也忍不住笑了,“老了,老了,竟杞人忧天了!”
君臣三人相视而笑,石珍说:“好了,就这么办吧,这道政令涉及方面很多,劳烦二位了。至于这科举嘛,办,但不是现在,我们刚刚和李从大战了一番,过两个月风声小些再办不迟。”
二人领命退下了。送走了他们两个,石珍从桌案边角处的一摞奏本中抽出一本,开始批阅。而刚刚学会迈步的石崭在刘氏亲自的看护下,从堂前一步一步的走过。
话说李从班师之后因为伤势,一只不能处理事务,连求见者也大多不见,加上昆仑奴的事,李从对身边的人倍加猜忌,连平融夫人也难得见上一面。
平融夫人只好一个人在偌大的皇宫里一个人独自伤感,从宫女的口中得知了在定河浦两次战败的前因后果,这令她寝食难安。她实在是太了解李从的为人了,如此大的打击,是他从来都没有遇到的,自从起兵以来就没有打过如此狼狈的败仗,甚至败仗也只有在肆关石头滩和这次而已,她很清楚李从现在因为伤势而不能动怒,也不能为了这些,在粮草不济,士气低迷的时候大动干戈。可是一旦他得到了机会一定不会放过,到时候一定是倾巢而出,不杀的天昏地暗誓不罢休。如果这样一来,必然是生灵涂炭。
一连几天都睡不好,终日唉声叹气,平融夫人身边有一个老宫女,突然对她说:“娘娘如此下去是要生病的,不如走灯吧!”
“走灯”是卫朝时期的一种丑行的名称,因为忌讳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不知所云的称谓。说是丑行,是因为所谓走灯其实就是宫中的嫔妃因为按捺不住寂寞,偷偷地与人私通,将男子伪装起来趁夜色偷偷的运进宫里,等完事后在如法炮制的送出去,走灯因此得名。坊间传闻卫朝定宗皇帝的皇后和一位贵妃就精于此道。后来烈宗时法令严苛,加上罪行不小,走灯才渐渐淡出。
平融夫人二话不说就将这个老宫女打发到浣衣局去了。
心中的忧愁无处排解,平融夫人只好找来薛小倩,与她饮茶聊天。在后宫御花园的凉亭里,二人赏花饮茶倒是很惬意。
平融夫人只是手自己惆怅,却怎么也不说原因,薛小倩问不出也就不问了,只是低头饮茶而已。平融夫人见薛小倩不再问了,却自己说出来了,“妹妹啊,我之所以不说出来,不是因为难以启齿,而是因为这话大逆不道。”
薛小倩抬眼注视着平融夫人,“娘娘……难道说……”
平融夫人说:“陛下这次战败,心情十分不快。本来胜败是兵家常事,可是我担心这样下去只会让陛下更加暴躁,最后会变成暴君。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让陛下不再介怀这些。就是……”
薛小倩只觉得脊背发凉,“娘娘,你该不是想设法引发事端,令诸侯自相残杀吧。这实在是太过冒险了,一旦被诸侯识破,只能让他们找到口实征讨我们,而且陛下知道了也会对我们猜忌的。这不是个好主意。”
平融夫人惨淡的笑着,“我自然也知道这些。可是我的心里者的很担心他,他现在已经是天子了,他的一言一行都关乎着千千万万的人,我不想百年之后的人一提到他,都说他是暴君。”
薛小倩托着香腮,看着凉亭外的五彩缤纷的花卉,“说到暴君,他是越来越像他了。昨天,几个内阁大臣提议为前朝暴君上一个谥号,你猜陛下如何答复?”
平融夫人摇头:“不知。”
薛小倩说:“咱们的陛下说前朝的暴君祸害百姓,还给他谥号,这不是给他歌功颂德吗?”薛小倩边说边学李从的语气腔调,逗得平融夫人掩着嘴笑,最后薛小倩说:“就这么着,现在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那个暴君。总不能直呼其名,叫他元信吧。连带着当年被逼造反的太子,他和姜妃生的太子,两个太子都不能得到谥号,想想怪可怜的。”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执拗的很。”平融夫人说。
薛小倩断端起茶碗,看着那几片茶叶,说:“谁说不是。他们这些男人就是这样,谁都别想抓住他的心。于是他们这些心怀天下的男人就越是如此,前一天还和你说说笑笑,后一天就像没见过你似的。说什么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若是这样也就算了,可是他的心里除了他的江山,还有别的女人,恨不得跟着哥哥一道出兵灭了他算了,省的难过。”
平融夫人看着薛小倩的脸颊,幽幽的透着粉嫩,“又在想石贝了吧。”
薛小倩先是一怔,转瞬换成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随意的将茶碗放下,反而看着平融夫人,“说别人的人最在意自己。嫂子在意我惦念石贝,其实是嫂子想着哥哥才对吧。皇后娘娘也是凡人啊!”
平融夫人嗔怒的笑了,“讨打!”
笑过之后,平融夫人又陷入伤感之中,“其实你说得对,按说陛下从不亲近别的女子,我应当感激才是。这些年吃过苦,也享过福,确实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是偏偏我是读过书的,这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哪一个不是刀头舔血,艰难创业,陛下他做事鲁莽冲动,又固执自负。我真担心他会树敌太多,再像石头滩、定河浦那样,败也就败了,可是赌上江山的大战迟早会有,现在国家空虚,民生艰难,经不起他这么虚耗啊。”
薛小倩拉起平融夫人的手,“其实你也是杞人忧天了,陛下现在的脾气已经被从前收敛了很多,不用你如此担心的。再说了,这种事我们最好不要参与,尤其是你,他会对你疑心的,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他,怕他行差踏错,就告诉我,在朝堂上我还能说几句话,至于能不能劝服他,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了。”
平融夫人苦笑着,“这就是女人的命啊,什么时候都是不由自主的。等你能自主的时候,偏偏又舍不下了。”
薛小倩默然的看着平融夫人,“……谁说不是。舍不下那个人,不能自拔,那个人心里可曾想过你?”
石贝站在岸边摇着扇子,定河的水在眼前缓缓的流过,石贝回想着石珍的命令。原来石珍早在李难攻打定河浦的时候就已经派人去李从的领土内,打探情报、绘制地图,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准备回来,可是双方边境上岗哨林立,他们无法通过,请求帮助,于是石珍请他出个主意。石贝接受了命令,准备吸引治军岗哨的注意,探子借机逃回来。
于是石贝才在渡口等待船只。
章德已经将船准备好,停靠在渡口,“主人,真的要这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