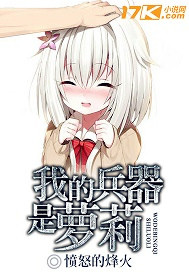陈叟听了,这才转头看向身旁立着的公子。
这一细看,不由得眼前一亮,只见那人一身锦衣,从头到脚都是上好的物事,面容俊秀,且双眼熠熠生辉,端的是贵气逼人。
这样的人,怎会为自家小姐牵马而行呢?
目光在两人面前转了几转,彩萱却突然反常的举步先走,牵着马儿边行边道:“快进来吧,我去叫月儿煮些茶水。”
看自家小姐行动急迫,陈叟心中更是疑惑,因此转身对上沈珂,开口问道:“敢问这位公子,是如何与我家小姐相识?”
沈珂坦然,“今集市上,萱姑娘被歹人随行,却不自知,恰好沈某途经此处,便上前助她脱险。”
陈叟闻言大惊失色,忙道:“小姐怎会被歹人随行?莫不是贪她钱财?”
沈珂摇头,沉声道:“萱姑娘年小单纯,被人哄骗,歹人是见色起义,特意将其往偏僻处引路。”
这话一出,陈叟立时站不住了,转身就要前去家中质问,沈珂在其后喊了一声,制止了他的动作,出言安慰:“老人家不必忧心,那贼人沈某已经派人抓住了,萱姑娘对此并不知情,那些个龌龊心思,还是不要拿来叨扰她了吧?”
陈叟这才回过神来,口中连声称道:“也是也是,幸得公子提醒,小姐只是豆蔻年华,的确不应与她知会这些,今日之事,老朽在此代小姐谢过了!”
说完陈叟就拱手弯下腰去,沈珂连忙将他身子扶住了,淡笑道:“老人家不必多礼,沈某此举,也是为感谢萱姑娘割爱,将那只银狐归还与我。”
“银狐?”陈叟恍然大悟,“公子原是常行沈家人,失敬失敬。”
沈珂摇头笑了,谦逊道:“沈家的名声,都是兄长一手撑起来的,我只是沈家一个不成器的份子,叫老人家见笑了。”
他这言语间将自己的姿态摆的平和,既没有自视甚高的跋扈,也没有恭逊谦卑的过头,叫陈叟这个外人看的很是舒服,因此,老人家语气也热络了些,忙伸手招呼他进屋。
沈珂本想推脱,但看陈叟待人热情真诚,心中也有几分松动,想了一下,索性就随他进去了。
陈叟路上边走边笑,口中言他过谦,“仅凭公子今日的作为,便知必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之人,况且沈公子还救了我家小姐,老朽真不知如何言谢。”
听了他的赞扬,沈珂面上却并未动声色,可心情也是极好的,平日里他在家中,看似过得逍遥快活,实则因兄长之名,颇为众人称道,虽然两兄弟面上都不在意这些,可是听久了,难免心生芥蒂。
大哥嘴上不说,可日日言语间都透露出要他早日收心,接管商铺的意思。
他与大哥感情是很好的,两人父母早亡,是大哥力排众议,凭自己经商的天赋和聪慧的头脑坐上了大当家的位置,这些年事事劳累,整日与那些东家勾心斗角,机关算尽,过得很是辛苦。
而他的脑袋也很聪明,只是心不在家业上,如无根浮萍,整日飘荡,与沈言相比之下,却显得快意潇洒了。
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兄长却毫无怨言的接过手去做了,原因无二,只是他为次子,长兄如父。
因此,他与沈言的关系堪称微妙,对于这个大哥,一方面尊敬有加,心怀愧疚,另一方面,却又因他徒增烦恼,落落寡欢。
市井皆言沈二公子为人轻浮,恣意浪荡,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只是一个活在沈言的阴影里,被打压的抬不起头的弟弟。
陈叟和彩萱的推崇,却是让他心田如久旱逢雨,又酝酿出丝丝生机。
如果那些诋毁他的人们,在两兄弟间,先相识于他,恐怕自己,真的能成为如那老者口中所说的,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之人,而不会落得如今这般狼藉名声。
沈珂嘴角讽刺一笑,摇了摇头,将心头这些恣意生长的妄想都强行压抑下去,换上一副如沐春风的温柔面具,径直朝那所破落的院子走去。
然一推开门,眼前的景象却叫他脸上笑容瞬间冻结。
这堪称贫瘠的院子里,中央空地,堆满了红绸捆绑的梨木箱子,竟然有四五个,那些箱子体积较大,几乎占用了整个空当。
陈叟见他看着这些箱子愣怔,便出言解释,“这些是大东家送来的谢礼,说是那银狐乃公子心爱之物,从小便养在身边,如今失而复得,一扫之前的不快,又恢复了生气,因此,特地送了感谢小姐的。”
说完,许是怕他误会,又连忙补充:“老朽也推脱过,但大公子态度坚决,况且,公子言箱中也不是贵重之物,老朽便自作主张替小姐收下了。”
沈珂侧头一笑,答道:“这是大哥送于萱姑娘的,老人家您作为管家代收了理所应当,沈某自是要恭喜的。”
陈叟见他并未面露不虞,便放下心来,伸手摆向前厅方向,沉声道:“公子请。”
沈珂进了屋子,正中的木桌被擦得干干净净,上面放着一个白瓷的茶壶和两只配套的茶具。
边上立着个丫鬟,沈珂瞧着眼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小丫头眨了眨眼睛,看起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可沈珂久居商场,虽没有直接接收府上的生意,却也不是完全顶着二当家的虚衔。
几乎一眼,他就能看出面前这看似灵动的少女,那双漆黑的眼睛后面,隐藏着他熟悉的欲望和贪婪。
彩萱怎么找了这样一个女子做丫头?
沈珂急不可见的皱了皱眉,随即想起晌午时她匆匆朝城角荒屋行走的身影,一瞬了然了。
看来,萱姑娘头脑虽然聪慧灵活,可是因年岁阅历有限,对于人心事故,却是知之甚少呀。
彩月见沈珂坐上了首座,便伸手端起茶壶朝莹白的杯中注了茶水,殷勤的端到他跟前,眼珠一转,脆生生道:“这是府中最好的茶了,还望公子不要嫌弃。”
沈珂端起来浅浅的品了一口,问道:“这话,是你家小姐说的?”
彩月闻言一愣,否认了,“只是奴家的意思,小姐在后堂里,不知晓的。”
沈珂闻言淡淡“哦”了一声,将茶杯放下不再言语了。
彩月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余光却见一旁的老管家陈叟面色僵硬了,转过头正对上她的目光,眼神恼怒而凌厉。
彩月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
就听耳边陈叟淡淡的声音响起,“你去院子里,将那些箱子里面东西腾空了,搬到仓房去。”
彩月诧异,张口道:“可公子还在……”
话没说完,就见对面陈叟脸一沉,喝道:“还不快去!”
她见此状况,无法,只得弯腰行了礼,转身出去关上门,搬院子里的重物去了。
彩月走了,陈叟这才微微一笑,看着沈珂,“家奴没有规矩,竟学了主子口气同公子言语,见笑了。”
沈珂摇摇头,淡笑不语,伸手请了陈叟入座。
两人关于生意寒暄了几句,沈珂发现,彩萱身边这个老管家,虽然看起来平庸至极,实则为大智若愚之辈,对于经商的规矩和条例,知晓的远比他清楚,言语间可见此人手段也异常灵活,只是可能常年身居低位,缺少了商贾的从容和魄力。
总体来说,如果此人利用得当,不失为经商路上的一大助力。
彩萱她的身世可谓不幸,但能得这位老仆鼎力相助,却也是这不幸中的万幸。
至于陈叟,见面前公子谈吐得当,对于商业的一些见解更是别出心裁,心知对方也非池中之龙,有心拉拢,便竭力邀请了他在府上用饭。
而沈珂这次却推脱了,声称家中还有事,与陈叟辞别了,没有惊动彩萱,被叟送到门前,外面家仆已经抬了轿子来,与叟客套几句后,上轿走了。
坐在车中,沈珂脸上的笑容渐渐淡了下来。
他眼前闪过彩萱家中庭院里那几个巨大的木箱,眸色随之沉了沉。
如果,他的猜测没有错的话,那么那位老者怕是就会错意了。
据他所知,沈言可不是无缘无故免费给别人送东西的人,不管那些东西,是贵重,还是低廉。
而他见过沈言类似如此的举动,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他十六岁那年收了自己的侍婢做通房丫头,毕日,便派遣仆人给那侍婢家中抬去几个箱子,里面装的是衣裳首饰和银钱。
第二次,则是族中叔伯为他寻了一门亲事,亲家是城中一高门大户,不仅家中生意做大,还有族人入朝为官。
那家的小姐开始不喜,死活不肯嫁他,毕竟当时常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沈家也因为父亲的突然暴毙而人心涣散。
后来沈言也是命仆役给那家小姐送去了几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扬州名伶的一套戏服和花中君子的三幅真迹。
那小姐收到后很是欢喜,瞒着家人将那些偷偷藏于屋中,观赏把玩,几日后,族人再提及婚事时,她便不再抗拒了。
如今,当年那个侍婢早已不知去向,而这位八抬大轿迎娶进门的花怜小姐,也在沈家东山再起之后,被沈言砭为侍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