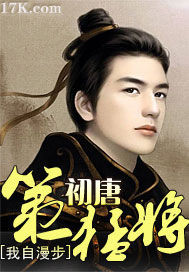“贱人,你竟然勾引三殿下,与你母亲一个德性!”张陶突然一个疾步,抡起手臂,啪的一声,一个清晰的耳刮便响彻全场。
我呆怔地看着母子俩的争吵,耳畔间全是张陶的的一阵紧似一阵的羞侮,却一声也说不出。当时的我,只当是权宜之计,却不曾想过有过多大严重的后果,这样的权宜,对女子名节而言,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住手!”在我还没反映过来之时,已见公孙子玉一把抓住张陶的手,狠力一推,张陶一个站立不稳,便已顿坐在地上。
“玉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待你母后?”
“母后?”公孙子玉微微嘲弄道,“若是她对儿臣的心爱之人礼遇有加,儿臣便还尊称她一声母后,,如若不然,嘿嘿,便休怪儿臣无礼了。”
“我与你这么多年的情份,竟然比不上这小丫头吗?”
“你——”公孙子玉骇然道,脸色涨得通红,“你胡说什么?”
“王后,你说什么?”
“说什么?”张陶头发凌乱,迎面对上公孙粼质问的眼光,冷笑道,“王上竟然不知道?”
“王后,请自重!”仲长卿上前一步,拦住张陶说道,“凡事请王后留一些情面!”
“情面?”张陶突然仰面大笑起来,凌乱的头发在她剧烈的狂笑下越发纷乱不堪,“王上?你知道吗?你的玉儿,我名义上的继子,与我是什么关系吗?”
“王后!”
“王后旧疾发作,你们还不快点将她扶下去世!”公孙子玉的一声大喝,吓醒了一旁近侍的宫女太监,众人见此情景,连忙手忙脚乱一把上前抓紧张陶便往下去!
“放开我!”
“好,放开王后!”公孙子玉突然出声道。“既是王后想说,那就让她一次说个够吧。”
那得到解脱的张陶闻言,整整仪容,略略思索后,朝公孙粼娇笑道:“王上,臣与玉儿这么多年的母子情份,如今玉儿却为了娶一个女子这样地伤臣妾的心。也罢,儿子大了不由娘。他要娶哪个,王上都不管了,臣妾又何必自讨无趣呢?”
公孙子玉闻言显然觉得有些意外于张陶的转变,一怔之下随即说道:“儿臣刚才失礼了,今晚儿臣会到母后宫中赔罪!”
我在一旁冷眼旁观,这“母子”俩,还真是一个比一个矫情。
当天晚上的东齐王宫,就在公孙子赔罪不久的凤至宫,便有丫头赶来汇报情况,可是当我们赶到凤至宫之时,只看到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公孙子玉与乱发掩面的王后张陶。
“哈哈哈!”阵阵狂笑响彻在凤至宫中,公孙子玉已是伤势严重,看见我进来,双眉飞扬,强笑道:“终于还是在临终时看到你了。”
“公孙子玉,你胡说什么?”我伸手掩去他俊脸上的斑斑血汗。
“我以为可以除掉她的,谁知却被她暗中下了药!这算不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苍白的脸色此刻因为连声的怪笑而显得妖异无比,可是看在我的眼中,却觉得是一种无尽的悲凉。“公孙子玉,你这又是何必?”
“那些谋害你的人,我怎么能够容忍得了呢?”
“你——”我低叹一声,却见他反握住我的手道,“如果,你早些遇到的是我,会不会,会不会喜欢我呢?”
会吗?我努力回想与他见面的那些片断,记忆如流沙般,从指缝间悄悄划过,敌视,争吵,嘲讽,诅咒,逃避,软禁,威胁,祈求,到最后,握在手中的满满的竟然全都不是,全然不对他的仇恨与厌恶,而是什么呢?是他盈满深情注视着我的双眸,哀怨而又动人心魄。
真的没有一丝的感动吗?
眼看着他的伤势越来越重,而太医却在旁束手无策,我不由恼道,“你们再不救治殿下,难道看着殿下死吗?”
说到死字,眼泪已是顺流而下。
“终于,看到你为我流眼泪了,看来,我没有白死。”他撑起身子,双手拭去我脸上的泪水。
“不许你说死,你这种坏人,怎么能够死呢?你没听过吗?好人多短命,祸害遗千年。你这种祸害,要活千年才行,你知道吗?”
“是吗?祸害遗千年,是啊,我是祸害,可我只想和你过一辈子而已,为什么——”
终于,他的手还没曾拭干我眼角的眼泪,便已垂了下去……
王后张陶,谋害王子性命,本应处死,但念在侍候君王多年的份上,死罪免去,被打入冷宫。事实上,她在进入冷宫之时,已经精神失常了许久。我最后见她的一次,是她被押送冷宫之前,她原本娇艳的容貌此时已失大半,灰败的面孔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妇人,正在冷眼讽笑着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我被她盯得毛骨悚然,却听见她阴恻恻的笑声彼时响起,“你和你母亲,长得真像啊。”
她慢慢地走近我,更仔细地端详着我,“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哈哈哈——凝霜,你终于来了,你你夺走了卫候的心,现在,你的女儿,再次夺走了我情郎的心,你这个贱人!贱人!你们母子,全都是贱人!”
她癫狂的神情狰狞而可怕,像是要将我整个都要吞进肚子里一样。我惊骇地往后退了一步,她紧跟着逼上一步,“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的命!”她直扑向前,双手如铁箍般紧紧圈住我的脖子,用力一摁,空气仿佛突然被全部抽走一般,我的眼中,只剩余下她那痴狂的神色,与狂妄的笑声,一种生生的绝望,突然便直直地**了我的心窝,记忆的碎片将陡然间将我带回了前世——
在前世的某个场景中,也曾有过这样痴狂的眼神,这样紧紧箝住我咽喉的双手,在世贸大厦,一个名叫李思洁的女孩子,把我推到了异世的深渊。
“我诅咒你,诅咒你生生世世,你所爱的人,不得善终,而你,孤苦一生!永不知情爱为何物!”
原来,这就是我的宿命!
我闭上眼睛,尽全力往她胸前凑去!既然命运的年轮再次重新启动,我又何必苦苦挣扎不休呢?
,这个时候,我也只能默默地站在他后面罢了。
只是未等到三个月后的册封大典举行,便已可是,世事总是如此,在我以为命运之轮就要重新启动的时候,它却突然戛然而止。
“快点放开她!”一个声音突然暴喝道。
是仲长卿带人赶来了!他奔到我旁边,一把扯开紧紧叉住我的张陶,一脚踢走她,动作粗暴,我从未见过这样神情的仲长卿,悲切而又紧张,以往的风清云淡突然间似乎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是揽住我,一迭声地唤道:“小蔓!小蔓!”
“长卿!”在唤了他的名字之后,我终于昏倒在他怀里。
公孙粼因为连番的打击之后,病倒了,一个月后,因为医治无效,便驾崩了。王位由仲长卿继承。
仲长卿勤政爱民,在他的统治下,东齐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原来许多贪赃枉法的事情少了很多,国运倒也算得上蒸蒸日上,而临近的其他诸国,却相继被越来越强大的周国灭掉。
但仲长卿眉宇间却不见半点喜色,他担忧的神情越来越重,因为继东齐等六国联盟失败之后,各国再也没有组织过更大的联盟来对抗周国,除开那些被周国灭掉的国家外,还有不少的国家,相继向周投诚。
这样平静的日子足足过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虽然有百官不断地上书奏请仲长卿立后,但是仲长卿却一直没有应允。
处理政务之余,他便会到我居住的宫殿来听我弹弹琴,看看书,或是看我新作的画。日子过得平静而安逸,似乎这便是幸福了。
我想。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的仲长卿,才会露出那种平静而淡然的神色,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种神情。
直至那一天,一个朝臣的奏章打破了这个平静。
宁静的夏夜,白天的闷热被一阵阵凉风渐渐吹散,我将御膳房的内侍为我准备好的夜宵端到了御书房,这段时间来,仲长卿一直都是呆在御书房里披阅奏折,有时忙至深夜也不休息。
从一些宫女内侍的私下议论中,我隐约知道朝庭中似乎出了什么大事,但我问起仲长卿时,他笑而不答,只是说没什么。
但是他眉宇间的担忧之色却是骗不了我的。
静静的御书房中,不见半个人影,只有沉香屑散发出的熏香缭绕在满室之中,那香味浓郁,使我几尽怀疑仲长卿竟能呆在里面许久,我轻悄地走到房内,才赫然发现仲长卿靠在椅子上,竟不知何时睡着了,半张面朝上,枕在一只手臂之上,也许是正在做着极美的梦,那张俊秀的脸上竟微微舒展开来,露出了极舒心的笑容。
心念所至,不由一怔,我这才想起,这笑容,竟是如此久违。那便让他好好地把这个梦做久一些吧。正想要退出之的时候,却在不经意之间,一眼看见掉落在他脚旁的一张奏折,我放下手中的夜宵,走过去顺手拾起,展开看了一眼。
那张奏折,明明只是轻轻的一本奏折,但是瞬时间却恍如千斤重的一般,我只听得头顶上“轰”的一声巨响,原本自以为平静的心湖却刹那间掀起了滔天巨浪。
……
卫女妖姬,惑世乱民,扰乱朝纲,望陛下以江山社稷为念,杀之以平民乱。
手上的奏章,不知何时已从手中飘落下来。
“小蔓!”
身后仲长卿不知何时睡醒了过来,拾起地上的奏章,只看一眼,便脸色大变,急道:“小蔓——”
“你不必说了。”
我抬起头,眼泪从眼眶中涌出,“你以为你能瞒我瞒到几时?”
他看着我,脸色迅速灰了下去,“我,我——”
“是先王后张陶原先的一些心腹,利用此次地震的事情,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臣工,大肆渲染,想为张陶报仇罢了!”
“杀了我罢!”我看着他,心中的悲痛不能自已。
如果再让我牵累到他,那我便是罪该万死了。
“这种无籍之言罢了,这个王英春,实在是罪该万死!竟然敢上这种奏章!”
“罪该万死的人是我!是我连累了你!连累了东齐!”
我拉住仲长卿,看着他纠结成一团的眉峰,强颜笑道,“这个王春英,我是知道的,他是东齐国的三朝元老,如果因为我一个人而累得你们君臣不和,我又怎能心安?”
“胡说!这种天灾人祸,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深居宫中,何来惑世乱民,何来扰乱朝纲,这些人,全部是信口雌黄!”
“明天,我就诏告全国,立你为后!”
“长卿!”我惊讶地看着他。“这怎么可以?”
臣子上书要杀我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立我为后?
“怎么不可以?”他一把抓住我的双手,“还是说你不愿意?”
“长卿!”我看着他,就这样看着他,还能说什么呢?有一个人,情愿舍弃生命也要保护你,宁愿置那么多人的“忠言”而不顾,只为了保全你,那么,我还能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于是举国下诏,定于三个月后举行册封大典。
全国上下议论纷纷,有些深知宫中典故的臣子亦曾几次三番上折劝告仲长卿,但全被仲长卿束之高阁。我知道,他心意已定经传来了周国大军率领百万大军将要攻打东齐的消息。
周国一路势如破竹,从最远的邺城开始,先使用臣服于周国的其他国家的先头军队,战火很快便到了东齐的国都临城,仲长卿先前只为了忙于救治地震的灾民,并没有多加防范,等到周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防守于远处的军队已然来不及回来救援。
我记得那个用最浓郁的的墨汁泼染成的天空的晚上,先是宫中一阵大乱,然后是不断呼喊奔跑的宫女内侍,金银珠器,在争夺声中洒落在四处,曾经森严辉煌的宫殿变成最嘈杂、最紊乱的闹市。人人弃之如草芥,逃之惟恐不及。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说的是亡国昏君啊,仲长卿自治理东齐来,兢兢业业,不曾荒废过一日政务,不曾贪图过一日享乐,为什么却同样做了亡国之君?
PS:如无意外,今晚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