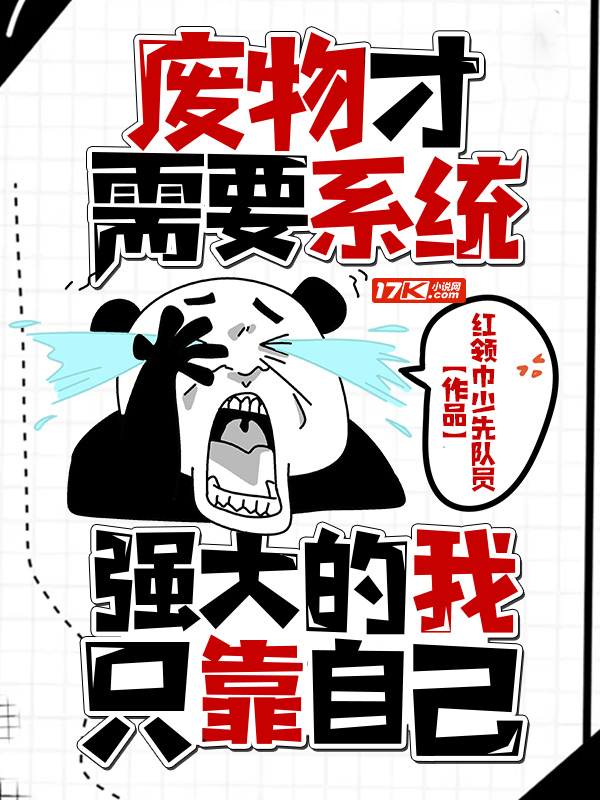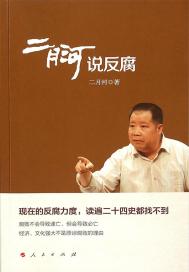“杀了她!杀了她!杀了她!”
……
一声声杀喊,震得她双耳轰隆鸣响,此刻她和魔军被成千上万的仙界三军,围困在荒芜的焚神山上,凉九欢隔着飘荡在空中的七彩朝珠,慌乱地望着一步一步缓缓走向自己的姚应华。
她在那双泛着细碎温柔的落雪深眸中看到抱着悦千冢倒在地上的自己,是等待他宣判的罪人。
君上,他们都说我已经不是至洁至圣之人了,我已经脏了,你信吗?
君上,你不要再过来了,此刻,我不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一个公然和六界称作魔皇的人在一起的我,会让你陷入两难……
而姚应华似是完全看不到她眸中无声无助的乞求,丝毫不顾万伺邪和皎月的戒备,双眸只是固执地回望着凉九欢,一步一步走近她,仿佛在说,别怕,我过去,听你解释。
众魔兵似是被他浑身散发的神尊君威所摄,在艳无疏的默认下,不得不退让出一条路。
他停在那里,视线自始至终没有从环抱住悦千冢的凉九欢身上离开。云间手指下意识地伸手去碰触隔在他们之间的七彩朝珠,却在半途中忽然收回了手,转而从袖中飞出一方玉质锦盒,将七彩朝珠纳入了其中。
东华帝君和灵智子、玄威子三人见状眉头轻皱,姚应华刚才那动作的深意,只怕……只有他们三人能看懂。
他竟然也碰不得那七彩朝珠。
那……想当初,九天之内,七彩朝珠只有岚音女神和姚应华能碰的。
“小欢,我不杀他,您跟我回苍华莲境,好吗?”
一指韶光云烟,似是吸收天地日月的宁谧之力,幻化成两黛雪巅月眉,斜飞入鬓,缓缓映出一双落雪深眸。
那脸庞分明就是韶光之神,采集世间之灵气,精雕细琢而成,透着与世无争的包容,还有几分说不清惊鸿冷艳。
似乎只要万物生灵都注入了他的品貌,天与地便有了精魂梦魄。
那浩瀚风华铺天盖地地映入一双痴呆的红宝石眼中,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此刻变得如此清晰,如此强烈,如此,压抑。
他身为上古神尊,怎能在对敌的关键时刻,罔顾三军与魔兵的生死惊诧,淡淡地伸出另一只云间玉手,递到她面前,这般任性地问出口。
“君,君上……”
这女人绝不能留!一道凌厉杀光闪过阴鸷眸底,就在凉九欢呆呆地瞅着姚应华的手,东华帝君掌心猛然聚气准备一击必中凉九欢。
这一掌,他是坏了必杀之心,自然用了十成功力。
“轰隆隆……”眼看这次凉九欢必死无疑,却只听一道惊雷乍响,震醒了呆掉的众人,他们寻声惊愕的抬头望去,只见她头顶的上空,不知何时已经急遽出现了一团团遮天黑云。
它们象一群奔腾咆哮的野马一层层漫过头顶,越聚越厚,越压越低……整个天空,很快都是炸雷的响声,锯齿形的雷光,就如上古凶兽,不时地冲撞天空。
“不好!这是欢宝的天雷劫!”
如此骇人景象,然而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处,却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山谷景象。
墨缎一碧的山色,天幕似空灵如洗,又似风雨欲来,此时的花事谷,静默得如同不曾有过一丝生息。
清风扫过,一抹天青的烟雨身影,似青雾笼身,投影在地,清丽婉约,矜持如韵。
这应该此时在浣音洞闭关养伤,正处在关键时期的花事了。
姚应华和悦千冢决战,敖听心被灵智子安排留下,镇守花事谷。她本担心花事了出关看到被皎月火烧的花事谷不开心,于是正在用自己的灵力恢复被毁的一草一木。
此刻听到动静,转头正看见不知何时站在的那里发呆的花事了,心中咯噔一声暗叫不好。
大师伯临走前不是说师父还需一个月方能养好伤出关吗?这会儿他们刚走,他就出来了,他就真的这么担心凉九欢,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吗?
“师父你不能出关!”责怨一股脑冲上大脑,她不管不顾地正要上前“说教”花事了,却见他抬头,对她笑着说了一句“想我开心,就呆在这里好好恢复这里的一草一木”便转身走了。
抱着一把琴,步入云海竹梯,幽幽地穿行在一片残败之中。
那手指宛如清晨跳动在竹叶尖上的露珠,晶莹剔透。他的发,乌青如碧石,仿佛从天而落的烟雨瀑布,滑出肩头,掠过竹叶,一曲九天韶音在晨光中流淌而出。
他的肌肤本来就是纯粹的雪白,在竹云间,白中透出一丝苍茫;那纤细如柳的眉,似诉不尽的温柔;那不染而淡粉的嘴唇,给纯粹的雪白添了几许生机。
敖听心一屁股坐在花事院的石凳上,懊恼一声大骂自己花痴,她就知道师父会利用她这一点,将她所有的不满轻而易举地变成无可奈何。
穿行之中,花事了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对着摇曳的露珠微笑,羞涩的露珠终于滑落竹叶头,滴在青葱指尖。
他突然想起曾经有一脱兔窝在他怀中将这指尖的露珠舔舐个干净,然后满足地露出一排洁白的兔子牙,嚷嚷道:“美人师叔,我还要喝!我要天天喝你指尖的露水,这比琼楼玉浆都要透心甘凉。”
他知道她体性热,最爱靠近凉性之物,所以他在一千年的日子里,只要不闭关,必然习惯性地每日早起采集清晨竹叶露珠,给她做花酒和花饼,这,对她的身体,的确是有益。
可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以后她会贪恋上这种味道,不会轻易将他忘记。
想到深处,转过身子,他环顾四周,四周竟到处都是一只兔子的身影。
画面中的兔子上蹿下跳个不停。一会儿藏在这片竹子身后,一会儿躲在那片竹子身后,好不惬意。
可是无论它如何小心翼翼地躲藏,对一道背对着它的天青身影,都像极了欲盖弥彰。
通体晶莹剔透的玉白兔身,在郁郁葱葱的竹林中,无论如何躲藏,好似都是一清二白。再加上它因为偷笑不止而浑身紧张颤动的身子,使得它身上的遮身竹叶震动的仿佛在得意洋洋地说:“你来找我啊,我就在这里。”
那道天青身影摘掉双眼上蒙着的那条白色的玉带,轻轻转身,仍然一眼就能看到它的藏身处,却故意装作犯难的样子,轻声惊讶道:“欢欢,你藏在哪里呢?师叔很笨,总是找不到你……”
那兔子听到后,身上的竹叶又是一个剧烈的颤动,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天青身影抿嘴一笑,去往别处寻找。
就这样,他找了许久,仍然找不到,只好坐下休息。
而惊险一过的小兔子突然窜到他身上,大笑不已:“哈哈哈,美人师叔真笨笨,每次都找不到我。凉九欢好聪明啊,每次都能找到美人师叔,所以这次美人师叔要给我弹琴,弹最好听的琴声。”
欢笑中,小兔子没有注意到天青之人满眼的宠溺。
小兔子看天青之人拿出琴,抱在膝上,高兴地手舞足蹈,立刻跑到琴前面,立起两只后爪子站起来,踮起两只前爪子,东倒西歪地蹦蹦跳跳,还嚷着:“那天我看大师兄和二师姐就是这样,大师兄抚琴,二师姐跳舞……这样跳……不对不对,这样跳……”
“嘻嘻嘻……”一把倒地,立刻又站起来,对着美人师叔憨笑不止,“等我化成了人形,定要二师姐好好教我跳舞!美人师叔抚琴,我跳舞,羡煞那些仙女姐姐们!嘿嘿……”
彼时,声声欢笑,句句憨娇,犹如昨日刚刚发生过的一般,清晰地徘徊在耳边,只是,此时那欢笑之人去了哪里?那些虽是做不得数的童言稚语,为何却给抚琴之人记住了呢?
他抚琴,她作舞。
他采露,她欢饮。
他焚香,她嗅闻。
此刻,他依然在这里,而她,在哪里?
风,起大了,抱琴之人似是与周身的竹林融为一体,从记忆回神,继续穿行步向云海竹梯的尽头,仿佛那里站着那昔年欢笑之人。
身形绝美,身影凄绝,决然行走,仍然是理不断过往,了不清回忆纠缠。
那竹叶簌簌不似风雨将至,却似声声呼唤,身旁所过的每一个竹林都是过往的回忆,那只兔子偷喝了花酒,偷吃了花饼,偷偷打开了他的琴盒,偷偷弄翻了他的捣药瓶,偷偷推倒了他的焚香坛,只为将他从琴声中拉回……
走的越急,记忆浮现的愈加清晰。
它终于粗心大意地提前化成了人形,怕他指责,就悄悄躲在花事院的门外,看他坐在树下焚香抚琴,扭扭捏捏不敢如同往常般讨他开心。
于是他装睡,给她靠近自己的勇气,却不想她居然一口喝下酒,变回兔子原形,一头视死如归地扑进他的怀中装醉。见她睡得那般心安理得,他终于可以放心浅眠了。
她醒来后,其实他也醒了。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他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像回到从前一般,任她在他怀中嬉戏一番。
她终于化成了人形,虽不是绝色倾城,却是独有的清秀可人。他心中欢喜不已,却也担心不已。
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她了。
他给她的千年天真无邪要到期限了。
他说他不怕任何人能带走她,那是假装的大方,尽管他有足够的自信,相信她不会愿意离开他。
化成人形的她,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对待外界充满了好奇,他不能限制她的自由,他不能拘束她的未来,他不能囚禁她的身与心。
如是为她,他甘愿默默注视着她的欢笑;如是为她,他情愿守在原地等她累了回来;如是为她,只愿她情有所归、意有所属、心有所安。
因为,他深深的明白,她从来不属于她,他能做的,就是护她永世周全。
终是要走出深藏记忆的竹林,强撑的坚强与疾痛,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竹林。
天与地,一幅烟雨浩渺的丹青画卷,他于她,永远是她生命中最远最淡的那一抹留白。
从来不会显得特别重要,偏偏又不能没有,让拥有它的人,想起时,总忍不住散发出无限怀念。
花事的生,只不过是一场告别,告别百花,告别流星,告别河流,告别大山,告别她,然后微笑说再见。
花事的凋,只不过是一场遇见,遇见百花,遇见流星,遇见河流,遇见大山,遇见她,然后微笑说告别。
初遇的海畔,是开始,也是终结。
尽头啊,呵呵,我终究不能护你到最后。
所以别怪我,将你还给了他。
你一直没有问我,我也一直没有给你一个完好的解释。
解释,到现在,我都不能给你解释。
此年的花瓣未败,思念的花事已起,远方那么远,时间那么长,原地那么疼,无望那么殇。
琴在膝上,手在弦上,思绪却在千里之外的焚神山上。
那里电闪雷鸣,不似他这方清亮,即便如此,指动琴乍响,宿命都必须向其低头!
几道黑色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来到他面前,花事了道:“曲成。”
黑色身影神色大喜,却又在听到后面的一句而勃然愠怒,“但是我不会弹奏。”
“神君,此话何意?”为首的黑衣人眸中闪过一丝杀意,却伸手示意众人稍安勿躁,转而问眼前人。
一身天青温婉,明明淡然清绝的琴音,却夹杂着扑面而来的修罗气息。
花事了不答反问:“你们的新主人是谁?”
“这是我们寐尸军之事,恐怕与神君无关。”黑衣首领同样不肯轻易妥协。
“的确与我无关,但是伤她者,死。”琴声骤然响起,震慑黑衣人。
黑衣首领心中暗惊,但是仔细明白过来他口中的她是谁之后,幽幽一笑:“神君不必多虑,我不妨告诉神君,她就是我们的新主人。”
“简直异想天开!”这话是明显动了怒的,琴声携杀而来,黑衣人避无可避,蓦然被震退数丈之远,口中鲜血直流。
“呵,”抹掉嘴角血迹,他依然保持一贯的幽幽笑容:“我君主临终前只有一句话,那便是誓死保护新君主。凉九欢,便是新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