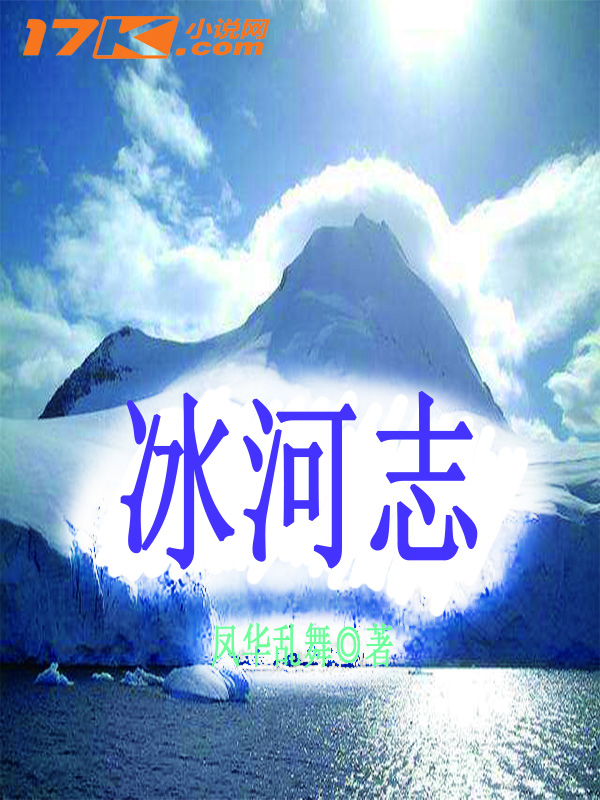慕容轻狂所说的药方,张傲秋已经拿到了手,药方里开的药材有固本培元的,也有扩撒静脉的,还有大量解毒的,但这其中几种药材张傲秋是听都没有听说过,比如鬼蛇藤,七彩仙兰,星莹火莲,还有碧血丹心草等等。
张傲秋看着药方,皱着眉头想了想,一些常见的药材,已经在之前给那些人包括城主府的云凤阁诊病的时候搜刮了不少,解毒的药材可以找罗兢田去收集,而那些特殊的药材,则只能打城主府的注意了。
这之前,张傲秋曾让紫陌给他易容到罗家,将罗烈完全治好,又通过辛七将罗烈秘密送到了城主府,而云凤阁自上两次施针以后,就没有再去过。
张傲秋右手轻轻弹了弹手上的药方,决定最近几天再到城主府去一趟。
而慕容轻狂需要修建的丹房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动工,这丹房果然不同其他建筑,不但要求整个丹房成密闭形式,但又要通风良好,而且还要保持干燥。
不过幸好慕容轻狂是这方面的专家,以前的丹房都是他自己所建,现在有专业施工队伍帮忙,更是得心应手。
第二天一早,张傲秋带着阿漓往城主府赶去。
昨天下午,张傲秋让方伯通知辛七,本来辛七说要一早过来接他们二位,但现在张傲秋他们新买了马车,想着也不用这么麻烦,就婉言拒绝了。
到了城主府后,张傲秋掏出云历给他的腰牌,交出随身携带的星月刀,守门的军士验过腰牌后将他们带到了城主府后院。
到了后院,辛七已经在那里候着了,见他们过来,招呼一声就往里走。
进了内舍,张傲秋老远就看到云夫人站在桌后,带着阿漓给云夫人见了礼后,云夫人笑呵呵地说道:“小先生,阿漓啊,以后你们就不要这么客气。这次怎么这么长时间才过来啊?”
这话倒不是责备,完全是拉家常的问语,云凤阁经过张傲秋两次治疗以后,虽然比不上以前,但基本生活早已可以自理,所以云夫人看着云凤阁的样子,心里也放下了块大石头,对张傲秋跟阿漓两人感激中自然带着一股亲切之意。
张傲秋解释道:“云公子的病,每施针一次,其间隔时间就越长,这次施针后,下一次就要等到年后了。”
云夫人笑着说道:“知道,知道。我啊,也是想见见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却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家阁儿要是能有你们一半,老身睡着了都要笑醒的。”
张傲秋欠身道:“云夫人谬赞了。”
云夫人笑着不理他,对阿漓招招手说道:“阿漓啊,快,到我这里来坐坐。”
阿漓乖巧地向云夫人福了福,走了过去,坐在云夫人旁边,张傲秋随后跟了过去坐在阿漓旁边。
云夫人拉着阿漓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又认真地端详阿漓的俏脸,赞叹道:“啧啧,这丫头生的可是真俏,不知道有没有许人家啊?”
张傲秋听了心里一急,连忙道:“阿漓虽然还没有许人家,但是她已经有了心上人了。”
云夫人听了叹了口气说道:“小先生不要紧张,你放心,老身不会抢你家阿漓。
我知道你这么紧张是什么原由,其实以前,阁儿是一个即善解人意,又聪明伶俐的孩子,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接触到了外面一些坏的东西,又因为他是城主的独子,外面的人都让着他,所以开始肆无忌惮。
有次他犯了大错,他爹当着整个临花城的面,亲自动手用刑,整整抽了十鞭,那次他是差点就……,后来在床上躺了半年才好过来,这也是他命大,但他爹毕竟是城主,有些事情要秉公办理,老身也不怪他,只是他平日里忙着公事,很少管阁儿,而我又……,唉,希望他经历这件事情后,有所改观吧。”
张傲秋想起那次云凤阁当街强抢民女的嚣张样子,不由升起义愤,说道:“云夫人,苛政必用猛药,如果一味的溺爱忍让,只是寄希望于他自身悔改,终究还是害了他。”
阿漓一听急忙拉了拉张傲秋的衣袖,暗暗地打了个眼色。
云夫人看在眼里,脸色一黯,叹道:“阿漓,小先生说的是。所谓慈母多败儿,这事老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正说着,云历从外面赶了过来。一看云历过来,张傲秋跟阿漓连忙站了起来,云历摆摆手说道:“好啦,不用见礼了,都坐都坐。”
云历坐下后,自有丫鬟送上精茶。
云历喝了一口茶水,正色道:“小先生刚才说的话,云某在门外都听见了,真是一针见血。
我已决定,等那孽子病好以后,就让他更名改姓,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送进军营,到时候身为军人,有军纪约束,也不怕他再出来祸害别人。”
张傲秋笑了笑,没有接话,这毕竟是城主府的家事,还轮不到他一个大夫插手太深。
云历见张傲秋不说话,也不以为意,又品了口茶,问道:“小先生这次给犬子施针,会不会像上两次那样费神?”
张傲秋老实答道:“云公子的病症,每施针一次就要好上一分,上两次已经打好底子,脑部的主经脉已经大致疏通,所以这次施针要比上两次轻松一些。
只是这以后可能要服用一些特别的汤药,这些药材很是难找,我已将药方带过来了,这方面还要请城主早做准备,免得要用的时候没有。”
云历笑着说道:“那就辛苦小先生多多费心,药材的事情,我等会吩咐辛七,以前也是他办的,小先生就放心好了。嗯……,等小先生施针完后,可否到我书房一坐?”
张傲秋知道云历有事跟他说,略想了下,点头答应下来。
一顿饭的功夫,张傲秋就收功拔针,云凤阁自有下人照料。
辛七领着张傲秋往云历书房而去,而阿漓则是留下来陪云夫人说话。
刚一进书房,张傲秋就被挂着书房右手墙上的一副字所吸引,不由自主走近细细观赏,越看越是惊异,由衷赞道:“好字,真是好字。”
云历在旁边问道:“好字?小先生,这字好在哪里?”
张傲秋说道:“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
我观这幅字,藏露结全,逆锋起笔,回锋收笔,锋芒藏住,极重含蓄。而且笔道停匀,腾挪起伏,深有曲折之美,笔画与笔画之间牵丝映带,用笔沉稳,章法分明。
整幅字外貌圆润而筋骨内涵,其点画华滋遒劲,结体宽绰秀美,平中寓险,深得‘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领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精妙。”
云历点点头,忍不住叹道:“想不到小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对书法见解也是如此精深,如此小的年纪,真是难得。”
张傲秋笑道:“观赏书法的再怎么精深,也比不上这写书法的修为,小民也没有想到,城主不但胸怀兵甲,还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
云历诧异地“哦”了一声问道:“小先生怎么知道这幅字是云某所书?”
张傲秋看着云历,笑而不答。
云历见他此时的样子,脑中立即想起老方有看不穿张傲秋的说法,此刻看来,竟突然心生同感。
云历也不再问,自顾自地走到手边靠椅上坐下,然后伸手一引,招呼张傲秋同坐。
张傲秋在云历对面靠椅上坐下,云历端起桌上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然后问道:“小先生不是临花城本地人吧?”
张傲秋一听,知道戏肉来了,正了正身子答道:“小民是莽山人士。临花城是最近才来的。”
云历放下茶杯说道:“那怪不得了,要是临花城有小先生这等人才,云某应该早就知晓才是。不知道小先生是要在这临花城常住了,还是只是短暂停留?”
张傲秋听得一怔,想起眼前形式及身负血海深仇,不由一阵茫然,摇摇头说道:“小民也不知道。不过小民手上还有笔债要讨,等诸事具了,也许会在这临花城终老吧。”
云历问道:“不知小先生所讨的这个债,是否需要云某协助?”
张傲秋见云历表情,知道若不坦承相告,就始终不能解开对方疑虑,不由把心一横,说道:“上次城主府与那一教二宗发生火拼一事,小民也有听说。不瞒城主,小民手上这债的债主跟城主府要对付的是同一群人。”
云历望着张傲秋,嘴角牵出一丝笑容,不紧不慢地接着问道:“既然我们对付的是同一群人,为什么小先生不一早就直接相告?”
张傲秋摇摇头说道:“一来我们初来咋到,若是一早告诉城主我们目标相同,我想城主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生怀疑,这是人性使然,城主以为然否?”
云历深深一想,随后缓缓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张傲秋接着说道:“二来就算城主一开始就相信我们,那时我们双方就算秘密行事,但终有蛛丝马迹,一旦对方有所察觉,我们几个势单力薄,即使有城主府的保护,但那也并非长久之计。所以不如由我们躲在暗处,这样不但可以保存自身,而且还可以方便行事。
况且那一教二宗势力庞大,并不是什么软柿子,没有确切证据,也不能贸然下手,不然只抓几条小鱼,根本于事无补。”
说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想了想接着说道:“本来我们打算找到真凭实据后,再通过辛七转告城主,如果形势严峻,则直接用城主赐予的腰牌,调动临花城军队的。但今次即以说明,以后的情况还请城主定夺。”
云历先是赞了一声:“小先生小小年纪,当真心思缜密。”
接着问道:“你们可有什么消息?”
张傲秋将杨记米店跟杏林阁的事情跟云历简单说了一遍,当然隐去了得到这个消息的过程。
云历嘴角一牵,嘴角露出嘲笑的神色,洒然说道:“上次在临花城大肆搜捕一教二宗的余孽,本想打草赶蛇,没想到他们倒是沉得住气,在我眼皮底下玩起花样。看来不下点狠手,他们还当我云历是傻瓜了。”
张傲秋道:“城主此时千万不可出手,我已安排渔帮的人日夜监视这两个地方,我担心这两个地方并不是他们在临花城的真正窝点,还是等一切有定论后,再一网打尽。”
“渔帮?”云历奇道,遂想起前几日老方跟自己汇报的事情,不由扬天叹了口气,说道:“要是我那孽子有小先生一半的才能,我云历就是不当这城主也愿意。”
接着断然道:“我会安排人手在你们周围,这件事情由辛七去办,你们有任何发现,一旦要动用城主府的人,辛七会第一时间将消息传给我,免得辗转耽误时机。
我这边也会加紧准备,你说的那两个地方,我不会动他们,就只当不知道此事。”
说完又深深看了张傲秋一眼,说道:“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