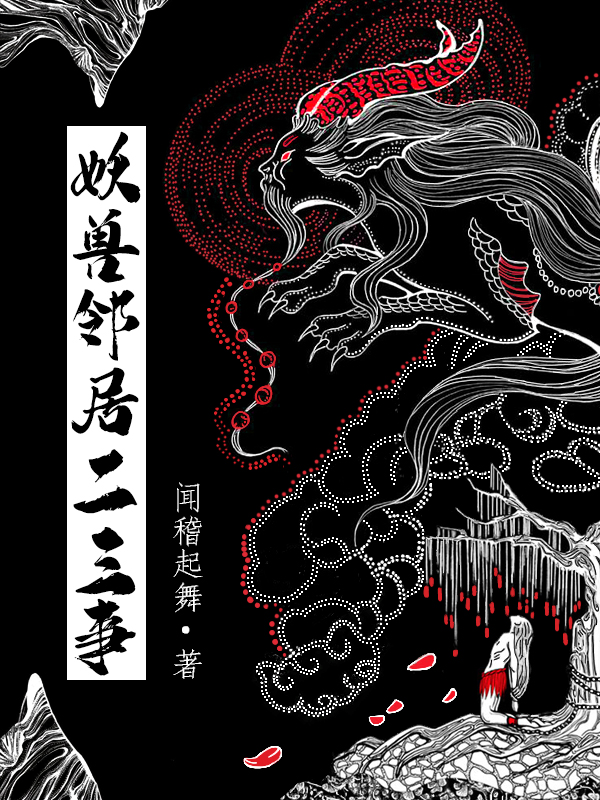袁柘垂下头,一字字地道:“臣知罪。”
刘羲纬叹息道:“袁柘啊袁柘,你我君臣多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当寡人不知道吗?若非刘勇他们拦着你,秦非他还能跪在这里说话吗?”
袁柘昂首道:“陛下英明神武,臣的心思根本瞒不住您。臣也就不绕圈子了。当初秦非请您御驾亲征,臣坚决反对,怕的就是您出意外。您是一国之君,是祁国的脊梁。您的到来,虽然会令军心大振,可您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大祁国千辛万苦争来的大好河山,便会顷刻间沦为雍国的领土。今日项重华那一剑若是真的刺下去,往日的一切辉煌都会化为乌有,您……”
秦非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袁柘,冷冷地道:“可是,今日最终输了的人是项重华。而且今日陛下剑上喂的剧毒,全天下只有我有解药。项重华三日之内必定毙命。这还不是多亏了陛下亲自出阵?”
袁柘霍然站起,怒视秦非,高声道:“亏你还有脸说!陛下这次刺中项重华全凭侥幸。若不是项重华一时走神,输的就是我们!秦非,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巴不得陛下出事!”
刘羲纬心里也自知自己的剑术不如项重华,听得“全凭侥幸”四字,脸色立即由白转青。他狠狠瞪着袁柘。右手重重地往榻上一拍,向他大声怒喝道:“放肆!谁准你在寡人面前叫嚣的!还不快给寡人跪下!”
袁柘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语,吓得跪倒在地,不断叩首。
秦非忽然站起身,自帐内的架子上取了一把宝剑,跪倒在刘羲纬面前, 将剑高高举过头顶,昂首道:“秦非本为雍臣,为苟全儿女性命,甘愿叛国为贼,已为天下所不耻。臣为祁国出谋划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依然被人视为居心叵测,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臣不是不怕死,但如此里外不是人,提心吊胆地活着,远不如一死了之。求陛下看在臣也为祁国侥幸得过几座寸土小城的份儿上,赐臣一个痛快。”
刘羲纬望着年仅三十却已经两鬓斑白的秦非,愧疚与同情油然而生,摆手道:“把剑放下,站起来吧!无论你是否真心视寡人为君,凭借你赢得的城池,也足以让许多所谓的忠臣蒙羞。”
秦非低声道:“多谢陛下。”将剑放在地上,拱手立在一旁。
刘羲纬这才看清他头顶一大块头发已经被袁柘削去,对袁柘的不满又多了几分,压抑着怒火向袁柘道:“袁令尹,秦司马是你用计请来的,也多亏了他对雍国诸多要塞的熟悉和过人的智计,我祁国才可以长趋直入,一路打过黄河,直逼潼关。当初要用他的人是你,如今要杀他的人还是你。你到底要寡人怎样才满意?”
袁柘道:“臣当初提议要留秦非,为的是利用他对雍国各大要塞的熟悉,打过黄河。秦非为人阴险多智, 如今目的已经达成,再留着他,只会夜长梦多。”
秦非惊出了一身冷汗,惊恐地瞪着刘羲纬。
刘羲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向袁柘喝道:“住嘴!”
秦非苦笑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原来秦非也不过如此。”
刘羲纬冷冷瞪着袁柘,道:“袁令尹您说的夜长梦多,针对的是您自己,还是祁国?”
袁柘急得满身大汗,站起身疾呼道:“陛下明鉴,臣几曾嫉贤妒材,排挤他人?”
刘羲纬喝道:“跪下!”
袁柘匍匐在地,颤抖不已。
刘羲纬仰天长叹道:“昔日寡人策马楚云山,路遇一道人,相谈甚欢。其有云曰,圣人已逝,贤人尽隐,天下唯余谋士。其中许殊虽智,然怯懦逡巡,不足以称国士。唯秦非以略著,袁柘以谋称,一为飞龙,一如翔凤。此二人者,得一人而足以得天下。寡人好奇,便问那道人,若飞龙翔凤兼得会如何?不料他只是笑而不语,隐身而去。如今,寡人似有几分明白他的意思了。一山难容二虎,一国难容二士。”
袁柘本欲争辩,望了一眼刘羲纬的表情,垂下了头。
刘羲纬道:“臣子间的勾心斗角本也无法避免,寡人只求你们莫把这些应该在私下解决的事情搞上台面。至少,不要让寡人看见。”
秦非叩首道:“臣谨遵陛下教诲。”
袁柘也勉强表示,绝不再与秦非为难。
刘羲纬一脸疲倦地摆摆手,道:“下去吧!寡人看见你们都累。”
秦非和袁柘一前一后出了门,差点撞上慌张赶来的息雅。
息雅心念刘羲纬,无暇和秦非、袁柘周旋,简单点了点头,便冲入营帐。袁柘见她如此无礼,又在刘羲纬受伤时赶来,怕她对刘羲纬不利,便想上前喝止,但想起刘羲纬对自己每况愈下的印象,还是强迫自己闭住嘴,只是狠狠瞪了一眼她的背影。
息雅见刘羲纬虽面色惨白,但周身无明显的重伤,心中稍安,这才命人去准备参汤,自己则留在他身边,亲手为他更换被划破了的衣服。
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却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馨和亲密。
刘羲纬深情地望着为他细细擦拭脸上泥污的息雅,似已痴了。
他看得出她内心的挣扎,看得出她的摇摆,但更看得出她眼中流露的发自肺腑的关心和柔情。他知道她内心的坚冰已经开始融化,他终于可以跻身其中。这么多年,他的痴情终于得到了回报。
息雅为刘羲纬擦完脸,将他的外衣脱下,惊叫道:“你的胸口怎么被划破这么一大道口子?”
刘羲纬笑道:“没关系,只是皮肉外伤,擦些药粉再辅以内力,不出一日就可以痊愈了。”
息雅嗔道:“血都染红小衣了,还说没事。那些军医是干什么吃的!”说着就要起身去唤人。
刘羲纬拉住她,柔声道:“不要叫军医,我看见他们那些橘子皮脸就头疼。药膏就在桌子上的药箱里,白色的那一瓶。你给我上药好不好?”
息雅点点头,取了药膏,正要替他把小衣也脱下,眼睛却猛然被小衣上的并蒂桃花所吸引。
花开两朵,并做一枝。天长地久,此情不逾。
被他失手掉在桃溪谷、又被她千辛万苦捡回的并蒂桃花,被她珍藏身边、伴她孑然多年的并蒂桃花,她本欲烧毁却下不了狠心、最终抛弃在风中的并蒂桃花,蒙了血污的并蒂桃花,前尘旧梦的并蒂桃花。
息雅的脸渐渐失去了血色, 如春末即将调离的桃花。她脑子里顿时一片澄明。
雍国除了秦柔和项重华,谁还有本事在刘羲纬的胸口上留下这么大的一道伤痕?秦柔正独守在雍国寂寞的凤藻宫里,不可能来前线。
所以……
刘羲纬也如同从暖春一下堕入寒冬,隐约猜出了秦非为何非让他穿上这件小衣,并自信他一定能胜过项重华。
息雅颤抖着抬起头,看向刘羲纬,目中的担忧和恐惧再也无处匿身。
刘羲纬心如刀割。他知道,这份担心已经不再是为他的了。
他强迫自己的眼泪不要渗出,保持着骄傲的微笑,尽量轻描淡写道:“他输了,但没有死。”
息雅的心落了下来。
刘羲纬咬牙一字字笑道:“但也活不久了!”
秦非刚刚将被袁柘削断的头发打理好,便被刘羲纬的亲卫兵接到了他的营帐之中。
刘羲纬已经换了一件便装,倚坐在小几子旁喝酒。
亲卫兵将秦非带到后便立即退了出去。
刘羲纬只是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看都不看秦非一眼。
秦非行完礼便拱手而立,也一言不发。
不知过了多久,刘羲纬终于将壶里的酒都喝尽,他拿着空酒壶,摇摇晃晃走到秦非面前,淡淡地道:“那件小衣是怎么回事?”
秦非不卑不亢地道:“陛下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刘羲纬红着眼道:“你说呢?”
秦非郑重地给刘羲纬行了一个礼,回答道:“臣遵旨!臣为陛下献上的这件小衣,的确不是什么请巫咒师施了法术的宝衣,但它可以保陛下险胜。因为,那件小衣胸口上所绣着的并蒂桃花补是息夫人与雍王昔日的定情信物,被夫人丢弃,却恰巧被臣捡到。雍王剑术刚烈迅猛无畴,与陛下阴柔刁钻的路术相克,往往取胸口突破。项重华对息夫人始终无法忘怀,只要他划破外衣,见到这并蒂桃花,定会走神。而陛下,则可以趁机取其性命。”
“当”的一声,刘羲纬手里的酒瓶被重重砸在秦非的身上,弹落地面,粉身碎骨。
刘羲纬目眥欲裂,一把揪过秦非的领口,红着双眼,狠狠地道:“谁准许你这么做的!你难道以为,我用这种方法赢了项重华,就会开心吗?”
秦非面无表情地抹去了脸上的酒水,淡淡地道:“陛下是臣的君主,不是臣的朋友。臣只负责陛下的胜败,不负责陛下的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