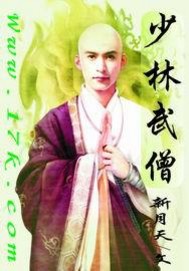涛儿道:“曹姬今日胃口不佳,自从午后就未吃任何东西,直到晚上才只是吃了些夫人送的点心。若非夫人在背后做靠山,解语区区一个宫人有这胆子下毒吗?”
息雅怒道:“你血口喷人!我有什么理由害曹姬!”
涛儿道:“那可不一定。您和曹姬都有孕在身,万一曹姬生下王子,岂不是您的威胁?”
息雅道:“你,你……一派胡言!”
曹姬也开了口,哭道:“难不成夫人认为,妾会害自己的骨肉吗!”
息雅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抱着解语,仿佛生怕旁人将她抢走。
涛儿道:“夫人送来的糕点,我家主子只吃了几口。您若是愿意当着大家的面,将它全部吃完,我们就立即向解语姑娘磕头认错。”
知秋和解语双双叫道:“夫人!”
息雅的心沉了下去。曹姬果然备好了后招。再次端上的点心里一定已经下了剧毒。她若不吃,就是不打自招,可若是吃了,也只会中毒。纵然能勉强洗掉嫌疑,孩子也万万保不住了。
刘羲纬从解语身上拉下了她的满是汗水的手,低声道:“够了。”向侍卫使了一个眼色,侍卫会意,上前就要拖走解语。
息雅大声疾呼,一把推开侍卫,奔到涛儿面前,道:“点心在哪儿!”
曹姬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笑意。涛儿已经端来一盘点心,放到息雅面前。
刘羲纬脸色一变,上前一把打掉息雅手里的点心,喝道:“你要干什么!”
息雅道:“我要证明解语的清白!”
刘羲纬喝道:“荒唐!给我回去!这件事交给我处理!”
息雅叫道:“我回去了,就再也见不到解语了!”
刘羲纬双目通红,道:“你就这么不信我?”
息雅哭着叫道:“不信!我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刘羲纬恍然错愕地看着息雅,随即目中充满了痛苦。
解语看了看满脸得色的涛儿,又看了看泪如雨下的息雅,冲到了桌前,拼命地往嘴里塞点心。
息雅想要去拦她,可已经太迟了。
解语吃完了最后一块糕点,转头看向涛儿,道:“现在,我清白了吗?”
涛儿瞪大了双眼,看着从她嘴角缓缓流出的黑血,一个字也说不出。
解语回过头,向刘羲纬行了个礼,道:“纵然奴婢不清白,夫人也绝对是清白的。请陛下相信夫人。”言毕喷出一大口鲜血,栽倒在地。
息雅惨叫一声,扑过去抱住了解语,大哭不已。
涛儿却依然不依不饶,叫道:“陛下明鉴!这点心里的确有毒!解语她不过是想把罪名都揽在自己头上,她……”
刘羲纬一个甩袖,涛儿只觉一股巨大的劲力猛然袭来,身体被狠狠冲到墙上,接着便听到了周身骨骼依次断裂的声音。
刘羲纬抱过解语,手指在她脖颈、胸口连点几处大穴,向知秋道:“去寡人的殿里取来硝苓丸,合着蜂蜜水让她喝下!快去!”知秋立即去了。
曹姬看着奄奄一息的涛儿,脸色骇得连一丝血色都没有。
刘羲纬道:“曹姬服毒后一个时辰才毒发,而解语刚刚吃了点心就成了这个样子,可见她们中的并非是一种毒。”目光缓缓看向浑身战栗的曹姬,又转向了涛儿,道:“曹姬自然不会毒害自己的孩子。最有可能下毒的就只剩下身为贴身侍女的涛儿 。”
涛儿挣扎了几下,很快就没有了气息,被侍卫拖了下去。
刘羲纬走到曹姬榻边,伸手摸向了曹姬冰冷的脸。曹姬只觉他的手比自己的脸更冷,不禁打了一个哆嗦。
刘羲纬道:“少动些脑子,劳神过重的人往往是活不久的。”
曹姬只觉这寒意顺着脸一直蔓延到了全身。
刘羲纬道:“起驾回宫!”转身向门口走去,连看都不看息雅一眼。
息雅用凤辇将解语载回寝宫,知秋恰好赶回,并带回了一个御医。解语服了药后,便开始狂吐不止,后来竟然吐出了血,息雅吓得花容失色,几欲晕倒。
御医忙解释道:“夫人不必害怕,解语姑娘吐出来的都是毒物和毒血,吐得越多反而好得越快。”
息雅颜色稍解,道:“那她是不是没事了?”
御医看了看解语,垂下了头。
知秋急道:“您再这样支支吾吾的,好人也要急病了。解语她到底怎么样了!”
御医叹了口气,低声道:“解语姑娘吞下的毒物过多,再加上她身体本身就虚弱,所以虽保住了性命,但……”
知秋道:“但是什么!”
御医声音更小,道:“但是恐怕今后,都不能说话了。”
知秋连退几步,幸亏被其他宫人扶着,才没有摔倒。
息雅放声大哭,扑倒在解语的身上。
御医道:“恕老臣直言,莫说是身子虚弱的女子,纵然是壮汉,服了这么多的毒,也难保性命。解语姑娘能活下来,已经实属不易了。”见息雅依旧痛哭不止,躬身道:“解语姑娘现虽无性命之忧,但气血紊乱,急需调理。臣现在就给她开两副补身药,夫人意下如何?”
息雅置若罔闻。知秋含泪对他道:“那就劳烦您老了。”
御医开完药,如释重负般逃了出来,连灯笼都来不及打,没跑几步,便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竟然是刘羲纬的贴身侍卫。
御医忙寻着刘羲纬,撩袍跪地行礼,刘羲纬却抬了抬手,示意他不要出声。往来呼啸的北风零乱了他的大氅,几欲吹散了他的发髻,他却依旧痴痴地望着息雅寝宫的窗子里发出的灯光。
南地的冬虽不似北地苦寒,但一入夜,也是冷得彻骨。何况,南地的人也不会像北人穿得那样厚实。两边的侍卫虽仍站得笔直,却已经在瑟瑟发抖。刘羲纬却俨然成了一座冰雕,纹丝不动。
御医冷得几乎要受不了,但祁王的冷酷更令人畏惧,他咽了口唾沫,想略略移动一下位置,却觉脚都几乎被冻到了地上。风更冷了,零落的更鼓自远方传来,恍如隔世般遥远。
御医一咬牙,决心借解语的病情脱身。他鼓足勇气,刚要张口,刘羲纬却吐出了一口白气,道:“她怎么样了?”
御医忙道:“解语姑娘已无性命危险,只是身子尚且虚弱,而且,恐怕以后是不能说话了。”
刘羲纬不耐烦地道:“论起毒,还轮不到你给寡人当师父!寡人问的是息夫人!”
御医吓得冷汗直冒,颤声道:“夫人一时还接受不了解语姑娘失声的事实。不过夫人向来豁达明智,一定很快就会想通了。”
刘羲纬默然半饷,道:“若她伴着的是项重华,秦非一定有办法彻底解了解语的毒。”苦笑道:“不!他压根就不会叫这种事情发生。我真没用!”
御医第一次听得刘羲纬以“我”自称,好奇之下抬头看向他,但见他徐发零乱,神色黯然,往日的霸气冷酷一扫而光,双目充斥着说不出的凄凉之色。御医虽怕极刘羲纬,此时心中也不由升起一阵怜悯之意。
息雅窗口的灯终于熄灭。刘羲纬也转过身子,一边向龙辇走去,一边吩咐道: “好好照顾解语,还有息夫人。”
御医忙称诺,想起一事,开口道:“陛下您看曹姬那里……”
刘羲纬脚步一顿,道:“宋御医擅长医治孕婴,让他照顾曹姬就行。你只要把息夫人这里照顾好就行,其他事不用多想。你身为御医院的翘楚,自是最应该明白医者的责任和尊严。寡人讨厌后宫争斗,更看不得其他人跟着瞎掺和! 曹姬丧子,寡人也甚为痛心。你们都给寡人伺候好了,再出岔子,寡人就给御医院换血! ”言毕撂下瑟瑟发抖的御医,登上龙辇。
远处奔来一个黑衣侍卫,见到刘羲纬的龙辇也不停步,直直冲了上去,跪倒在地。
刘羲纬示意停下,向黑衣侍卫道:“可是令尹来了吗?”
侍卫拱手道:“令尹在御书房侯驾,说是有要事禀报。”
刘羲纬立即跳下龙辇,施展轻功,赶到了御书房。
袁柘行礼完毕,摒退了侍卫和宫人,向刘羲纬道:“郑既吃了败仗,没有拿下婺城。韦松君也被守城将领杀了。”
刘羲纬怒道:“祁军已经从韦松君手里占了婺城外关。婺城没了天然屏障,人数又远少于我军,纵然有青龙山的奇器巧械,也无济于事。郑既那个废物是怎么攻的城!”
袁柘道:“此事也怪不得郑将军。我方将士在交战当夜,集体中毒,死了大半。郑将军自己也差点被毒死。”
刘羲纬一掌将砚台拍得粉碎,双目通红地高声怒骂道:“饭桶!一群饭桶!寡人要这么一大帮子酒囊饭袋有什么用!还不如去喂上几条激灵好使的狗!身为白虎门掌门的臣子,自己居然栽在了毒上,还有脸说!他们的巡视士兵是干什么吃的!那么多的粮仓被下了毒都不知道吗!”
刘羲纬平息了平息怒气,把声音压低,问道:“心呢?心那边有没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