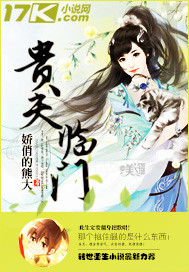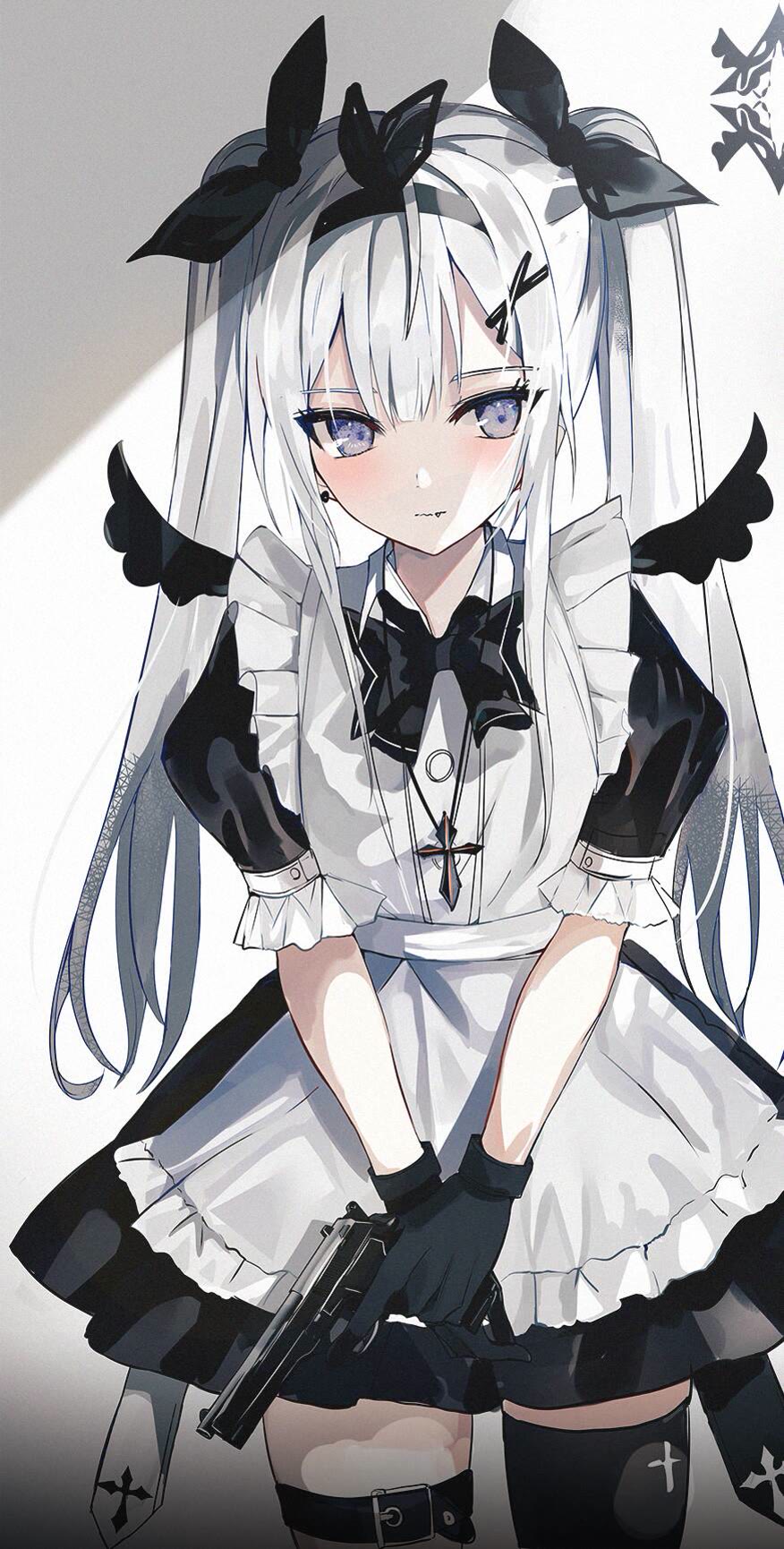“老太君说的哪里的话儿?奴婢还要跟着您,再伺候您五十年呢。”
老太君年纪大了,越发的喜欢听这种话,心里舒坦了,脸上的笑容也就真切了,拉着姚妈妈的手拍了拍,道:“这些年来,也亏得你是个明白我的人一直在身边陪伴着我,否则我都不知道这一路要找谁去说这些知心的话去。那些个兔崽子们,一个个的就只会惹我生气。”
想起这个,老太君忽然就想起当日曲太医处来诊治她时,白永春那恨不能让她真的脑袋受伤的模样好蒙混过关。老太君也是有一些心凉。
那样的儿子难道能够指望他要紧关头为了这个做娘的考虑多少?他不将她拆了剁了就算不错了!
老太君的面色阴郁,喃喃的道:“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这白家的男人,真真都是一个德行。”一想亡夫,自己也打心底里倦怠了。
姚妈妈看老太君的面色,也知道她心里在想一些什么,当即也不多开解别的,只道:“老太君素来豁达,早前您不就说么,人这一辈子,总要什么困难的事都经历一番才是完满的,您这般阅人无数,早就看开这个道理了。老奴就只求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安稳一辈子,老奴只求能陪着您一起老去就好了。”
即便他们是主仆关系,能有一个人了解自己的一切,陪伴自己身边,老太君也是觉得欢喜的,她心中的怒气和失望也就渐渐地散了。
姚妈妈就服侍了老太君歇着。
待到老太君睡熟之后,这才安排了上夜的丫鬟来睡在外间,往后头自己住的抱厦去。
躺在炕上,翻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姚妈妈心事重重的摸了摸自己的枕头。那枕头的侧面有一处仔细摸起来比别处要厚一些。里头藏着的是她这些年来积攒下的体己钱。她都已经兑换成了银通票号的银票。
她这样冷眼看着,侯府在原来的主子手里怕是太平不了,保不齐自己这个一心护主子的忠仆,到日后还会成了赢家手里羞辱老太君和侯爷的一颗棋子。
姚妈妈一这么想,就觉得浑身肉疼。已经是年过半百,黄土埋进去半截儿的人了,一心一意的服侍主子,成婚后依旧还住在主子身边服侍,为的就是给家里人攒下一些家底儿,让儿孙们不必在去做服侍人的奴才。
好不容易混的快到了容养的年纪了,好死不死的却摊上了这么大的事,偷换皇子,欺上瞒下,这些事她听着老太君的吩咐样样都没有少做过,待到他日事发,她或许葬身之地都没又,闹不好还要带累了儿孙。
姚妈妈的丈夫如今在外面田庄上带着一家老小过活,生了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如今也都做的是正经事业,虽算不得大富大贵,好歹也是小康之家。
这样的平静日子,让她知足又不知足,人心不足,日子过的再好也是想更好的,而儿女双全一家子平安自给自足也是她知足的。
她就想着,在老太君身边伺候多赚一些,也好多帮衬儿孙一些。
想不到啊想不到,她这么老实的一个人,老年了居然要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万一因为老太君的事耽误了她家人,那她真是死一万次也不够了。
姚妈妈抓心挠肝的一夜没睡好。
次日清晨服侍了老太君盥洗更衣,又服侍了早膳,姚妈妈就笑着道:“奴婢去给您请个靠得住的大夫来可好?”
“嗯,我这毛病太医未必能看好,也就这样吧。”老太君点头,让姚妈妈自己去开箱笼取了老太君的体己钱去外头请个好大夫来。
姚妈妈按着吩咐做了,就举步出了门,到了外院叫人套车。
她所乘坐的是一辆仆人用的寻常蓝帷小马车,盘膝坐在里头,因一夜没有睡,这会子晃晃悠悠的反而觉得昏昏然快要睡着了。
也不知她是睡着还是没睡着,更不知是过了多长的时间,姚妈妈忽然觉得身子往前一趴,险些从骤然停下的马车里掉了出去。
姚妈妈吓的不轻,三魂七魄都快飞了,一手撑着车墙壁喘粗气,高声骂道:“作死啊!赶车不会看着一些路吗,这样忽然停下来是想摔死我不成?!”
话音方落,就听见外头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那声音极富有磁性,虽略有些沙哑,但只听轻轻地咳嗽,便可判断那咳嗽的男子应该是个声音温润的年轻人。
姚妈妈心里打鼓,隐约觉得这人自己该是认识的,猛然掀起车帘,一瞧见眼前那人,当即惊的瞠目结舌,怎么下马车都要忘了。
那人一身淡蓝色茧绸直裰,墨发挽起,身形高瘦,容貌俊秀中带着一些病态,却并不显得女气,而是气质高贵但又冷淡疏远。
这么一个人,沐浴在晨光之中,俊美的宛若天上下凡的谪仙,就连以帕子掩口咳嗽的模样瞧着都令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姚妈妈看的心里一震,呆愕住半晌方找回自己的声音:“世,世子爷,您怎么……”
白希云已收好帕子,笑着道:“特地在此处等姚妈妈,有些话想与你说。”
姚妈妈看看左右,这马车趁她方才不注意时已经驶出了城门到了城郊,远山近河,小道羊肠,右手侧就是一条大河,四周皆无人家。
这一看就是个毁尸灭迹的好地方啊!
若是有什么话回的不对,保不齐今日就要扔在这里了!这么说,刚才赶车的人也是世子爷都安排好的了?
姚妈妈心念电转,就已经分析出情况,一下子浑身冰冷,背脊上的汗毛都一根一根竖了起来。人还在车上,已经能够感觉到那河水没过头顶的窒息和绝望了。
白希云唇畔含笑,道:“不知姚妈妈可否赏脸,与我去那边说话?”指了指河边一处草地。
姚妈妈吞了口口水。
她能说不吗?
犹豫之下,看了看白希云身旁跟着的那个穿红衣的公子,据说这人是二皇子身边得力的,定然是武功超凡吧?在说白希云身后还跟着五六个汉子,各个看着都不弱。她若敢说不,会不会直接就被人扔进河里去?
姚妈妈脸上挂着笑,尽管冷汗已经要浸透了她的衣裳,依旧是冷静的下了车,笑道:“世子爷的吩咐,奴婢哪敢不从?您有什么话请尽管吩咐。”
白希云似笑非笑道:“姚妈妈是聪明人,这就好办的多了。也免去了一些无谓杀戮。”
杀戮?!
姚妈妈面色惨白。
白希云没事人一样缓步走向河边,身边就只带了管钧焱一个。
姚妈妈则是苦着脸,在众护卫的注目礼中去了白希云身畔站定。
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姚妈妈依旧端着世家老仆的风度,礼数周全的道:“世子爷请吩咐。”
白希云看着湍急的河水,缓缓道:“姚妈妈可知道这条河会流向何处?”
“老奴,不,不知道。”一滴汗自额头滑落到鼻尖,低落在墨绿色细棉布衣襟上,变成了一滴近乎于黑色的痕迹。
白希云又道:“其实我也不想姚妈妈知道这河水流向何处又有多深多冷,甚至不想你知道这条河里是不是有鱼。毕竟您也是跟着服侍老太君一辈子的人了,家里也是一大家子,少了你一个,家里断然不成个样子了的。”
“是。世子爷说的是。”
“所以今日问你的话,你要实话实说啊。”白希云笑着道:“姚妈妈是聪明人,心思缜密,又懂得审时度势,自然可以看得出以后侯府的走向,也可以看得出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正在将自己往绝路上引。”
倏然抬头看向白希云的背影,姚妈妈的心里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是知道了什么?
刚才这一番话是已有所指,还是无心之言?他说的只是侯府之中这些年来的乌烟瘴气,还是在说老太君和安陆侯夫人竟然将二皇子的身世告诉了他的事情。
姚妈妈很想在白希云的脸上看出一些情绪,也好做出判断,是以她缓步上前到了白希云身畔。
白希云听见脚步声自然而然的回过头来。
姚妈妈趁机打量,却只看到他俊秀的脸上似笑非笑高深莫测的神情。
这般无懈可击,到底是与白家人不一样。
姚妈妈仔细想了想,忽然之间一个事实再度冲到自己脑海里。
面前站着这位病弱的世子爷,实际上却是龙嗣啊!若是当年没有换子一事,现在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就不在是二皇子,而是面前这个人!他才该是皇帝的儿子,才该是姓陈名禹表字天佑的二皇子啊!
姚妈妈思及此腿上一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您,世子爷,您有什么事儿但请吩咐。奴婢绝不敢有半分推诿。是,奴婢的确是看出了一些事,跟在老太君身边也必然会知道一些事,可是这些事情都是与奴婢没有关系的啊!奴婢只是个下人,家里也有老小……世子爷想要奴婢做什么,或者想从奴婢这里知道什么,奴婢都可以据实相告。只求世子爷千万不要迁怒于奴婢的家人!”姚妈妈说着,就连连磕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