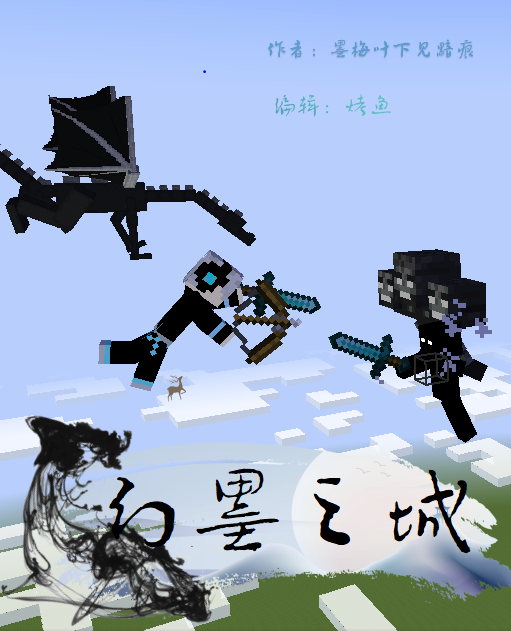随着“当啷当啷”的声音那些东西几乎散落一地,顿时屋内的人气息一紧,注意力都转移到了那小堆东西上,反观谷雨却是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他立时快走了两步,矮下身子将那些掉出来的东西又勉强重新快速的塞入那个还有些破烂的布包里,然后起身到床边动作自然的将它塞到那人枕着的枕头下面,但东西刚刚塞好便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刚刚离开不久的那道熟悉的声音又再次飘起。
“客官,客官,您慢点,您这样,您这样不太合适…额…”却又像是只突然被杀死的鸭子,声音在一瞬间就被阉割,屋内也因此变得安静而戒备。
“碰!”的一声,门被突然的打了开来,强烈的阳光从打开的门中直射入门内,也似乎是因为光线的强度,那进来人的长相竟然一时不能让人辨识出来,直待他迈着四方大步又向前晃了晃,一把尚在鞘中的大刀随着动作在他的身侧斜斜地向前一横,粗眉,星目,黄铜色的脸颊不带一丝笑意,方正的下颌微微抬起,同时其余的脚步声则都截在了门外,看似鲁莽却又稳极。
“咳咳,”只有刚刚被掐断的小二的声音又再响起,看向这里的目光似乎也带着一丝为难,心中却又重新掂量了谷雨之前给的银子。
“嗯!”那人清了清嗓子,在要开口前扫视了屋子里剩下的所有人后,将目光更多的停留在了床上的人,他毫不顾忌的简直过去,将那遮住了那人大半面孔的头发扫开,顿时神色间一片放松,然后看向了屋子里仅剩下的一个似乎可以做主的男人,抬了抬眼皮盘问道
“先生何许人也?”
在见其一番作态后的言论后,谷雨微微皱了皱眉,还未答道,那刚刚的动作便似乎被人注意到了,一道声音从门外传来,语音温润而明晰如玉击环。且随着他渐近的脚步,让人听得越发明晰。
“先生,现下您床上躺着的这位是我们府上的贵客,因昨日府内意外受袭而不知其下落何处,故而多问几句,也望先生勿怪。”随着声音的停止,那人一身褐色衣衫缓步向前,又最终停留在刚刚那个男人身后。
听必谷雨面上颜色稍缓,点了点头,接道
“无妨,在下为清玄居的谷雨。”话音未落便见那个褐衣的男子眸中似乎快速的闪过了什么。然而谷雨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遇到的太多了,他并未做出其他反应,只是继续说道
“昨夜城中大火,我恰巧遇上此人,见他深受重伤,思及性命为大,故待诊断一二,如有不妥,二位可带人自行离去。”
听此言,那之前的人正要去带人,却忽觉衣摆处一紧,正要问及,便听身后的褐衣人道:
“如是自然是呆在先生这里更好些,只是久未相闻,不知云老可还安好?”
谷雨略带疑惑的看了看对面,回道:
“呃,先生可有记错,我清玄居并未曾有叫云老的人啊。”
却看那人只是笑了笑仿佛得到了什么满意的答案,退回到先前那人的身后,在那人跟前耳语了几句,那人便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那个褐衣人,那道温润的声音便又再响起道:
“谷先生,我们阁内此次遭袭至今事情还未有定论,故只能暂且将宗政先生托付与您,这封信也烦您在他醒后交付与他,事后玲珑阁必有重谢。”说着,一揖到地。
让谷雨一时倒慌了手脚,还未等再回些什么,那一行人便又都像来时那样快速的退了出去。徒留谷雨一脸难色,待回头看向那个烦恼的源泉时,发现之前还有些呆呆的沈千亦已经从突然被自己卖了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现在正半蹲着身子面冲着榻上的人伸出手指,执着又坚定的戳着那个伤者的脸颊。
“你……”谷雨话刚开头,便听到刚刚一直沉默到竟然几乎要让人忽视成背景的女人接了一句。
“他醒了。”声音平淡而笃定。
再看那人时,发现沈千亦已经起身挪开,也让人更加清晰的看见他已然睁开了双眼,面上却丝毫没有被抓包的尴尬,他一手撑着床,勉强的要撑起身,却在身体扭动的一瞬咬紧了牙关,冷汗冒出,见此谷雨忙上前了两步扶住他,让他能维持平衡又不会二次伤及,而他也在搭上谷雨的手臂的同时神色百转。
“先生,我是浦阳派掌门宗政濮,此番多谢先生相救。然恐怕因昨日之事,或已累及先生,不知先生现时有何打算。”宗政濮抬头看向谷雨时,平日上挑的桃花眼也带上了一丝严肃。言谈中语音很是诚恳,面色中也似乎透露着一丝急切。
“呃,我且未定,不知宗政掌门又有何安排呢?”正说着,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谷雨将那离开的褐衣人留下的信拿过,交与宗政濮。
宗政濮毫不迟疑的接过后,一目十行快速读完,便抬头看向谷雨的同时将那信件翻转给谷雨观看,同时道:
“先生,我未曾料到此事会出现如此大的后果,但现在先生因与我接触恐有伤及,此为我所不愿之处,”语音一顿,正待继续时,看到不知何时出现在眼前看着信件且随着自己话语一本正经的点头小女孩,忍不住嘴角一抽。却又马上回转,淡定的把手放到沈千亦的头上揉搓了两下,顺便将她挪偏了位置,继续道:
“先生不若随我到玲珑阁暂且安顿一二,我昏迷前已然放出信息不出三日我派人必到,到时先生可选择是留下还是随我看看水东景象。便是先生不愿,也请先生随我且留几日,待一切落定后再做他选。”手指略略拂过路上就被上过药的地方,接着道:
“我浦阳派虽非大派,但也不愿见曾对自己有恩之人受自己拖累。”
“这……”谷雨刚要作答,突然似又想起了什么,回望了眼那个女人,却看那女人仿佛什么都未曾听到一般用碗盖拨弄着茶碗里沉浮的茶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