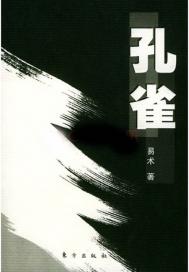那一天,我搞到两张中国剧院的票,上午就和老K说好了,晚七点我在剧院门口等他。
不到晚七点,我便在剧院门口引颈张望了,手持戏票的男女们三三两两地开始入场了,我还没有见到老K的影子,心里就骂一句:“老K你真他妈的。”骂完了,老K仍不见人影,我手里捏着两张票开始在剧院门前的空地,上踱步,一边踱一边看表,免不了在心里又把老K骂了一句。
天渐渐地暗下来了,街灯已燃亮,此时正是春天黄昏那种时刻,我一遍遍抬起头,向马路上张望,我身边的人流早已稀薄下去,隐约地听见剧院预演的铃声已经响起。手里的两张粉色戏票在春风中发出细碎的响声。我不再望马路,去望剧院门前的广告,广告上醒目地写着“灵魂飞向天国”的字样,我知道那是今晚将上演话剧的名字。我想再等一会儿,老K再不来,我就他妈找老K算账去,就是他跑到天国也要把他找到。
我正这么乱七八糟地想着,突然一种柔媚光明的声音在我很近的地方响起:
“你好,让你久等了。”
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正娇好不安地冲我笑着。我怔在那里,眼前的女子我似乎见过,却一时又想不起来。我嘴里本能地“啊啊”着。
“我们进去吧。”
“进去?”我很蠢地这么问了一句。
“已经开演了。”她带着歉意地说。
“走吧。”我仍糊涂着。
接下来,我便脚轻脚重地往剧院的人口处走,她走在我的一旁,脚步轻盈敏捷。当走进剧院时,戏的确已经开始了,在服务员手电的引导下,很快找到了我们的座位,我坐在座位上,却仍不知身在何处。
过了一会儿,她说:“老林还好吧?”
“老林?”我这么一问,马上想到写剧本的老林,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但仍然说:“他还好。”
剩下来,她便不再和我说话了,目光入神地盯着舞台上的演出,脸上的表情随剧情丰富着。
我就想,见鬼了,一定是见鬼了。没等来老K却等来了一个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我仔细地想着,我就约了老K一人,没有再约过什么人呢,况且身边这个女人我又不认识,不可能也一同约了她。这么想着,我就定睛去望她,舞台上背景灯光反射在她的脸上,一时间,显得她一张娇好的脸很朦胧,也越发的楚楚动人。她似乎发现我在望她,她很快地看我一眼,冲我笑一笑说:“这剧真不错,看剧吧。”然后又扭过脸去,入神入境地看剧了。
我却一点心思也没有,心里又一次咒老K,老K你说来不来,却冒出一个女人坐在我身边,这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就想到了老K:老K比我还大两岁,写诗已经很长时间了。老K人生得很瘦小,一点也不和他的年龄相配,老K没写诗时,生着一头又乌又浓的头发,自从他开始写诗,头发便日渐稀疏,最后头顶上的粉红色头皮已清晰可见,老K的诗却愈写愈惆怅缠绵,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疯了的爱情》,我记得有这么几句:爱情的旗帜扛在疯子的肩上/疯子在广场上奔跑/把爱情挥洒得在大街小巷里流传/疯子说饿了/拾起行人扔给他的面包/他说这世界太可爱……老K至今仍没结婚,老K现在是个体户,专门给报纸副刊写稿的那种个体户,老K的烟酒钱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手段所得。
我不明白身边的女人是不是老K的什么伎俩。老K知道我现在正和老婆分居,会不会是老K在考验我的意志?想到这,我又瞥一眼身旁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确长得无可挑剔,年轻漂亮自不必说,起码和我老婆的姿色不相上下。这时,我就想,老K你他妈太小瞧我了。
转念我搜肠刮肚一想,老K的一些女朋友女哥儿们我都见过,在这一点上老K从不瞒我什么,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身旁这个女人。是不是老K背着我还留了一手什么。我又一次发现老K的狡猾多端。以前老K还写诗的时候,我们一见他日渐稀少下去的头发就说:“热闹大街不长草,聪明脑袋不长毛。”我们这么念叨时,老K就骂:“妈那个X,谁聪明人写诗?!”
我正胡思乱想着,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剧院的灯突然亮了。人们热烈地向出口走去。我一时有些发怔,舞台上我看了几眼,却一点也没记住任何什么细节,我很愚昧地说:“完了?”“完了。”她说。
我们俩在人群的最后面往外走,我走在前面,我本意应该是我和她并肩走出去。但我没那么做,我想老K此时说不定正躲在什么地方手捂着嘴巴偷看着我,我不能让老K小瞅了我。一直走出剧院门口,我仍没有发现老K。这时她已经和我并肩走在了一起,她见我左右张望便问:“你等人么?”我装出无比镇定的样子说:“没,没有。”
我走在大街上,老K仍没有出现,她一直随在我身边走着。我想老K一定会出现,结果老K没有出现,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些什么。看样子她并没有马上离我而去的念头,此时已经是夜晚,街上的行人稀疏寥落。几对恋人,躲在树下的暗影里喁喁低语。我和她在大街上伫立一会儿,突然想到了酒。酒是我和老K公认的好东西,一喝上酒便把什么都忘了,晕晕乎乎舌根发硬地说一些人不人鬼不鬼的话,于是什么便都没有什么了。我一想到酒,就有些激动。便偏过头建议地冲她说:“走,咱们去喝酒吧。”她没说什么,只是冲我浅笑了一下。便跟着我,横穿过马路,向对面几家酒馆走去。
我们坐下的时候,突然我就生出要报复一下老K和她的念头,便有些恶狠狠地说:“喝白酒。”她仍然不说什么,垂着头看自己的手尖,我这才注意起她那一双手,那是一双秀长优美无比的手,在灯光下闪发着一种圣洁的光芒,我的心就颤了颤。但我却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望着一排霓虹灯变来闪去。
酒菜很快上来了,我把自己的杯里和她的杯里都倒满酒,便举起杯子说:“干,为了今晚。”她端起杯子,目光里是无所畏惧的样子,脸上依然挂着浅笑。我喝完一杯的时候,她杯中的酒也丁点不剩了,这样我心里陡然生出几分感动,心想,老 K还有这么一个讲义气的女哥儿们。我差不多快为老K幸福了。
一连气,我们各自喝了五杯之后,我快把老K忘在脑后了。此时只有她和我。
“今晚真不错。”我说。
“就是。”她笑一笑。
我又给她杯里倒满酒。
“你还挺能喝的呢。”我说。
“我今晚这是第一次喝酒。”她真诚地说。
“那好,咱们再干。”我又举起了杯子。
“干。”她说。
“你真行。”我说。
“我也不知自己这么能喝酒。”她说。此时,她的两颊已一片绯红,目光里波光流萤。我心里陡然又想起老K。
“老K真能耍花招。”我说。
“老K是谁?”她说。
我笑了,很世故地望着她。
“你们别涮我了,你当我是小孩子?”我说。
她真的一脸惶惑了。
我就有点发怔。
过了好久,她说:
“我没涮你。”她的眼里似乎有泪花在闪动。
我的心又抖了一下,掩饰什么似的,一连干了三杯。
她说:“别喝了,你要醉了。”
我说:“你叫什么?”
她怔着眼看我,半晌说:
“我叫朱美呀,你真的醉了。”
她那神情,好似我们已认识了八百年似的。我愈加糊涂不安。
后来,我就真的醉了。
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我已经说过,我自从和老婆分居,我一直住在单位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和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大学刚毕业时,分到这个单位我就一直住在这间办公室里,直到我结婚。当我结婚满了一年又一个月时,和老婆分居,这又成了我的老巢。
我躺在床上,望着静静的阳光暖烘烘地照在靠窗边那几张办公桌上,桌子上落满了灰尘,那些灰尘也静静地浮在那,恍似这个世界静止了。模糊中,我又依稀记起昨天晚上的一些事儿来。想到昨晚便想到了她,那个叫朱美的女孩,她是怎么走的,我自己又是怎么回来的,这一切全记不得了。难道这一切全是梦,我又想到了老K,我想找到老K什么便都会清楚的。我从床上爬了起来,这时才发现自己头疼欲裂。我坚持着走到厕所,想洗一把脸,拧开水龙头,准备用手去接水时,这时,我才发现我左手心里写着一排隽秀的小字:
你醉了,下星期早八点我在紫竹院南门口等你。朱美。
我一看到这一行字,差点叫了起来。我又一连看了几遍,待确信无疑了,才想起昨天的一切不是梦,热血在周身上下翻腾了几次,这才想起洗脸。
洗完脸我第一个想见的是老K,我想验证这些把戏是不是他一手导演的。
老K住在离公主坟很近的一条胡同里,胡同里有一排平房,倒数第二个门就是老K的房间。我来到老K门前时,看见他的窗帘仍拉着我挥起拳头砸门,砸了一会儿听见老K有气无力的声音:“我操,是谁这么用劲。”我说:“是我。”老 K听出了我的声音,“呱叽呱叽”穿着拖鞋往屋门口走来。他一打开门,一股酒气迎面扑来,老K只穿了条裤头,赤条条地立在门旁,他的两只小眼睛红肿着,冲我一副非常抱歉的,样子。我说:“老K你是怎么回事?”
他摇晃着走到床前开始穿衣服,我清楚地看见老K瘦小的前胸上的根根肋骨。我心里什么地方动了一下。
他说:“别提了,我昨天差点没喝死。”
我说:“你跟谁喝?”
他说:“自己呀。”
我说:“昨晚看戏的事你忘了?”
他这时已经穿好了裤子,冲我苦恼地笑着。
“没喝酒前记得好好的,喝完酒什么都忘了。”
他又开始穿上衣。
我说:“你认识朱美吧?”
他睁大眼:“谁,朱美?”他摇着头。
我说:“你别跟我演戏了,昨晚的事。”
他说:“操,咱哥儿们什么时候和你演过戏,你他妈还不知道我?”
我真的知道老K。我自从大学毕业就认识了老K。十几年来,从我认识老K的那一天起,我们便成了哥儿们。虽说彼此之间,偶尔也幽默一下,但还从来没有玩过这样过火的事。我知道这些日子老K的心情很不好。老K是改革后第一批合同制诗人,第一次签的是三年。第一个三年过去了,老K没能兑现合同上的一些项目,比如三年中每一年必须得有一部 (首)作品在全国有反响。老K写了十几年的诗,从来没有什么大反响,这三年的合同中也不例外,下一个三年时,老K便失业了。领导再也不同意和他签合同了,老K便成了个体户。从此老K不再写诗了,而成了诸多报纸的撰稿人。各种花花绿绿的小报四版上,都有老K化名“郁金香”的文章面世。“郁金香”的文章都是一些奇闻轶事,男恋女欢,吸毒、赌博……老K就非常痛苦,经常约我喝酒,每次喝酒大都是他付账。他说:“别看是个个体户,比以前写诗强多了。一个月发两篇小稿,就够了。”
我就说:“那以后呢?”
他说:“谁知以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活一天算一天吧。”
他一边说话时,就一边用手胡噜脑袋上稀疏的几根头发,两只小眼里流窜着无奈的光亮。然后就感叹:“人呢,真他妈不容易。”
老K年轻时曾经如火如荼地火爆过,他经常夹着自己新出的诗集,在各种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出没,一时间,他成了本市女大学生崇拜的偶像。那时每个女大学生的日记本上都抄录着他的爱情诗;那时老K骄傲得像一只小公鸡,在女大学生面前引颈高歌着。那时,老K不时地会收到几封女大学生的求爱信,他自然不把这些求爱信放在眼里。最后他还是和一个大学生恋爱了,那个大学生没给他写过信,而是在他每次讲课时,总是坐在最前排,一双明澈的大眼睛脉脉地望着他,他便在众多的目光中发现了这双不同寻常的眼睛。于是老K便掉进不能自拔的深潭中。那几年,老K每天黄昏都要像狗一样,钻过大学校园的铁栏杆,找到那个女孩,在林荫路上行。那时,他写出了许许多多关于眼睛和爱情的诗篇。一切进展即将顺利的时候,那女孩突然在大学校园里失踪了,老师和同学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老K像一条急疯了的狗。没多长时间,老K收到了那女孩寄自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封信,才知道那女孩已经去了美国。老K那些日子不写诗了,而是操练起英语,他说他也要去美国。老K的英语还没操练到火候,他又收到了那女孩的一封信,同时还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女孩穿婚纱在教堂结婚时的照片,她的身旁站着一位挺绅士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小伙,她在信上说:让他把过去的都忘了吧,过去的一切就过去了,她目前很幸福,杰克是她丈夫,在宾夕法尼亚是一名杰出的山地车运动员。老K疯了,老K傻了。……
老K从那时候起便开始喝酒,骂人,大把地掉头发,人莫名其妙地瘦下去。他也不再写那些美丽的爱情诗了。老K就在喝醉酒的时候,一遍遍地对我说:“真诚过了,我们便不再真诚。”
老K后来又有了一些女朋友,他真的没对谁再真诚过。
那一天,我和老K从他家里出来,老K随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八一湖。我们俩躺在湖边一块刚萌芽的草地上,昏昏欲睡,一直到黄昏时分。
后来我跟他说了朱美,和昨天晚上的事,我还让他看了我左手心上那排隽秀的小字。老K就说:“我信。”然后我们俩就坐起来抽烟,一边抽烟,他一边思考着朱美和我的种种可能。到最后我也不清楚,朱美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在剧院门口和我邂逅,又约我星期日在紫竹院门口见面。
这时,我想起了我老婆。我和我老婆谈恋爱时,曾无数次地在紫竹院里约会,我老婆是会计,她对数字异常地敏感,而且记忆深刻,可以说过目不忘。就是在结婚以后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她和我在紫竹院约过十八次会。我说:“真的是十八次么?”她说:“是十八次,没错。”平心而论,没结婚时,我老婆还是挺崇拜我的,我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编小说。小说一篇篇地在杂志上印出来。我每发表一篇,她都拿去拜读,读完一遍她就说:“真不错,用劲写吧。”我真的用劲去写了,而且,把得到的稿费如数地交给她,保存起来,等待日后结婚用。
我和老婆结婚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合同制作家。我这人非常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这人的长处就是编小说,其他的再也没有什么长处了。我知道,我离开编小说的行当,其他一切将一事无成。想靠体力挣钱我手无缚鸡之力,想“下海”捞钱,一没门路二没靠山,三没本钱,若要“下海”必淹死无疑……大势所趋,合同作家就合同作家吧。我自己也清楚,想在这个世界上凭稿费吃饭更是难上加难,好赖合同作家还有一份工资,公费医疗,住房煤气水电等等,还有一个大后方,万一一旦脱离开大后方,我将成为和老K一样的个体户,我又没有老K编小报的本领,露宿街头也说不定。
我深知兑现合同的重要性,于是玩着命地写,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手还能拿住笔,思维还没有僵死就写。渐渐地,我发现就写出了毛病,每天上床的时候,都要挨老婆一顿臭骂。老婆就说:“扶不上墙的东西,滚一边去。”我深知对不住老婆,忍气吞声,躺在那一动不敢动,自己咬牙切齿地努力着,自我感觉行了,凑到老婆身旁,一触到她那骚动着的滚热身体,便又不行了。老婆无力地叹口气说:“滚吧,滚远一点,就当没你这个人。”说完一脚把我踹下床来,同时老婆把毯子扔过来。我只好抱着毯子睡到沙发上。
那些日子,我一面在稿纸上挣扎,一面在床上挣扎,结果弄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从此,老婆再也不看我发表出来的东西了。过了不长时间,老婆和别人合伙“下海”了,老婆果然身手不凡,不长时间就收获颇丰,我每次从邮局取回稿费,以前这是老婆对我最温柔美丽的时刻。此时,老婆再也不用正眼咴我那点含辛茹苦的稿费了,她哼都不哼地说:“臭显摆什么,你那点钱,还不够我撮一顿的呢。”同时我也发现,老婆日渐回来得晚了,每次回来老婆都打着酒嗝,浑身再也不火热滚烫了,对我这个人也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有一天,我正在床上努力着,以求得她的欢心,突然她在身下冷冷地说,“你不想尝尝离婚是什么滋味?”一下子我便绝望在那里,我简直要呜咽了。
从那以后,老婆每天回来得更晚了,有时干脆就不回来。我知道,她是在向我宣战。我默默地忍受着。
有一天,参加一个哥儿们的聚会,回来时,一进门,看见老婆正和一个陌生男人亲热地坐在沙发上吃苹果,那男子见我回来,站起身说:“阿芳我走了。”阿芳是我老婆的名字。老婆却说:“刚到兴头上,再坐会儿嘛。”那男人冲我笑一笑还是走了。
那一晚我因喝了些酒,就多了一分胆量,冲送人回来的老婆说:“恶心,真恶心。”
老婆非常镇定地说:“你他妈说谁恶心呢,我还没说你呢。一个大男人连自己老婆都拴不住才他妈恶心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说这种粗话。一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我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她怔了一下,接着又乐了。然后说:“好,我就盼着你有这一天呢,咱们缘分从现在开始,结束了。”
“结束就结束,臭女人有什么了不起。”我气呼呼地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说。这房子是结婚时老婆单位分的,缘分尽了,该走的是我而不是她,这一点我清楚。
临出门时,她说:“什么时候想好,什么时候回来办个手续,我随时奉陪。”
我也不示弱地说,“什么时候都行。”
住进办公室,酒醒了,那股冲动劲下去了,便有些后悔。后悔归后悔,但我知道,我和老婆的关系完了。不是因为那一巴掌,一巴掌只是一个理由而已。这么一想,也就想开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我想,是她先背叛了我。
那个春天的晚上,我和老K又坐在了小酒馆里。
他真诚地举起酒杯说:“为朱美干杯!”
我笑着和老K一饮而尽。
老K又说:“真诚过了,这个世上再也没真诚了。”
此时我有些同情地望着他那双哀伤的眼睛。
“为了生活干。”我这么提议,我心里装满了柔情。
“我真羡慕你。”老K又干完一杯这么说。
此时,我又想起朱美,心想,你在哪里呢,昨天晚上此时我们正坐在中国剧院里,我心里那缕柔情随着酒融化了。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遥远的,一家商店里有歌声传来: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
谢谢你给我的爱
今生今世不忘怀
……
后来我和老K摇晃着走出小酒馆,走进春风荡漾的大街上。耳畔响着那首情意绵长的歌声——
我时时刻刻忘不下朱美了,盼星期天早日来到。朱美此时在我心里像一个神话故事里那神秘的女仙,在我眼前飘浮不定,时而朦胧时而具体。
星期天,八点不到我就赶到了紫竹院公园南门,我翘首以待,东张西望着。我不知道朱美将来自何方。我又想起那天晚上在剧院门口等老K的情景。
八点还差五分的时候,首体路口方向走来一位极像朱美的女孩,她没有穿那件红色风衣,一条白得耀眼的牛仔裤,一件黑色宽大毛衣外套,婷婷地向这里走来。我的心狂乱地跳了起来,迟疑地向前迈动着脚步,我一时拿不准过来的女孩是不是朱美,那天晚上,我一直都是和朱美在朦胧中交往的。她来到了近前,说了声:
“你好,让你久等了吧。”
果然是朱美,我一听见她的声音,马上认定果然是朱美。
“刚来。”我这么说,其实我已等了有半个小时了。
她说:“咱们进去吧。”
于是我和她走进了紫竹院公园。园里的一切是那么新鲜宁静,我曾无数次地来过这里,却没有一次像这次激动不安过。
我说:“你以前来过这里么?”
她说:“当然。”
我说:“你自己?”问这话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她说:“当然不是。” 我笑一笑。她也笑一笑。
后来我们进了园中园,这里比外面清静多了,再后来我们就坐在一簇新鲜的绿竹下,太阳温暖着我们。眼前是一池清水,清水上浮着荷花叶子。
我说:“你知道齐白石么?”
她说:“当然知道。”
我说:“当年齐白石就在这里画虾写生,园外那条路就叫白石桥路。”
她说:“我还知道前面魏公村还有白石墓呢。”
我说:“是么,我还从没听说过。”
她很骄傲地笑着。
我说:“你家离这不远吧。”
她看着我。
我补充:“要不,为什么你对这这么熟。”
她笑了,没说远,也没说不远。
这时,日影渐渐在头上移着,世界极静,恍似一切都睡了过去。半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一阵风吹过来,有几根头发在她眼前飘浮着。我在风中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芬芳。她坐得离我很近,大约也就是十几公分的样子。我心里挺激动,试探地向她近前又移了移,她对这一切似乎没有任何反应,我的胆子大了一些。把手伸过去,搭在她的肩上,她对这一切似乎期待很久了,把头偎在我的肩上,她的头发撩着我的脸颊,弄得我浑身痒痒的,这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缕芬芳,我似乎醉了,在这春天的紫竹院里。她似乎也要睡去了,偎在我的胸前一动不动。我们就这么静默着,时光悄然流逝,转眼又到了黄昏。她似突然从梦中醒来似的说:“我该走了。”
我说:“是么,过得这么快。”
当我们俩向园门口走时,我恍似丢失了什么东西,心里空空的、怅怅的。走出园门时,我才想起还没有约定下一次呢。
我便立住脚说:“下一次,还在这么?”
她犹豫了一下,立住脚说:“我这阵很忙,你给我打电话吧。”
我说:“行。”
她从兜里掏出一支小巧的圆珠笔,又拉过我的左手,在上面写下了一串数字。然后说了声:“再见。”便翩然而去了。我恍惚地站在街上,看着她青春的身影消失在车流人流中。
那天晚上我躺在办公室的床上,久久睡不着,窗外的月光光洁明亮。
我就想,朱美是从哪里认识我的呢,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我就想到曾出入过几次大学里的文学社团,给他们讲过课,也参加过几家刊物的颁奖会,照片也曾在刊物的封二或封三上出现过几次。这么想着便有些释然了,也许朱美读过我的作品,通过这些方式认识了我,然后和我接触。我真的为朱美感动了。我又想起她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我借着月光看着左手心里那排秀气的阿拉伯数字:6013355。看着看着,这一串数字,变成了朱美的影子婷婷地向我走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给朱美打上一气电话。三楼我们头儿的办公室就有电话。门是锁着的,碰锁上有一条缝,我用皮带把锁捅开,再把门锁上,于是整个办公室就成我的了。
每次都是朱美接电话,我一听见她的声音就知道是她,她一听见我的声音,同样也能听出是我。我黑着灯,在电话里和朱美聊天,仿佛朱美就坐在我的对面。
每次和朱美聊完天,心里都有一种畅快无比的感觉。可静下来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想起我老婆,现在她在干什么呢?我不是多么思念她,而是因为有了她,我和朱美之间这种来往,我总觉得怪对不住朱美的,好像我欺骗了她。
有一天,我回到了久别的家里,家里的一切摆设依旧,仿佛我刚出了一趟差,又回到了这里。
老婆仍在床上睡着,毛巾被里露出一只丰满的大腿,我站在老婆床前,觉得一时竟口干舌燥。不知什么时候,老婆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咱们的事什么时候办?”
我醒悟过来,老婆这么说完,我的心一下子透亮了许多,仿佛我对这话期待了许久似的。于是我无比镇定地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办。”
老婆说:“明天。”
我说:“好,就明天。”
老婆说完,转了个身又睡去了。那条光洁的大腿仍露在外面,我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心想,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再看它了,以前它是属于我的。
转天,我和老婆来到了离婚办事处。原来她早就安排好了,办事处里有个老太太,是她同学的母亲,真是熟人好办事。我们上午领了表,填好,又分头各自回单位盖上章,下午就把离婚证书领到手了。按规定,要等上三个月的。我就想:这世道,也真他妈的了。
我和老婆走出办事处,心里一时竟说不出什么滋味,我又仔细认真地看了几眼老婆,我们毕竟相亲相爱过,到现在她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曾去过紫竹院公园一共十八次。我最后又叫了一次:“老婆。”她看了我一眼,很妩媚地冲我笑了笑,然后伸过一只手说:“再见。”我只用指尖碰了碰她的手,便转过身各走各的路了。
那天晚上,我又和老K在小酒馆里喝酒。
老K又说:“为了我们曾真诚过,干!”
我说:“干!”
老K说:“人呢,这辈子真他她不易。”
我说:“说容易就容易,说不容易就不容易。”
我们又举起了酒杯,两只杯子清脆地碰在了一起。
老K说:“朱美还好?”
我说:“好,很好。”这时我又温馨地想起那串阿拉伯数字。我想,明天无论如何要见她了。
这时录音机里又响起那首叫《小芳》的歌: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
那天晚上我们双脚高高低低地走出小酒馆。我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三楼用皮带捅开锁给朱美打电话。
这么晚了,朱美好似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我的电话,电话刚响了一声,就听见朱美的声音,她说:“你好!”
我说:“你好,明天……我要见你。”
她说:“什么时候,在哪?”
我说:“八点,紫竹院南门。”
她说:“好。”
我说:“好。”
我摇摇晃晃走到厕所就吐了,吐得翻江倒海,气吞山河。
那一天,在紫竹院我又见到了朱美。此时已是春末夏初了,到处都是莺飞草长。我和朱美默默地向公园深处走去,今天不是星期天,大白天的公园里人很少,只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在练气功。一切都静止着,仿佛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后来我们相拥着坐在一片竹林里,叶影斑驳地照在我们的身上,草地的芬芳,竹林的馨香,朱美的芳馨交揉在一起,我吻了她。这时她闭着眼睛,有两滴又圆又大的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流了下来。
“你不高兴?”我颤抖着声音问。
她好半晌没有说话,眼睛仍那么紧闭着,直到那两滴泪水在她腮边消失,她这才睁开眼睛,很灿烂地冲我笑了一下,我第一次发现朱美有着这么整齐洁净的牙齿,这让我激动了好一会儿。半晌,她说:“我真的好高兴呢。”
再后来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透开斑驳的竹叶空隙望头顶破碎的天空。
“此时此刻,我一生也忘不了呢。”她喃喃着。
“我也是。”我这么说时,望着她陶醉的神态。
我终于伏下身子,我们热烈又缠绵地紧紧搂抱在一起。
慢慢地,我觉得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嘎”地一响,然后我觉得有一股力量从脚底慢慢升起,最后涌遍全身。此时此刻,我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气力,每块肌肉,每块筋骨都坚强地挺立起来,此时,我感觉,我可以征服世界上的任何什么。
当繁星拥满头顶的时候,我们才恋恋地走出竹林,后来她在一个十字路口很温柔地吻了我,轻说了一声:“再见。”然后转过身消失在车流人流里。我怅然若失地站在十字路口,觉得和朱美在一起的一天,恍似梦一样地就过去了。
那几日,我在极度亢奋极度焦灼中度过,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朱美,装着一个崭新的爱情。不少人都惊愕地望着我,以为我因离婚受了刺激才有了这不同寻常的情态。我心里说:“你们他妈的永远也搞不明白有了爱情是什么滋味。”那些日子,我一点也没有想起老婆。
爱情是幸福的,也是折磨人的,那些日子我虽然精神亢奋,人却瘦了。我期待着下次再和朱美见面,下次见了朱美我一定向她求婚,向她彻底表白爱情。
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想约朱美见面的时机到了。我又像贼一样溜到头儿的办公室门口,用皮带捅开门锁,操起电话,迫切地拨电话,电话通了。这次接电话的不是朱美,而是一个老头的声音,我冲着听筒说:找朱美。老头惊讶地又问了一遍:“找谁?”我更清晰地重复了一遍,老头这次很凶恶地说:“没有这个人。”接着放下电话。我起初怀疑是不是拨错电话了,我又拨了一遍6013355。接电话仍是那个声音,这次我详细地向他描述了朱美的外貌和声音,老头很有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坚定不移地说:“我们肯定没有这个人,这个办公室十几年了一直是我自己。”说完便挂断电话。“真他妈活见鬼了。”我骂出了声。我不知自己要干什么,心想,一定要找到朱美,不管她在哪里,可朱美除了给我留下这个电话外,别的没有任何地址。我开始怀疑老头在骗我。我要去一趟,找到这个电话的单位,我怕老头耍什么花招,我这次直接拨通了114查号台,我问查号小姐6013355是什么单位,查号小姐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我,是第二监狱收审室。我听到这就有些愣了,朱美怎么会和监狱联系在一起,我躺在床上就想起了这几次和朱美的接触,她的确实实在在存在过,亲我时那味道那感觉仍在我的唇上回绕。我决定无论如何,明天我得去监狱一趟,那一夜我一直没有睡踏实。
第二天一早,我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第二监狱,找到了那间收审室,值班的仍是那个老头,老头用狐疑的目光望着我,我真诚地向他描述朱美这个人,老头很有耐心地听着,我说完了,老头才说:“你看看,我们这哪有朱美,只有犯人抓来才放在这里。”我又屋里屋外地看了一遍的确没有朱美这个人。我在收审室门口站了好久,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什么时候才离开监狱的。
我突然想起了剧作家老林,我记得刚见朱美时,她曾问过,老林还好么?当时我没多想。接下来,我又迫切地来到老林家,老林正在为电视台赶写一个什么剧本,他听我打听朱美这个人,想了好半晌,还是摇摇头说:“没印象了,她真的认识我么?”我又详细地描述了朱美的身高、相貌,说话的声音……老林听完还是摇摇头说:“记不清了,没印象了。”最后老林又拿出他的通信录,一个个地查,也没查到朱美这个人。
我从老林家出来,近似绝望了。我想到了老K,老哥是我哥儿们,也许他能帮帮忙。我见到老K时,他正在独自喝酒,他一见我就说:“你小子他妈有了爱情就忘了哥儿们。”
我什么也没说,抓过他的酒杯先灌了几口才说出详情。
老K就唉叹一声说:“我们都真诚过了,这就够了。”
“去你妈的。”我大声说。
老K惊惧地望着我,半晌终于气忿地说:“那你就去找,无论天涯海角。”
我从老K的眼睛里看出,他仿佛对这一切早就有预料似的。我就想,老K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又来到紫竹院门口,我在等待朱美。我从人流里辨认着,寻找着。天暗了,天黑了,夜深了,公园门口不再有一个人了,我才怅怅地回去。
一连很多天,我都在等待着朱美。
最后我在大街上开始寻找,从海淀到丰台,再到西城,再到朝阳……那些日子,我跑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没有看到朱美的影子。时间转眼到了秋天。我想,北京是找不到了,只能去外地了。我要走时,告诉了老K,老K对这一切似乎也早就有预料了,很随便地问我:“你几时走?”我说:“明天。”
正当我收拾完行囊准备出发时,老K来了,他带着酒和菜。他说:“喝酒,喝完酒再走,酒是好东西。”
我们便开始喝酒。
酒喝光了,最后他说:“你先准备去哪?”
我说:“没准,就是找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
老K一挥手像将军一样地说:“那就去吧。”走了两步又回过头说:“别忘了时常来个信。”
我说:“知道了。”
坐火车,再坐汽车,然后徒步前行,我来到一条大河边,在一间没人住的棚子里住下来。从这为圆心我开始寻找朱美。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老K寄来的一份报纸,报纸的右下角发了一条和我有关的消息——
本市合同制作家Q去黄河体验生活
老K报道:合同制作家Q为了深入生活,写出改革大潮中更贴近生活更有分量的作品,日前只身一人去黄河流域体验生活……
在大河畔的沙滩上我碰到一个牵牛饮水的汉子,我指着面前这条宽大的河问:“这叫什么河?”
汉子不看我望着远方说:“是长江。”
我在心里恨恨地咒了一声老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