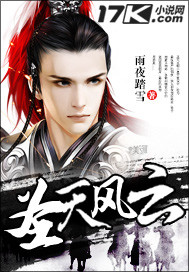话说封印姜魁的五彩神石被两个少年从长平战场附近的大粮山上,带到了项羽坑杀二十万秦卒的新安城南氓苍山,结果在二十万秦卒的怨气和尸气的帮助下,姜魁破除封印重回人世。
姜魁蓦然呆立,良久才记起了曾经的一切。
姜魁记起了自己是谁,记起了长平之战,记起了韩章、莫逾、王二愣,又记起了元让、苏射、赵括、白起。。。。。。一幕幕往事如同一幅幅画面,接二连三的在姜魁眼前纷纷闪过。但是令姜魁不解的是,自己不是死了吗?记忆中的自己被厚厚的黄土压在地下很深很深的地方,令自己喘不过气来,浑身筋骨几乎都要被压断,黑暗之中自己的神智也越来越模糊,最后慢慢的就失去了知觉,而现在,我又是在哪里?
姜魁疑惑的四处望去,发现了远处昏迷着的姜靖和付甲,这两个看起来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吧,姜魁暗道。
姜魁抬腿走了过去,拍拍付甲,没反应。。。。。。狠狠的踢了一脚,付甲哎哟一声坐了起来,茫然的瞅着姜魁。
姜魁面无表情的看了看这个小胖子,说道,
“是你把我救出来的吗?”
付甲一脸茫然。。。。。。
“。。。。。。”姜魁无奈,走到姜靖旁边又是一脚,姜靖也晃晃悠悠的醒了过来,忽然发现面前有双人腿,猛地抬头看去,与姜魁的目光在半空中正好撞到一起。
“哇!”姜靖一声大叫,连连向后退去,“你是什么人。。。。。。你从哪来的,刚才怎么没看见你啊。。。。。。”
姜魁一脸的郁闷,
“我也想问你,是不是你把我从坑里挖出来的?”
“坑里?挖出来?”姜靖转头望去,发现远处一个巨大的土坑出现在原先空旷的地面上,姜靖顿时惨叫一声,
“诈尸啊!。。。。。。”说罢一头栽倒,晕了。
姜魁无语,转头看向付甲说道,
“我很吓人吗?”
付甲也不吭声,只是愣愣的看着姜魁的胯部。
姜魁不解,也低下头看去,一看之下,血液顿时凝固。身无寸缕,春光大泄。
姜魁看着付甲的眼神一阵暴寒,连忙上去把姜靖的衣服裤子扒了下来穿到身上,虽然很紧但起码不用曝光了。
姜魁顿时心安不少,有些恼羞成怒的冲付甲沉声喝道,
“小胖子!赶快告诉我这是哪里?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付甲被姜靖的一句“诈尸”吓得不轻,又见姜魁上去扒姜靖的衣服,还以为姜魁要吃了姜靖,结果姜魁只是扒了衣服而已,这时被姜魁一声喝斥,立马清醒了。哆嗦了一下,付甲颤颤的说,
“我们。。。。。。我们原先是。。。。。。是大粮山下卫家村人,都是他。。。。。。”付甲指了指姜靖,哭哭啼啼的说道,“他非拉着我跟他来这里挖死人坑。。。。。。不关我的事啊。。。。。。”付甲边说边抹鼻涕,那一把把的液体直看的姜魁恶心不已。
姜魁皱了皱眉,问道,
“死人坑?这里埋着什么人?”
“姜靖说,说这里埋了秦军,二十万降卒。。。。。。”付甲仍是哽咽的说道。
“秦军二十万降卒?!难道长平之战后又有什么大战了吗?”
付甲愣了一下,也顾不上鼻涕眼泪的了,掰着指头算了算,最终无奈的说道,
“有很多的,五十多年间打的仗都数不清。。。。。。”
“五十多年?!你说什么五十多年?”姜魁大吃一惊,猛地叫道。
付甲被吓了一跳,不明白这家伙为什么一惊一咋的,怪异的看了看姜魁,付甲有些埋怨的说道,
“长平之战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姜魁骇然心惊!
五十多年?怎么会过了五十多年!这五十年我在干什么?!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突然,一幅幅画面瞬间闪过姜魁的脑海!画面中,一个长着怪异犄角和长长獠牙的人形怪物正在和一帮人拼杀,但不同于沙场的是,这些人都在操纵许多会飞的古怪东西,有瓶子、镜子、烟台、雨伞。。。。。。他们在说什么,凶魔?无尘子?清源?明德。。。。。。头好痛,头真的好痛!
姜魁面现极度痛苦之色,忍不住抱头发出一声惨号,声音震撼山野,直冲天际!
昆仑山上,重霄殿中的无忧突然睁开双眼,眼神中透露着惶恐不安,心中惊骇莫名。
无忧伸出手颤颤的算了算,顿时面无人色。
无忧不禁痛苦的流下了眼泪,
“怎么会这样。。。。。。”无忧心中充满悲苦,师尊舍弃生命封印凶魔,为什么还会让它破印而出?师尊岂不是白白牺牲了!难道这场浩劫最终还是无法阻止吗?
忽然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无忧不用看也知道是蜀山现任掌门明慧和峨嵋现任掌门清云。
性情最火爆的清云最先踏进重霄殿,一边走一边急匆匆地说道,
“无忧,你可知道凶魔破印了!”
无忧叹了口气说,
“知道了。”
清云不禁怒气冲冲的说道,
“那你可知道凶魔为何能够破印?!”清云不等无忧回话就接着说道,“还不是那些凡人!为了争权夺利妄开杀戒!白起死了,又出来一个叫项羽的,一口气坑杀了二十多万人!结果滔天的尸气和怨气帮助凶魔挣开了封印,只可惜我们的师尊。。。。。。”说到这里,清云不禁阵阵悲戚,泪水浸湿了眼眶。
“冤孽啊。。。。。。”无忧叹到,口气和表情跟他师傅无尘倒是一模一样。
明慧在一旁不禁一乐,说道,
“无忧和无尘子前辈倒真像师徒,但为何清云却和清源前辈截然不同,清源前辈是我们三人师尊中性情最温和的,而清云却是我们三人中性情最暴躁的,有趣,有趣!”
清云没好气地瞪了明慧一眼,开口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插科打诨!”
明慧悠然自得的说道,
“什么时候?现在怎么了?咱们的师门不好好的吗?依我看来,凡人的争斗咱们大可不必理会。当初我们的师尊悲天悯人,想让凡世间少死些人,但结果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就会死人,这就和天劫一样,是我们无法改变和阻止的,就算这头旱魃没了,过个几十年又会有新的旱魃出现,说到底,凶魔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本身,只要人类还有欲望,还有野心,就会有凶魔出现的可能!”
无忧点了点头,但仍是皱着眉道,
“话是没错,但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岂不是辜负了师尊的教诲。。。。。。”
“无尘子前辈临走前的吩咐是什么?”明慧不慌不忙地问道。
“师尊让我留守山门,为昆仑山留点人脉,好将昆仑道法发扬光大。”一提到师尊,无忧立刻面容一整,肃然无比的说道。
“这就是了,如果无忧道兄坚持去除魔,想必没有半分的把握吧?”
无忧不禁点了点头。那可是天尸旱魃啊,三位师尊和三派所有的高手不要性命也只是能够暂时封印而已,就凭三派现在的力量,去了就是送死。
“如果我们带领剩下的这些入门不过二十多年的弟子前去除魔,那和送死没有任何的分别,到时昆仑、蜀山、峨嵋就此灰飞烟灭,那才是辜负了师尊的教诲!”明慧面容严肃的说道,令无忧和清云悚然一惊。
“对!凡世间的事情我们不管了!让他们折腾去吧,好叫他们尝尝自己酿的苦酒!”清云气狠狠的说道。
无忧长叹口气,无奈的说道,
“也好,自作孽不可活,我们确实管不了了,但愿他们好自为之吧。。。。。。”
姜魁终于大致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眼前这两个一个叫姜靖一个叫付甲的少年,在大粮山上找到了一块五彩石头,然后他们带着这块石头来到了氓苍山,据付甲说,当时那块石头从姜靖怀中飞了出来,不停的吸收一种黑黑的气体,然后突然爆炸,接着两人就都晕了,醒过来就看见一丝不挂的姜魁站在他们面前。
姜魁对照脑海中曾经闪过的画面,发现里面也有一块五彩的石头,还有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气体。
姜魁前后思考了半天,终于可以差不多的确定,那画面中的人形怪物应该就是自己了,后来被那个叫做无尘子的老头领着一帮人把自己“装”进了那个五彩石头里,然后扔到了大粮。五十多年后,这两个少年把那块石头带到了氓苍山,应该是那黑色气体的缘故,自己又从石头里蹦了出来。
姜魁想到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而最关键的问题是,自己还算是人吗?
姜魁摸摸胸口,触感冰凉,而且好久没有感觉到一下心跳,这都说明了一个极其残酷的问题,自己是个死人,一个活着的死人。
姜魁欲哭无泪,以为自己活过来了,但没想到自己还是死的,看看姜靖和付甲那惊惧的眼神,就知道他们也没把自己当人看。不过想想,这样总比那些被埋在长平的兄弟们好一些,毕竟自己还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世界,而他们则永远没有可能了。姜魁不禁这样自我安慰着。
姜靖只穿着一条裤头,在寒风中哆嗦着身体,看着正在苦苦思索的姜魁,他壮起胆子问道,
“你。。。。。。是人。。。。。。是鬼?”
姜魁回过头来,凄然的笑了笑,说,
“我也不知道,说了你们可能也不信,我是从你们在大粮山捡到的那块五彩石头里面出来的,我是怎么进去,又是怎么出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不用怕。”
姜靖想了想,胆子更大了一些,
“我记得,我们村里的一些老头说过,方士抓鬼的时候,如果灭不了的话就会找个东西把鬼封印起来,好像。。。。。。好像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也许吧,我现在应该不能算作是活人了吧,说我是鬼也没什么错。”姜魁黯然感伤,当一个人失去了生命才会知道生命的弥足珍贵,但一般人失去了生命也不会有什么想法了,至于能体会到这种苦涩的,普天之下应该只有姜魁这个死而复生的“人”吧。
“那。。。。。。你要去哪里?”姜靖似乎知道面前的这个怪物无害,便放开了不少,开始和姜魁套话了。
“去哪里。。。。。。”姜魁一阵茫然。
去哪里?我还能去哪里?我一觉睡了五十多年,现在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我还有地方可去吗?
家,姜魁下意识的想到了家。
“我要回家!我要回邯郸!”霎时,姜魁的热泪滚滚而下。
通往邯郸城的官道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木已然遮天蔽日,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气息,现在正是一年中天气最好的时候。
姜魁倒是没什么心情欣赏风景,但却因为多了两个“尾巴”,也只好放慢了速度,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来到邯郸。
邯郸城。
此时的邯郸城依然繁华,虽然现在天下只是暂时的平静,说不定哪天就又会再起战端,但老百姓不会管这些,他们还是要活下去,所以,店铺商行除非兵临城下是不会关门的。此时,邯郸西城的主干道旁正是商贩做买卖的黄金时间,抬眼望去,到处人声鼎沸,车马如云。
随着人群,姜魁走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看着路旁随风招展的酒旗幌子不禁激动异常,在长平打仗的时候,曾经几次梦回邯郸,醒来都是一脸的泪水,这次终于回来了!
“嘿,这邯郸城可真够大的!”付甲眼花缭乱的说道。
姜靖穿着一件付甲从河边偷来的衣服,本就被宽大的衣袖弄得烦不胜烦,又看到付甲一副傻头傻脑的样子,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费劲的捋起衣袖,从后面就给了付甲一个凿栗,不满的说道,
“你少给我丢人!一看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而付甲则是一副苦头苦脸,有苦说不出的小媳妇模样,直令人捧腹。
姜魁回头看了看,不禁一阵苦笑。
从氓苍山出来,这姜靖就死活要跟着自己,说他娘生下他就死了,他爹几个月前也去世了,家里就剩他自己一人,无牵无挂,一定要跟着姜魁出来见见世面。
姜魁曾恐吓姜靖说要吃了他,谁知姜靖很是不屑的说,“你要吃早就吃了,而且看到你流泪的样子就知道你不会吃我,就算你是鬼,你也是个有感情的鬼,你是不会随便杀人地。还有,你是被封印而不是被打得魂飞魄散,说明你很有实力,不跟着你出来混混世面我岂不是白白被你吓晕过去。”
姜魁无语。至于付甲就更好说了,虽然姜靖一直对他凶巴巴的,但是付甲从小就是孤儿,要不是姜靖总为他出头,他早被村里的坏小孩儿欺负死了,于是自然姜靖去哪他就去哪。
不过这样也好,有了这两个活宝,一路上倒也不会太寂寞,而且从姜靖和付甲的嘴中,姜魁了解了不少这五十多年来天下发生的大事和现在名震一方的人物,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名字让姜魁记忆深刻,秦始皇,项羽和刘邦。
同时,姜魁也知道了如今的天下是谁说了算,那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被称为盖世无双的猛将,西楚霸王。
听到这个名字,姜魁体内似乎有股热流在涌动,那是一种尘封已久的战士的欲望。
通过姜靖和付甲的叙述,当姜魁知道白起被秦昭襄王勒令自杀后,姜魁久久无语。
白起啊白起,你一代名将竟会如此下场,不知道元让、苏射、赵括他们知道了你有如此报应会是什么感想?杀人者最后把自己也给杀了,这算不算是个天大的讽刺呢?还是因为没有人能杀得了你,除了你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此时的姜魁居然没有临死前那么的怨恨白起了,难道说睡了五十多年,当初那么强烈的怨气和恨意都消散殆尽了么?姜魁甚至在想,如果自己是白起,又会怎么做?杀?还是不杀?而除此之外,姜魁剩下的也只有遗憾了,遗憾自己没能成为他的对手,遗憾自己不能亲手打败他,割下他的首级。
而在来邯郸的这一路上,姜魁随处可闻赵国百姓对赵括的咒骂,恨不得把他从地下挖出来鞭尸三千,而亲身历经长平之战的姜魁却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姜魁重回人世后,反复思考了长平之战的整个前后经过,他想了很多很多。
其实赵国从胡服骑射后,经沙丘之乱,内外交困,国运衰微,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力日盛,攻与守,固然有一定战略上的意义,但战争最终是靠实力决定胜负的,不可否认,单单在战前秦赵整体实力的比较上,赵国就已经输了。而且当时多出名将的赵国似乎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自从马服君赵奢死后,蔺相病重,就只剩廉老将军一个人独撑危局,而小一辈的将领中还没发现有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像上党这么重要的战事,赵国竟还是派出67岁高龄的廉颇老将军领兵挂帅出征,能有比这更无奈的么?
秦军远道而来在于速胜,急于与赵军主力进行决战,以结束战争,而廉颇老将军身经百战,一眼便看出长平的地理位置优势,于是令赵军主力扼守长平避战不出,以迟滞消耗秦军,届时秦军将不战自退。到那时,只待战机出现,全军而出以逸待劳击溃秦军。
然而这一切全被赵括的到来所打破了。赵括是一个不能够以国相托的人,赵括不见得不能打仗,但是他过于轻浮和自大,这场决战要的是必胜,对赵国来说不能冒险,赵括换一个地方拜将,比如秦、楚,可能都会是不错的将领,但要他在赵国生死存亡关头领一国之军,与强秦决战,非他之能,更何况,他的对手是白起。
统帅失败,国君则更加失败。
秦昭襄王在55年的从政生涯当中,使秦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削弱了六国的实力,而且还剔除了秦国内部对王权有威胁的势力,为后来始皇帝最终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国家权力的集中、军队实力的强横、内外政权的稳固,秦昭襄王已经作了他可以做的一切。
长平大战之后,秦国独霸,更是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起兵攻周,掳姬延入秦,既而释归,没过多久,姬延崩,周亡,立国879年曾经辉煌强盛的周朝就这样亡在了秦昭襄王手里。
经此一战,秦昭襄王奠定了秦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基础,秦国由此更是声威大震,统一天下已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所以秦昭襄王死后,秦国举国哀恸,上至豪门权贵,下至贩夫走卒,都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涌上街头,对秦昭襄王展开各式各样的哀悼活动,纪念这位为秦国强盛而殚精竭力的国家领袖,如果非要说秦昭襄王有什么重大的失误的话,那也就是杀掉白起了,但在姜魁看来,这是白起罪有应得的报应,怪不得秦昭襄王。
按姜魁的想法,如果让秦昭襄王多活上三十多年,统一天下的壮举必将由他来完成,就没嬴政什么事了,而相比来说,赵孝成王就差得太远太远了。
由此可见,长平之战上,秦国有这样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在背后撑腰,赵国则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执掌朝堂,别说是赵括,就算是廉颇来指挥长平之战也未必会赢,所以把一切的罪责都推到赵括身上是绝对不公平的,这场战争,从国君到朝廷到将领,赵国就没有一个地方不输给秦国,焉能不败?